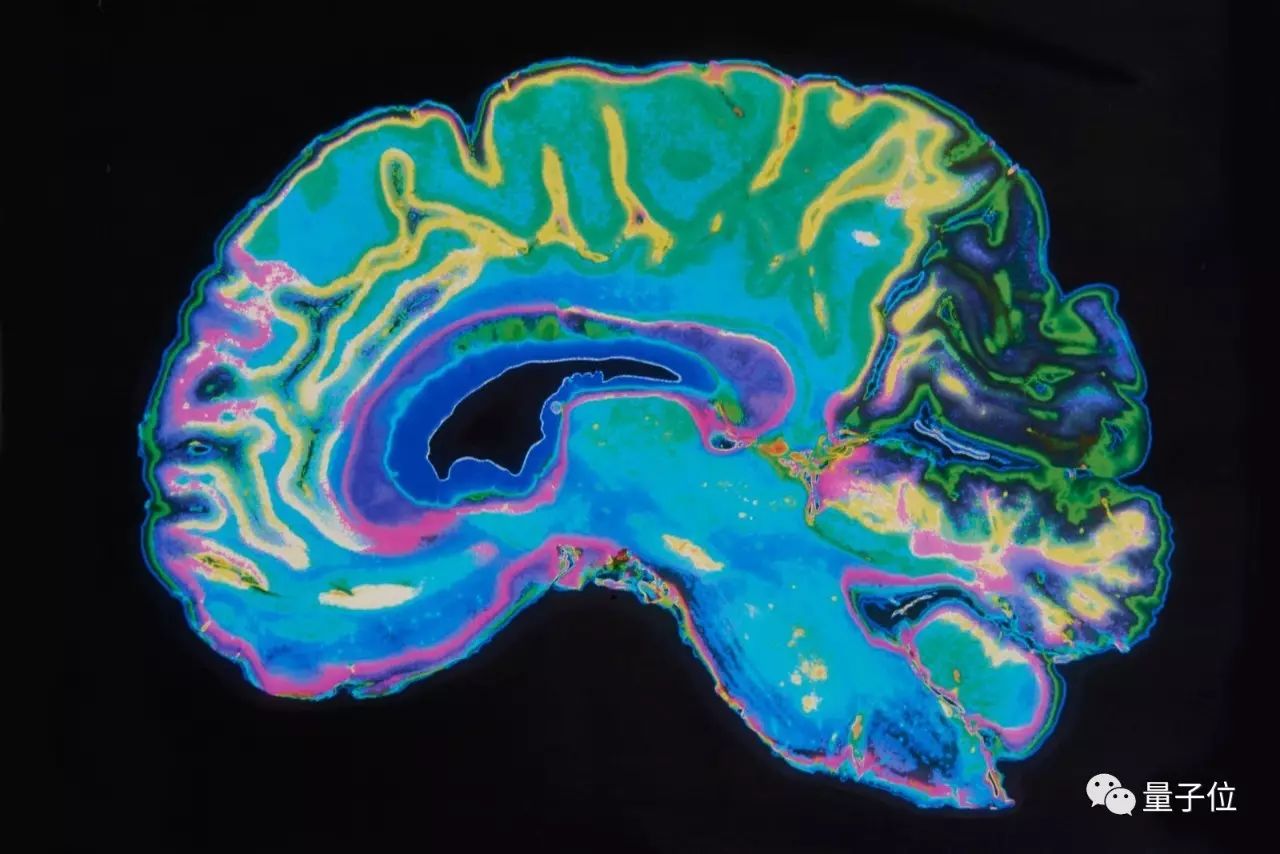一场以“冥婚”为主题的街舞,让这种奇怪的民俗一下子引起了世人关注。尤其舞蹈编排集现代舞美和邪典(cult)于一身,颇有几分阴森可怕的意味。
近日,山东德州被虐至死的女子方洋洋被安排阴婚——原本并不被关注的习俗,再次引发了大量讨论。人们关心它,除去故事本身的荒诞与耸动,更是因为它与现代的观念格格不入。
一个现代人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看起来极其愚昧的习俗,这究竟是出于什么社会心理,又为什么还能延续至今?
冥婚又称幽婚、冥配、鬼婚、配骨、阴婚、娶骨尸、丧娶妇、鬼媒,是指亲属按人间的婚仪为生前未婚的死者寻找配偶行婚礼,使之能在阴间过上夫妻生活。
为什么要给死者找个配偶结婚?这说到底与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信念有关:
死后无嗣者将化为无法得到安息的“厉鬼”,会不断搅扰生者,以期得到祭祀。
虽然常说人死之后,“阴阳永隔”、“人鬼殊途”,但实际上古代更普遍的信念是生死两界并不绝对分离,所以祖先的“在天之灵”仍可以赐福,鬼也能对人施害。
万志英在《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中说,中国人“崇拜祖先的一大主要目的是使死者待在自己应在的地方”,而
那些“寿数未尽”夭折或凶死的人尤其危险,因为他们没有子孙给他们上供,还会在世间游荡,可能给活人带来疾病乃至死亡
。
[美]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 著,廖涵缤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
在缺乏医疗条件的时代,未成年而亡的现象相当普遍,即便是帝王之家也难避免。据《生活在清朝的人们》一书统计,清朝从顺治到光绪的九位皇帝,共生下146位子女,其中就有74人殇逝(15岁以下夭折),竟占了一半多。可想而知,穷人家恐怕就更严重了。
在近代西方,未成年儿童夭亡也是常有的事,1702-1714年间在位的英国女王安妮多次流产,生下的婴儿也都夭折,共有18次之多。直至18世纪,随着马尔萨斯主义的诞生和避孕方法的推广,儿童夭折不可避免的观念才最后消失——在中国则晚至20世纪。
这种还未成家就夭折的孩子,在古人看来都属于非正常死亡,必须另行安排
,这一点在边远族群中仍可看到。彝族将死者分为四类:幼年夭折、中年病故、凶性横死和老后自然死亡,最后一种才被视为“理想的死”。在云南德钦县的奔子栏,当地藏族对有子嗣的死者一般都采取土葬,但对无子嗣者(包括幼年夭折者),则实行水葬。
滇西的阿昌族村寨,亡者若是死于非命,葬礼就较为简单,且不能葬在老祖坟里;而夭折的孩子非但没有葬礼,而且在出殡前,常常还有“破相”的风俗,即把小孩的脸划破或打烂,有的甚至要割下耳朵、鼻子,然后弃之野外——这看起来残忍而难以理解,但
从社群的心态来说,正是出于对“厉鬼”的恐惧,是为了让这些“厉鬼”不敢轻易报复生者,将他逐出活人的世界
。
近代来华的西方人很早就注意到,在中国社会观念中,死后无人祭拜的亡魂是最为可怜、也最为危险的。
玛丽·布莱森(Mary Bryson)根据自己1890年代在武昌的生活见闻,在《中国儿童的生活》一书中说,中国的父母坚信,夭折的孩子是“某些邪灵的附体,仅仅是开始焦虑和不幸的源头,越早忘记他们越好”。
科马克夫人(J.G.Cormack)在民国时期的北京也注意到,夭亡的孩子从不被埋在家庭墓地中,“因为那意味着收养,而收养一个邪灵进家是件很愚蠢的事”。在香港新界,人们害怕把自己未婚子女的牌位放在屋子里,“因为她们可能会游荡于整个屋子”。在台湾民间,人们常说“
你必须为女儿的亡魂做点什么,否则她就会回来找麻烦
”。
要处理这些未婚而亡的死者有很多不同办法,除了另行安葬之外,还常常集中将其牌位特别安排在寺院里镇魂,而冥婚说到底也就是为了让未婚而死的人得以安息。
武雅士 著,彭泽安、邵铁峰 译,郭潇威 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在考察台湾民间社会之后,1965年写下著名的《神、鬼和祖先》一文,发现中国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意父母要抛弃青少年儿子的亡魂,而非自己去祭拜他们”,因为祖先崇拜之下,是子孙应该祭拜父母,而父母永不会祭拜自己孩子,他断言
冥婚(ghost marriage)的目的“不是为死去的女孩提供性伙伴,而是给予她们有责任对她们加以祭拜的孩子”。
这样一来,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就不再是无人祭祀的孤魂野鬼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虽然现在人们常常以为,冥婚是一些父母为死去的儿子找对象,但其实,
在传统上,更多的倒是让未婚夭折的女儿“嫁出去”,因为她们在父系制社会中更难找到位置而变成游魂野鬼。
更重要的是,她们“婚配”的对象不仅限于未婚男性。
武雅士就发现,以往台湾民间社会,一个女孩的父母“摆脱他们女儿亡魂的方式,就是为她诱捕一个丈夫”。办法是将其名字、生辰八字写在红字上,放在钱包里,一旦有人路过捡到,就被视为“命中注定要娶她的证据”,而此人“是否已婚并没有关系”。甚至相反,“
结婚的男人是被优先考虑的,因为他们有孩子,而他们的孩子有义务将亡魂当作母亲来祭拜。
地方风俗认为,亡魂是男人的第一任妻子,因而给予她被她丈夫所有孩子祭拜的权利。”人类学家焦大卫(David K. Jordan)发现,台湾的中南部的冥婚,新郎通常是新娘姐妹的丈夫。
在日本,自古以来也像中国人一样害怕那些非正常死亡的“怨灵”,在日本山形县的村山地区也流传着一种冥婚习俗,让未婚而死的年轻男女与虚构人物结婚的绘马,称之为“ムカサリ絵馬”(むかさりえま)。这不仅寄托了家属的哀思,能让死者在阴间不再孤单,也预防了他们变成可怕的怨灵,实际上相当于一种安魂法术。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这种习俗的结婚对象绝不能是活人,否则据说可能被带去阴间。这也体现出中日文化上的不同:
日本人着重于镇魂,并与生者的世界隔绝分离,而中国人在意的是把未婚的死者安置在家庭的系谱中,使之有权利在祭坛中得到一个位置,以此获得安宁
。
对高度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来说,鬼神这类彼岸世界已经是令人敬而远之的存在,冥婚则听着就有几分瘆人;然而,如果相信人鬼并存于世上、也能相互交往,人们心态可就很不一样了——至少要复杂得多。
对于有些家庭来说,
冥婚不仅仅只是让夭折的子女能在阴间安息,也很好地安抚了两家生者的心灵
。
1925年生于河北望都县的历史学者丁守和曾回忆,他父母很早给大哥定了娃娃亲,两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但“自从有了我这个男孩以后,原来由两个儿子分的家财,就要由三个人来平分”,于是女方提出退婚。他未过门的大嫂非常难过,抑郁而终,不久之后,他大哥也因病离世。两家商量下来,为他俩举行冥婚合葬,以安慰其在天之灵。
不仅是民国时期的河北农村如此。香港著名音乐人、Beyond乐队的鼓手叶世荣,曾与女友许韵珊深深相爱,不料她2002年意外身亡,伤心之余,叶世荣就在其葬礼上举行冥婚仪式,为她戴上结婚戒指,在此后的音乐专辑中也一直不忘亡妻,这一度让无数人为之感动。
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下就能意识到,中国很多著名古典传说中都隐含着冥婚的意味。最明显的是梁祝故事:梁山伯死后,祝英台经过其墓地,恸哭之后投身墓穴,两人灵魂化为蝴蝶——这常被视为凄美的殉情,因为人们通常只留意到两人之间死亡也无法分开的爱情。
更早之前,在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在被拆散后各自殉情自杀,“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暗示其家人承认了他们死后又成了夫妇。明代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中,杜丽娘伤情而死,化为魂魄,与阳间的书生柳梦梅相爱后,又起死回生,其间也有冥婚的影子。
吴光正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原型与母题》一书中推断,中国社会流行久远的种种人鬼恋故事,其主要来源就是冥婚习俗。在这些故事中,往往“女鬼生前大都为妙龄少女,未遂人道便暴病而亡”,因此人鬼遇合时,
往往是女鬼的形象更为勇敢大胆地追求未得到满足的情欲,而“故事中的尘世男子就显得被动、怯懦、卑琐、自私和不负责任”
。
他更进一步指出,这些故事越到后来越被浪漫化、世俗化,以至于女鬼变得越来越像人,甚至寄托着现世中的落魄书生对异性的美好愿望,成了他们的“精神补偿品”。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共有17个人鬼恋故事,但“其结构和文本意蕴已迥异于前此的人鬼恋小说,它不是以尘世男子在阴间安慰亡灵为目的,而是以阴间女鬼来到尘世,让落魄书生实现自我安慰为目的,
传统的冥婚模式完全被复活模式所取代
,女鬼的形象不再仅仅是一个备受性压抑的亡灵,而是一个集传统妇德于一身的圣母”。像聂小倩、小谢、秋容这些女鬼们不再可怕,倒成了“传统妇德典范”,不仅美貌、多才,而且“无论对前妻还是对后妇,女鬼们身上均体现出不妒之德”。
这最明显地体现在《聂小倩》故事中,她“十八夭殂”,在死后与书生宁采臣相遇倾心,之后复活,竟为佳偶,宁采臣的家人“反不疑其鬼,疑为仙”。1987年,由此改编的香港电影《倩女幽魂》上映,张国荣和王祖贤将这个故事演绎得既惊悚又浪漫,给传统赋予了全新的现代意味。
绝大多数观众们似乎只注意到了剧中人物之间的荡气回肠的爱情,有意无意中也把聂小倩看作是一个人而非鬼,几乎不会把这个浪漫的故事和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冥婚”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