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爱手工』做一个生活家

文|朱老板
来源|大蛋疼家朱老板(ID:dadantengjia)
我曾经很多次想写写我的父亲,我那又爱又恨的父亲。中式家庭关系中,父子之间的感情永远是不那么直接透明的,我相信很多八零后和我一样,从出生到现在,没有对父亲或者母亲说过一次“我爱你”。我即使只想想这句话,都觉得脸上发麻,这就是我们从小被压抑的感情。
我的父亲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为了把他们拉扯成人,他小学没念完就上山干活,然后当兵,然后兵转民成为了工人。他空有一手秀气的钢笔字但没有任何文凭,却把叔叔姑姑们培养成了大学生,也算是不负青春。借着年幼学徒做木工和电工的基础,他在车间能制图能做零件,不知道算是哪门子的举一反三,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都能修理,而后又不知道在哪学了修表,竟然也就成了厂区里知名的钟表匠,按照现在的话来说,我这跨界原来也是有遗传的。
小时候每每听母亲说到父亲的经历,她神情中总是带着崇拜和骄傲。当邻居同事们上门有事相求找万师傅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的表情——那些人都不叫父亲朱师傅,他们叫他万能的朱师傅,简称万师傅。
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位矮矮的男人年轻时如何风光,他34岁才有了我,我记事时他已经几乎没了头发,我记事时,他就是那副低着头专心致志摆弄手表的样子,每一个动作都细微得仿佛静止。
小时候我们家中,有一个一米半高的杂物柜。柜顶的面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闹钟,杂物柜的最下面第一个抽屉里,满满当当全是手表和怀表。这些各种形状各种大小的东西都有一个共性:都是坏的,都在排着队等着父亲修理,都在等着他把零件买来换上。他修表进程不紧不慢,修一块,休息一两礼拜,再研究下一块。邻居们隔三差五会敲门来打听他家的那块表修得怎么样了,父亲总是回答说差的那个零件得下次进城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也不是说他从来没修好表,那些一旦修好的,他早就第一时间给人家送上门去了,不会等到上门来打听。
父亲一周六天上班,晚上若有心情便对着台灯戴上单眼放大镜,把手表零件一个个拆下来在旁边的白纸上摆放整齐。碰上我看完动画片在旁边凑热闹,他就会一边用细小的镊子拨弄那些零件,一边告诉我它们都叫什么名字,太多的名词我根本不可能记住,现在唯一记得的就是一个叫做“骑马叉”的奇怪零件(学名擒纵叉)。第一次看到那么袖珍的金属零件时我欣喜若狂,我问他这么小的东西怎么可能用他那么粗的手拆开修好又装上,他说手表虽然精密,但也是人手工造的,要把工作做出色,就要靠细致和耐心,急是急不出好东西来的,欲速则不达。那时我还在读学前班,他又突然问我明不明白时间是什么,我想了很久没有答案,那晚我想到一个人的时间用完了会是怎么样而想到彻夜难眠。关于时间的真正的答案,让我一直想到了今天,想到自己毕生的时间已经用掉了一半。
父亲曾经尝试过教我怎么修表,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戴不上他那奇特的单眼放大镜。而且我正处于好动的年纪,不把他满桌的零件都掀了已经算是运气。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看着他从那些外观各不相同的表壳里倒出圆形的机芯、取出长得都差不多的那些发条和零件们。那时候起我知道了梅花、海鸥、上海、北京这些手表品牌,也知道原来卡西欧除了做计算器还做手表。再后来我戴了一只同学的卡西欧电子表回家,父亲把玩了很久,说,时代变了,他的手艺要废了。
父亲修表从来都不赚钱,我印象中价格贵或便宜的零件他都没收过人家的钱,进城的路费也从来都是自己掏。他在享受着把一件精致的东西从坏变好的过程,也在挑战一个普通机械工人的极限人生价值。很多人知道感恩,既然不收钱,那就送点鸡鸭粮油或者水果挂历上门来,于是我家总有很多取之不尽的吃的用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占便宜上瘾,一直到现在我父亲年近七旬,还拉着他当免费劳动力上门做木工。对于这样的情况母亲总是抱怨,而父亲笑笑说,反正在家也是闲着,还能动,就当锻炼。
后来我去城里读高中,住校,每周一早上要5点起床搭第一趟班车进市区才不会迟到。于是那段日子,每周日他都摸出一台闹钟开始修,修好测试成功然后定上5点闹铃。而这台闹钟要么他马上给主人送回去,要么就坚持不了一天又坏了。于是再当我下一次回家过周末时,他在修的又是另一台闹钟了。总之父亲会确保我周一早上5点能醒来,即使有时候忙到深夜我和母亲都已经睡去。
很多年后我工作了,父亲的视力也急剧下降,戴着放大镜也不能修表了。他日益变得顽固,我翅膀也硬到能够养家,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面对面说话总是不太客气。我第一次去日本给他买了一只西铁城回来,他面露不悦怪我乱花钱,但是母亲偷偷告诉我其实他视作至宝。我把旧的笔记本电脑带回家里给他打扑克和ZUMA。他让我把电脑拆开给他看看,他以修电视机的姿态看了一会,然后直摇头,让我把盖子盖上,别少了螺钉。
前两年父母亲来北京我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我初中毕业之后我们一起相处的最长一段时间。父亲不认识我常戴的那只万宝龙,但是我的索尼手表他关切地看我操作了很久,我留意到他的眼神就像个孩子,而让我很内疚的是当时我居然有些不耐烦。有天我下班回家,他兴高采烈地和我说起苹果手表,看电视新闻看到的,问我苹果做手表会做成什么样。我告诉他,那就是接打电话的玩具而已,他说太高级了,现在科技太发达了。
作为一位钟表匠,父亲对手表的价值判断和我们几乎相反。在他眼中,电子产品似乎更有价值,因为他不懂,不会拆不会修,看不懂英文说明,所以足够高深。而我们看来价值连城的那些传统机械手表对他来说就那么回事,多少个零件,怎么运转,他明明白白,一点都不神秘。当然我没有和他提起过陀飞轮这种高级东西的存在,他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无论如何,我不想拿这些去打击他自认为了不起的专业领域。
他辉煌在他的时间,那个没有手机可以看时间、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他是一家之主是弟弟妹妹的大哥是邻里间的万事通;而我光鲜在我的时间,黑科技互联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都集中在一条光纤上,视线离开屏幕片刻便会错失无数重要信息。他可以从容淡定地面对那一桌子充满奥妙的零件游刃有余,而我面对讯息万变的世界惶恐不安。曾经我对世界充满好奇时,他会耐心地告诉我一切并且启发我去思考更多,而如今他对世界仍然好奇时我却不能够以同样的心境去教会他。
等到若干年后,我有一天也终于会成为父亲,再等时间过去,我的孩子长大到能和我交流,再等到我成为他眼中的老古董时,我会明白这一切。虽然我早已千百次的去假设这样的场景,并且千百次地明白过了。
那天我站在布拉格广场的天文钟前,抬头看着错综复杂的表盘结构,暗自琢磨其内部是怎样的设计。准点报时,耶稣十二门徒穿行而过,我只想到了一个人。
答应我,你们谁都不要让他知道,我写了这么一篇东西。
-End-
.最后2天时间,三两好友不在一起但可以共处一堂,60万元助学金等你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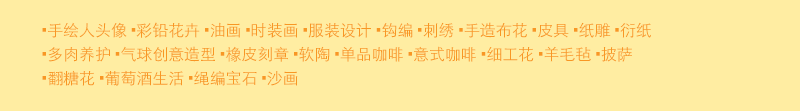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好课程快来报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