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本平台后,每天为您挖掘8篇历史史事


在沈陽尋找張學良的痕跡很容易,張氏帥府、同澤女中、東北大學、九壹八紀念館……壹百多年前出生在這裏的少帥,圍繞他的種種功過評價、花邊新聞,依然被人們耳熟能詳。他所生活過的地方,變成公交站名、壹日遊目的地,融入在沈陽市民每日的生活之中。最新的壹處是東北講武堂,2015年5月18日向公眾開放。
這個新開的博物館只有壹排平房。夾在沈陽東西快速幹線、龍之夢大酒店的摩天大樓之中,四周所有的建築都比這排房子高,對面是老龍口酒博物館,空氣中常常彌漫著濃稠的酒糟味兒。
12年前,這裏還是沈陽中捷友誼廠的舊址,整個地塊被房地產公司買下,老工廠動遷,所有的廠房都扒了,唯獨剩下最後臨街的這壹排。
原因是房頂上方有壹條高壓線,沒法在這建新房子。剩下的這壹排老房子,即便是在中捷友誼廠的歷史上,也說不明白到底是做過醫務室,倉庫還是幼兒園,就在擱置狀態下,本地學者考據出,這個破破爛爛的老房子,竟然是東北講武堂的舊址。

東北講武堂始建於1907年,是清末新政的產物。由遼吉黑三省出錢,培養新式軍隊,清朝覆滅後壹度停辦。1919年,作為東三省巡閱使的張作霖恢復了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此時國家正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東北三省已處在半獨立狀態,張作霖興辦這個軍隊學堂,是為了奉軍輸送軍事人才。
第壹期最有名的學生,必是張作霖18歲的長子張學良。張學良少時頑劣,家裏請了兩任先生都辭館而去。在東北講武堂是他第壹次認真接受系統教育,在這裏,炮兵科學生張學良結識了戰術教官郭松齡,兩個人惺惺相惜,草蛇灰線,張學良此後壹生的命運也由此而起。
郭松齡是沈陽本地人,1883年在東郊的漁樵寨村出生。來講武堂之前,他已經在國內輾轉過四川、北京、廣州等地,他是同盟會會員,見證過四川的革命起義,也投奔過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屢屢見證革命的挫折後,他回到了奉天。
已接受過革命教育,帶有開放思想的郭松齡,明顯與其他奉軍軍官有涇渭之別。國民黨著名黨務專家齊世英年輕時追隨過郭松齡,在《齊世英口述自傳》中,他回憶郭松齡“體格修長而健壯,經常著軍服,好讀書,生活嚴肅,思想前進,治軍甚嚴,恒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不近煙酒,不貪汙,不受饋贈,亦不治生產。”

郭松龄
這也是諸多史料中對郭松齡最常見的評價,因為性情嚴肅,從不含糊,如同日本人作風,人們背後又叫他“郭鬼子”。講武堂剛剛開課,其他教官都因張學良的身份,對他極度恭敬,唯有郭松齡依舊異常嚴格。
張學良也確是矚目,入校頭壹個月,他就考了個第壹,此後屢拔頭籌。成績好得甚至鬧過風波:有學院認為教官們偏袒大帥的兒子,跟他勾結作弊。小道消息傳的沸沸揚揚。最後是教務長專門出面,當眾調換座位,給學生們出了四道考題。
當年的講武堂,學生文化素質都極低,有些學員甚至從始至終大字兒不識壹個,畢業要靠口述答卷。這當然不能跟家中有私塾、又在青年會學過英語的張學良相比,直到暮年,張學良還自信能背出講武堂裏的要緊功課,更不要提剛剛十八九歲的少年時期。張學良所在的教育班有壹百多名學生,那壹次,只有張學良壹個人完整地答出了四道考題,且全部答對了。
“本來大家還沒註意我、特別關註我,這麽壹來,我在講武堂,在同學之中,在教官之中,就引人矚目了。我就這麽樣同郭松齡結成了朋友,這郭松齡也看中我了。”張學良說。
所有人都明白,有老帥的庇護,張學良未來必將在東北擔當重任。在進講武堂之前,父子倆打賭是用自家的官位做籌碼的——張作霖激勵兒子,如果能堅持到畢業,“回來我就給妳當營長。”
此時的東三省姓張,張作霖是不折不扣的“東北王”,他掌握著軍權和財權,手下大部分是奉天人,有的是他的結義兄弟,有的是他的被保護人,張作霖幾乎對所有下級都有強大的控制能力。
27師師長兼奉天衛隊旅旅長張作相,也是綠林出身,是張作霖的拜把兄弟,他給了張學良人生的第壹個職務。當時張學良還沒畢業,就已經當上衛隊旅的第二團團長,衛隊旅的參謀出缺了、副官出缺了,各種問題,張作相都跟這個19歲的侄子商量。張學良是壹路被推著,火箭壹般的速度跟著張作相向上晉升,畢業時已經接任巡閱使使署衛隊旅旅長:“他是師長,我當旅長,他當督軍,我就當他的師長,直到拿到軍權,我都不知道怎麽拿到的。”
還是黃毛小子的張學良,需要壹個有能力,又有個人魅力的人來輔佐他。張學良看上了郭松齡,對方有學問有見解,身上追求進步的特質與他從小接觸的各路軍官,截然不同。
東北講武堂的第壹期結業教官名錄中沒有郭松齡,還沒等到畢業那壹天,郭松齡已經得到了自己的政治機遇,去衛隊旅當參謀長兼第二團團長去了。
二人的合作很快就引起了外界註意。
東北自從清末開始,因為局勢動蕩,土匪橫行。過去張作霖曾派壹位旅長前去平患,這名旅長驍勇善戰,但抓住土匪就用鍘刀鍘死,很多被迫為匪的農民也被殺害,這使得奉軍與當地矛盾越發激烈。
1920年10月,張學良畢業當年,就領了剿匪的任務。此前郭松齡已經對衛隊旅做了整頓,提升軍隊的訓練、教育和紀律,已經顯露出過人的領導才能。在東北的寒冬戰鬥,難度可想而知。晚年張學良接受電視采訪時還故作神秘地問記者,我們打仗前壹小時不許士兵撒尿,妳知道為什麽嗎?在臺灣出生的記者被問得壹頭霧水,張學良得意地告訴他們,嚴寒中槍栓都凍上了,開打前必須澆壹泡尿把槍栓化開啊!
跟土匪的遊擊隊伍相比,張學良、郭松齡率領的衛隊旅軍裝整齊、軍紀嚴格,軍事實力明顯更強。剿匪鬥爭屢屢得勝。張學良用“剿撫並用”的方法,持續壹年時間,平息了吉林、黑龍江的匪患。
首開得勝,張學良立刻被晉升為陸軍少將,被任命為第三旅旅長,郭松齡成為陸軍第八旅旅長。也從這時候開始,二人在奉軍中的地位壹路上升。

張學良
三旅、八旅是聯合司令部,合成“三八旅”,實際上具體管理都是郭松齡負責。大量東北講武堂的畢業生被吸收進來,郭松齡定期輪訓軍事骨幹,實行精兵主義。老奉軍的軍餉都發給長官,由長官自己決定怎麽發放,報上去100人,戰後即便有傷亡,長官依舊按100個人頭領錢。還有人為了吃空晌,平時不養兵,等到打仗前才現抓人充軍。郭松齡推行軍需獨立,賬目公開,禁止軍需變成長官的私人賬房,這實際是把舊軍閥部隊向正規化的重要改良。多年後蔣介石曾評價,東北有兩件事值得學,壹件是王永江的理財之道,另壹件便是軍需獨立。
張學良和郭松齡壹起經歷了兩次重大戰爭。第壹個是1922年第壹次直奉戰爭,當時奉軍整體素質極差,交戰不到壹周就全線大敗。只有郭松齡指揮的三八旅守住了山海關,讓直系的軍隊無法完成合圍,不能乘勝追擊,否則直軍入關,後續的歷史不知道要怎麽改寫了。
第二個是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張作霖第壹次戰敗後,下令整軍作戰,他擴充了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的規模,並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以整訓部隊。在整理處,張學良擔任了參謀長,但實際上替他操盤的還是郭松齡。
第二次直奉戰爭,郭松齡率兵攻入九門口,俘直軍萬余人,奠定了奉軍的勝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倒戈進京,直系全線崩潰,張作霖最後獲得了勝利,北洋政府也由此進入了張作霖時代。
兩次大戰建奇功,張、郭二人此時已親密無間,惺惺相惜。郭松齡對張學良說過,剛來奉天時,他和太太境遇可憐,在家裏只有兩個茶碗,壹個還是沒把的。“沒有妳呀,我也早就完了!”
張學良也常說“我就是郭茂辰,郭茂辰就是我”,張作霖罵過他壹句話,說:妳除了老婆不跟郭茂辰去睡之外,吃壹個水果,妳都要給他壹塊!
這樣親密的關系,其實掩蓋了二人出身、性格和理想上的差距。張學良需要郭松齡幫助他帶軍打仗,完成自己作為少帥的職責。但在郭松齡這,軍人的職責並不是毫無分辨地接受任務,拼死完成這麽簡單。
當年在同盟會、在孫中山身邊接受的救國思想,與眼下張氏父子日益膨脹的地盤和權力,越發遠了。
張氏帥府,如今是沈陽必去的壹處旅遊景點。春節剛過,帥府壹片熱鬧景象:門口的廣場正舉辦社區的秧歌大賽,穿紅戴綠的老年人們興致勃勃地等著進場比賽。鑼鼓嗩吶聲中,門內帥府遊客絡繹不絕,在大青樓的木樓梯上,人多得要互相側身才能經過。

大青樓是張作霖的辦公室,這是壹座三層羅馬式建築,因為每層的舉架都很高,這座包含觀光平臺和地下室的建築壹共高達37米,與遠處沈陽故宮的鳳凰樓遙遙相對,當年是奉天城內最高的建築。
1922年搬進這幢洋樓的張作霖,也正逐步攀爬至個人權力的巔峰。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整個奉系已經占據了八省三市,黑龍江、吉林、奉天、熱河、河北、山東、江蘇、安徽,以及北京、天津和上海。“以中比西,則此時的奉系地盤較中古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或近代西歐之英、法、德、奧、義、荷、比、西八大列強疆土之總合猶有過之。”歷史學者唐德剛評價:“奉系此時擁有精兵三十七萬人。陸海空軍俱全。訓練、裝備、補給皆舉國無雙。奉張父子之權力,至此可謂登峰造極了。”
然而這壹幢漂亮的大樓,連同其他的四合院、小青樓等高高低低的帥府建築,卻在1925年險些付之壹炬——1925年11月22日,郭松齡揮師反奉,通電要求張作霖下野。反奉軍隊壹路勢如破竹,打到錦州,下壹步即要攻占奉天了。張作霖緊急動員數十輛大卡車,把大帥府的財物壹車壹車運到滿洲鐵路的日本事務所倉庫,往返十多次才運完。張作霖第壹次感覺危險如此逼近,以至於在大帥府四周堆滿木柴和大汽油桶,隨時準備全家撤離,把這些亭臺樓閣壹把火燒掉。
郭松齡突然反奉,後人分析有幾種原因。
其壹,是奉軍中壹直有“老派”、“新派”兩個派系,老派大多是張作霖的結拜兄弟,如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孫烈臣等,大多為綠林響馬出身;新派分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士官”派,和畢業於中國陸軍大學、保定軍官學校的“陸大”派。士官派以楊宇霆為首,陸大派以郭松齡為首。二人分別得張作霖、張學良的寵信,但兩人私下裏卻水火不容。
郭松齡曾給自己下過評語:“魯莽躁切,跋扈侵權。”張學良多年後也回憶到,自己有壹點最看不起郭松齡,“我說他,比女人還小器。”楊宇霆、郭松齡各有性格缺陷,處在政治和軍事的核心位置,自然互相傾軋。
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楊宇霆和親信姜登選分任江蘇、安徽督軍,擠掉了郭松齡的位置。這樣的安排,讓郭松齡開始心懷不滿。
第二種原因,是郭松齡的救國情懷。沈陽學者武育文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研究郭松齡,做過許多郭松齡下屬的口述記錄,他並不認同“利益不均”導致郭松齡反奉的判斷:“郭松齡的思想壹直是想把張學良扶植起來,把東北改造好,變成壹個全國首富之區,不要經常打內戰。”武育文認為,郭松齡壹貫反對武力擴張政策,強烈提出過“退兵出關、保境安民”,並且“堅辭不就”安徽督辦。但張作霖還是抱著舊軍閥的野心,堅決出關,期冀繼續擴大自己的地盤。
在日本觀操時,郭松齡獲知奉軍江浙戰敗消息,並與日本訂立合約,這是促使他與馮玉祥、李景林合作,簽訂密約共同反奉。
張學良多年的信任,和自己政治地位的顯赫,給了郭松齡反奉的自信。從日本回國後,他在天津手握了七萬五千人的精銳部隊,這包含步騎炮工輜各兵種的隊伍,幾乎涵蓋了張氏父子軍隊的精華。就帶著這樣的壹支隊伍,郭松齡起兵,壹路向奉天攻去了。
最難堪的是張學良。
郭松齡的聲明中,要求張作霖下野,懲辦楊宇霆,擁護張學良為司令,改革省政。——人人都知道張學良與郭松齡關系好,很多人以為,讓老帥下野,這是少帥自己的主意。
張學良乘軍艦抵達秦皇島,希望能與郭松齡面談。郭松齡沒有見他,因為壹旦會面,必然無法再幹戈相向。在軍艦上,張學良也眼看著陸上壹輛壹輛的戰車向關內駛去,有人建議用軍艦去轟炸,張學良沒同意——那畢竟都是自己的兵。而在軍艦上,張學良接到了電報,開頭稱呼便是“張漢卿先生閣下”,落款竟是張作霖和王永江,電文讓張學良回奉天主政,這讓張學良羞愧難當,幾欲跳海:連父親都以為自己是叛軍!
12月20日,郭松齡的部隊已經達到了新民市,在巨流河西岸北站。巨流河今稱遼河,是遼寧的母親河,新民、沈陽,隔河相望,隆冬之中河流封凍,已然可輕松渡過。
對岸防守的是張學良的部隊。張學良壹直認為,自己的和父親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自己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少年時,張學良在青年會裏接受過西方理念,民初國內各種新雜誌、海外報紙、新思想也經過青年會不斷塑造著張學良。張學良聽過張伯苓《中國不亡,有我》的演講,終生念念不忘。他之所以願意師從郭松齡,是被他身上愛國救亡、革除積弊的理想所吸引。然而現在,24歲的張學良,還是要效忠於自己的父親。
郭松齡此前告訴過張學良,自己是寧折也不彎。張學良說自己完全不同,是寧彎也不折,這是做人的態度。在冰封的巨流河對岸,張學良又想起了這段對話。他知道老師壹定會哪硬往哪打,堅持正面進攻。只要自己把正面工事做好,再加上宣傳攻勢就壹定能成功。
正在錦州休養的郭軍部隊,確實如同張學良預測。聽見對岸喊話“吃張家飯,不打張家人!”,又接到飛機撒下來的傳單,很多士兵的軍心動搖了,許多講武堂畢業的官兵,尊敬郭松齡,但並沒有那麽高的政治覺悟,他們內心還是相信,自己理應為張氏父子效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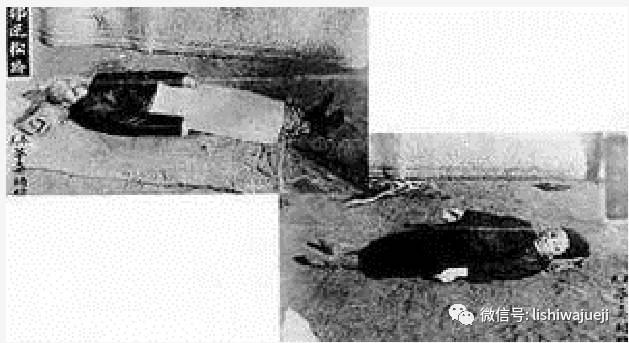
郭松齡在政治上也過於輕率,與他共同簽訂三方合約的李景林、馮玉祥,並不是堅定的盟友,二者居然在後方相互開戰,郭松齡失去了後援,也沒拿到李景林要送的棉衣,天寒地凍之中,軍心徹底散了。郭軍參謀長鄒作華等三人已成奉軍內應,逼迫郭投降,且發出請降通電。張學良、郭松齡的師生情誼、郭松齡的革新思想,如同冰封的巨流河,就此困凍,郭松齡的大勢已去了。
1925年12月25日,郭松齡夫婦逃亡失敗,被張作霖、楊宇霆下令就地槍殺。屍體運回奉天,在小河沿體育場曝屍三日示眾,並將遺體拍成照片各處張貼,傳示東三省各市、各縣,懲壹儆百。
跟隨郭松齡反奉的齊世英,兵敗後壹直藏匿在日本新民屯領事館。反奉失敗,張作霖並沒有吸取任何教訓,齊世英在領事館裏看到,奉軍很快就再次入關:“他們用京奉路運兵,鐵路離新民屯領事館很近,大約五百公尺左右,車子來往的聲音皆可清楚聽到,從傳來的聲音斷定,鐵路和車輛損壞得很厲害,但張作霖還要入關,我想張真不可救藥,我對他的厭惡更深。”
郭松齡的影響,要放在更長遠的時間範圍內顯現。
在反攻郭松齡時,張作霖慌不擇路找了日本關東軍幫忙,定立密約,答應日本方面增築鐵路、獲得商租權等侵害中國國家主權的要求。戰事結束後,張作霖立刻全部反悔,只用500萬現大洋做酬謝。這讓日本方面極度憤怒,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從京返奉,在專列上被日軍埋設於皇姑屯的炸藥炸死,亦起源於這次的分歧。
離開郭松齡的張學良,失去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他坦言自己訓練軍隊的能力並不好,“等到郭松齡叛變了以後,這個東北軍的訓練就沒有那麽好了,尤其是我帶的東北軍更壞。”更重要的是,在五十多年後,“九壹八”事變50周年之際,張學良長嘆:“如果當時郭松齡在,日本人就不敢發動‘九壹八’事變”。
“郭松齡很久之前就在做對日本的防備和部署。郭松齡在的話,奉軍實力強大,日本也不敢貿然進攻。”武育文分析,如果郭松齡還在,奉軍不會宣布不抵抗,起碼要打壹打:“當時日本軍隊就壹萬多人守著鐵路。當時東北軍有二三十萬人,那不是輕而易舉就打回去了嗎?”
武育文認為,張學良此後的東北易幟、西安事變,都帶著郭松齡影響的印跡。之所以張學良沒有變成父親壹樣的舊軍閥,正是郭松齡日常那些潛移默化向張學良灌輸的民族民主思想,在時機成熟時,便顯現了它深遠的影響。
關於郭松齡、張作霖、張學良三人的糾葛,和各自在歷史上的功過評述,也壹直因種種原因不斷變化。研究東北講武堂的遼大教授王鐵軍告訴我們,“近些年來,這三個人,誰的評價變了,對當年歷史的整個判斷都要重新梳理。” 就像張愛玲在以張學良為原型的小說《少帥》中所說:“現代史沒有變成史籍,壹團亂麻,是個危險的題材,決不會在他們的時代筆之於書。真實有壹千種面相。”
郭松齡夫婦的屍體,最後是親友親友代為裝棺,暫昔於小東門外珠林寺。這裏離珠林路上的東北講武堂不遠,是沈陽的壹處知名的寄靈寺。郭氏夫婦的棺槨從1925年壹直寄存到1931年,“九壹八”之後遷出,移昔到老家漁樵寨附近的國公寨胡家墳高崗上。
然而這次移靈,居然還是跟張作霖有關:九壹八事變後,張氏帥府被日本人占領,原來暫昔於自家家廟的張作霖靈柩也移到珠林寺。昔日兵戈相向的郭、張兩人,自然不能存居壹處,張作霖的靈柩在珠林寺也停放了6年,直到1937年在錦州安葬。
如今,壹切都已經蕩然無存了。珠林寺已不復存在,郭松齡夫婦的靈柩幾經遷轉,在1948年才入葬。難得的是,文革期間,人們還記得他反奉的事跡,沒有破壞二人的陵墓。但2013年,郭松齡的長孫郭泰來回鄉尋找時,卻發現墓葬所在之處,早已經是壹片房地產工地。最終只能就地取土引靈,在沈陽東郊的龍泉墓園下葬。這片墓園所處的正是漁樵寨,郭松齡的故鄉。
在龍泉墓園,郭松齡、韓淑秀的墓地,與張學良的“漢卿園”比鄰而立。不過實際上,張學良的墓也是空冢:張學良2001年在美國夏威夷去世,與趙壹荻合葬在當地,沈陽這處是衣冠冢。
張學良晚年時說,父親的死和郭松齡反奉是他壹生最難過的兩件事。八十八年前,巨流河兩岸的那場死別,又終以這種形式重逢。
參考資料:《東北近代史研究》,武育文著;《東北講武堂》王鐵軍著;《張學良口述歷史》張學良口述,唐德剛撰寫;《齊世英口述自傳》齊世英口述 / 沈雲龍等訪問 / 林忠勝記錄;紀錄片《世紀行過:張學良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