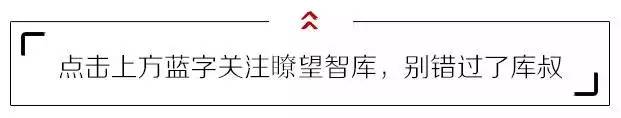

中国政府治理着一个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族群、宗教与文化的“跨体系社会”,这个社会处于急剧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利益正在发生深刻的重组,社会矛盾多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展现出了强大的领导力与执行力,能够较为有效地引导资本的流向,能够对社会实施基本的保护,同时又能掌控自发的社会反向保护运动的力度。离开这个政治体系,我们很难设想中国会从这轮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如此大的收益,同时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那么,中国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做对了什么?
文 |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
摘编自《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在进入政治制度的探讨之前,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保持了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中国国家的“自主性”提供了经济基础,使得中央政府有较为独立的财政收入来源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从而避免了过度依赖社会中的强势经济集团,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经济前提——当然,防止国有经济部门的“封建化”,使其始终保持服务全民的性质,也成为执政党时刻需要面对的挑战。而着眼于中国政治制度自身,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方面的实践具有基础性意义:
1
中共始终保持为一个自觉地为全社会设置战略性愿景的党,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既有社会力量静态利益的党
如果中共光是强调对于各社会群体静态利益的代表,其结果不过是将既有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吸纳到党内,让党内变得如同社会上一样分歧丛生。要解决这些矛盾与冲突,形成政治整合,就需要高瞻远瞩,提出更为远大的战略性愿景,以“未来”驾驭“当下”。在此意义上,“代表性”话语不能脱离“先进性”话语。
“先进”,顾名思义,就是要比别人先走一步,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能够把握这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相对于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言,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就会分出轻重缓急来;“人民”也绝不是一个均质的共同体,其中不同的群体与未来愿景、与执政党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要整合一系列在当下并不同质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以对社会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作为其根基,需要更重视那些当下利益和社会根本利益、长远利益重合度较高的社会群体。
而要增强设置战略性愿景的能力,不仅需要加强对当下世界与中国国内利益格局的认知,更需要对何谓社会主义、何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谓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形成更为成熟的认识,为全党提供未来的方向。“民族复兴”话语当然也能提供一种战略性愿景,对内有一定的感召力,也能与社会主义话语相结合,但在国际上并不具有感召力,因而对其使用尤需谨慎。
执政党的战略愿景设置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整合,综合并提炼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主张,形成更高的论述。如果没有对大方向的把握,各种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就会介入对战略性愿景论述权的争夺,只不过他们所提供的是一种“伪愿景”,是将狭隘的特殊利益打扮成普遍的、长远的利益,比如将“人民”悄然替换为“市场主体”,将“为人民服务”替换为“为市场主体服务”,而且打出的是“深化改革”的旗号,需要细致甄别。
2
在80年代,“党政分开”一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该方向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的机关减少对微观管理事务的介入。在80年代末期,这一思路受到实践检验,被证明具有重大的政治风险。1989年下旬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政分开”已经转向了党政分工而不分开的做法,强调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
为何重新强调“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实践出真知,长期不接触一线的实践,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必然也会发生退化,其权威可能会发生衰减。而处于一线的官员却可通过不断的实践而积累知识与权威。长此以往,“两个中心”的问题就会逐渐凸显。90年代以来,党政分工而不分开,党政交叉任职,这就使得执政党始终能接触第一线的治理实践,保持自身的领导能力。
在全球化时代,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执政党始终掌握着对经济工作尤其是金融工作的领导权。在国家治理事务中,经济工作尤其是金融工作具有高度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同时又与被监管的资本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的金融资本都在呼吁“去监管化”,这种内外互动更为监管带来很大的压力。在这一领域,执政党如果稍微放松领导,就可能形成脱离党的总体战略布局的利益格局,党也会因为领导能力的衰退而无力驾驭经济格局。在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重申了“党管经济”的原则,并将之提到新的高度。
3
执政党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形成一个职业治国者梯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交流布局
在多党竞选体制下,只有执政党才能利用执政优势,将干部放到特定位置上进行锻炼和培养,但这种布局受到“政党轮替”的冲击,其范围和连续性都有限。但在中国,可以“全国一盘棋”进行布局,而且可以着眼长远,将“相马”、“养马”与“赛马”结合在一起。实践中出现了不少亮点:
——要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其履历的全面性非常重要,往往需要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岗位上以及不同类型的地域工作过,获得丰富的治国经验。近年来,对于新录用的公务员也加强了对其“基层经验”的要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的古训。当然,对履历全面性的强调也促生了中高层领导干部送“自己人”下基层“刷履历”的做法,一些地方最终被提拔的仍然是下来“刷履历”的干部,而不是真正优秀的基层干部。我们主张给予土生土长的优秀基层干部顺畅的上升通道。但也要看到,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在基层“刷”过简历的干部比没有“刷”过的干部还是经验丰富一些。对于治国经验的强调,有助于克服浪漫主义和教条主义,培育起审慎的政治德性。
——在过去30多年里,升迁标准的明晰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形成“赛马”效应,发挥干部的积极能动性,促进地方的发展。组织部门在提拔干部时要考虑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年龄、学历、政绩的因素,也要考虑班子的搭配问题,从来都不存在单一的“唯GDP主义”,因此对所谓“GDP锦标赛”不宜过度强调。但对地方主官来说,要获得升迁,至少需要有过得去的经济发展成绩。在中国经济整体高速发展的条件下,“过得去”的标准也随之水涨船高,促使地方主官努力整合与盘活本地各种资源,推动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我们看一看每年的“中国百强县”榜单,听一听这一“俱乐部”新进成员的故事,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地方主官领导力的重要作用。而这种领导力的发挥,离不开背后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所提供的激励。当然,在全国主体功能分区之后,尤其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GDP增速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不同地区的干部面临的考核标准出现差异。但干部考核标准仍在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差异化带来的是激励设置的进一步精确化。
——针对缺乏骨干人才的区域,中央能够投入资源,进行专门的培养。比如“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这是一个国家定向培养专项招生计划,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民委、财政部、人事部等五部委联合实施。进入该计划的研究生在读期间由财政部提供全额奖学金及一定比例的生活补贴,毕业后原则上回到原籍省份或原单位服务。中央也能从其他区域调入人才来进行帮扶,比如委派对口援藏、援疆干部,这就提供了为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是一种能力建设。这对于中国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十分重要。
4
重视巩固和保持中央权威,同时在地方层面保持着弹性试验的空间
通过上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的汲取能力大大加强,扭转了90年代初出现的“无米下锅”的局面。“财大”才能“气粗”,中央汲取能力的增强巩固了中央的政治权威,对地方的潜在离心倾向形成遏制。财力的增长使得中央政府有可能实施较大的战略布局,比如通过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编织社会安全网,减轻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震荡,等等。
同时,我们能看到,中国在地方层面一直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政策试验。能够在地方上进行政策试点,凭借试验结果来评估政策收益、成本和风险,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点之一。试验成功,则可以推广;试验失败,取消试点即可,不会触动全局。比如说,2002—2012年间,很多地方进行了“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的地方试验,进入试验的干部层次达到了厅局级。但由于效果不理想,十八大之后就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定,不再推广。放心做这种政策试验的前提恰恰是:中央有足够的权威,不必顾虑地方通过某些试验来挑战中央。
5
执政党在社会中仍然保持了广泛的存在
党的组织系统在形式上仍然是完整的,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吸纳社会各界先进人士;连接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既为决策提供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同时也有助于较为准确和迅速地向社会传递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尽管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在组织生活上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形式化、空洞化的现象,但从汶川地震等事例来看,当常态社会秩序崩溃的时候,执政党的基层组织系统还能发挥出其组织与动员能力,在秩序重建中起到重要作用。
总监制:吴亮
监制:夏宇
责任编辑:戴丽丽 李逸博
编务:谢芳
库叔福利
库叔的赠书活动一直都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库叔提供10本《大道之行》赠予留言获赞排名前10的热心读者。
高扬社会主义理念,直面“中国问题”,以贯通中西、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从文明、政治、社会、基层、经济各方面分析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理的优势与问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重重危机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