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是弗里曼·戴森
(Freeman Dyson)
的生日。他今年已经九十三岁,仍在继续写文章、做研究,包括纯数学方面的一些有趣工作。戴森的名字在中国也许已经不陌生。作为杰出的作家,他有广泛的读者。他有好几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处女作《宇宙波澜》甚至有三个译本,而邱显正的译本在2002年荣获了台湾吴大猷学术基金会颁发的首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全方位的无限》、《想象中的世界》、《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反叛的科学家》和《一面多彩的镜子》也先后出版了中译本。想必很多读者都为戴森的文笔所吸引,而对他作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身份却未必很了解。本文将尝试解读这位集科学才能与人文修养于一身的大家。《赛先生》获作者授权连载此文,欲读前文请见
戴森传奇之『英才少年』
、
戴森传奇之『奠基量子电动力学』
、
戴森传奇之『鸟与蛙的妙喻』
。
林开亮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博士,目前任教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
1975年,斯隆基金会邀请戴森写一本科学自传。在考虑如何回复时,戴森想起了老师哈代的话:“年轻人应该证明定理,而老年人应该写书。”于是接受了这一邀请,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这引出了他的处女作《宇宙波澜》,1979年出版。戴森曾说,他的生命是从55岁开始的,因为在那个年纪他写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自那以后,戴森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各占一半。戴森作为作家的名望很快赶超了他作为科学家的名望。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译成中文的书外,颇具影响的还有《生命起源》、《武器与希望》、《从爱神到盖娅》等。因其杰出成就,戴森获得了1996年的享有“诗人科学家”美誉的托马斯奖(Lewis Thomas Prize)
[1]
。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他最重要的著作《宇宙波澜》,该书曾以七种语言被翻译,中译本就有两个。书名“Disturbing the Universe”,取自于诗人艾略特(T. S. Eliot)的名作《普鲁弗拉克的情歌》。据戴森给笔者的回信,书名的含义是:我们未来的活动将改变宇宙的命运。1993年,戴森为邱显正翻译的《宇宙波澜》专门写过一篇很精彩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
[2]
:
本书从浪漫的角度来看科学世界,把科学家的生活比作个人灵魂的航程;它有意略过每个科学家生活、工作所在的机构,以及政治、经济的既定框架。在科学史上,团体与个人是等量齐观的,但大多数历史学家往往侧重于机构与团体的活动。本书特别强调个人,因为我希望写点新鲜而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对科学的浪漫观点虽然并不代表全部的真理,却是真理中不可或缺的重点。
比起美国和欧洲的读者,中国的读者也许更习惯于把科学视为一种集体创作的事业;因此,我也很高兴将我个人的观点介绍给中国读者。如果你不觉得我笔下的故事新奇又陌生,没有发现它与你习惯的思维方式有所差别,那么就枉费了本书写作的初衷了。
本书于十四年前在美国付梓,之后我又陆续为非专业的读者写了四本书,然而《宇宙波澜》仍然是我的最爱。它是我的第一本书,字字发自肺腑,比其他几本书投注了更多的心血和情感。如果我的著作只有一本能流传千古,而我又有权选择哪一本的话,我将毫不犹豫选择这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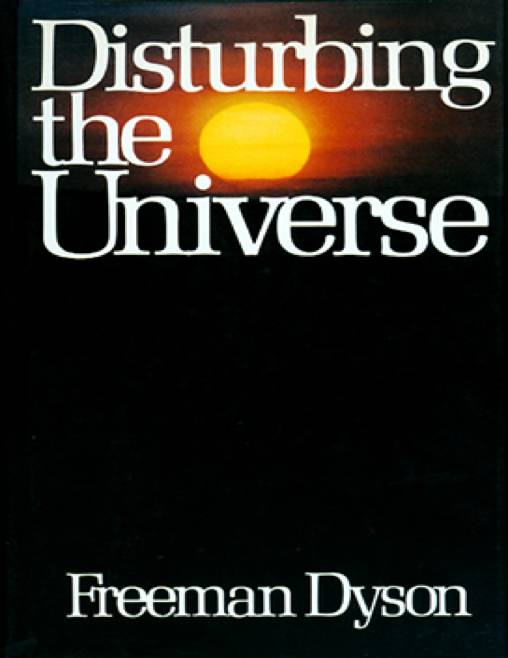
《宇宙波澜》,戴森著
《宇宙波澜》想必能够流传千古。因为戴森兴趣广泛,人生阅历丰富,本书读起来颇有趣味。书中第六章专门回忆了他与费恩曼1948年为期四天的阿尔伯克基驾车之旅,途中与费恩曼的反复讨论,使戴森终于对费恩曼的路径积分方法(也称“对历史求和”)有了深刻的领悟。戴森与费恩曼的结伴同行,起初只是一个偶然的局部事件,但对戴森和费恩曼两个人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深刻改变了二十世纪物理学的整体面貌。戴森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幸运的际遇。(令人费解的是,费恩曼本人似乎忽略了戴森对他的影响,他很少提到戴森。)
这些年来,戴森一直笔耕不辍。除了写书以外,他还写了许多有趣的文章。例如,1955年,二十世纪的大数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永久成员赫尔曼·外尔逝世,戴森为英国的顶级科学刊物《自然》撰写了一篇简短的讣告,转述了外尔作为一个大数学家的价值观
[3]
:
他(外尔)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工作就是努力把真与美统一起来;当我不得不作出抉择时,我常常选择美。”
[4]

Truth and Beauty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徽章
[5]
1988年,费恩曼过世,戴森根据他从前写给双亲的信件编辑了一篇回忆文章《费恩曼在一九四八》(见Dyson 1992)。
近些年来,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些大物理学家相继去世,而新世纪的到来又轮到许多大物理学家的百年诞辰。许多与戴森有过交往的,
例如泡利(1900-1958)、费米(1901-1956)、狄拉克(1902-1984)、奥本海默(1904-1967)、贝特(1906-2005)、特勒(E. Teller,1908-2003)、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1910-2005)、克默尔(1911-1998)、惠勒(J. A. Wheeler,1911-2008)、萨拉姆(1926-1996)等,他都写了回忆文章。
戴森还不时地为《纽约客》与《科学美国人》撰稿,也常常为新出版的各类科学著作写序言和书评,因此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纽约书评》中。2013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森的书评集The Scientist as Rebel的中译本
[6]
。就在最近,戴森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评集Dreams of Earth and Sky
[7]
。近些年来,国内出版了许多优秀的科普书,其实很多都有戴森写的书评,如美国科普作家瑞德
(C. Reid)
的《希尔伯特》
[8]
,格雷克(J. Gleick)的《牛顿传》
[9]
与《信息简史》
[10]
,理论物理学家格林
(B. Greene)
的《宇宙的结构》
[11]
,费恩曼的女儿米雪·费恩曼
(Michelle Feynman)
编辑的《费曼手札》
[12]
,法国数学家埃克朗
(I. Ekeland)
的《最佳可能的世界》
[13]
,英国传记作家法米罗
(G. Farmelo)
的《量子怪杰:保罗·狄拉克传》
[14]
。如果译者能将这些优美的书评一并翻译过来附在中译本中,想必会令读者颇受教益。
作为数学家,戴森的数学能力毋庸置疑。但他并不以数学家的身份特别骄傲。在他看来,有些数学家过于离群索居缺乏人情味了。他之所以后来与妻子胡贝尔离婚,就是因为她是一个数学疯子,沉湎于数学不能自拔,甚至置子女于不顾,而且从来没有被点醒过,不像戴森年少时被母亲点醒那样
[15]
。1958年,戴森与马拉松长跑运动员艾米
(Imme Jung)结婚。戴森共有六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女儿,唯一的儿子乔治(George Dyson)
是著名的科学史家。

左图:戴森
与妻女(乔治缺席的全家福);右图:
乔治·戴森
(图片来源:http://www.achievement.org/autodoc/page/dys0int-2)
戴森的数学生涯与剑桥数学学派特别是哈代有密切关联,正是哈代与赖特合著的《数论导引》引发了戴森对数论长达一生的兴趣。应该指出,虽然戴森学习和吸收新东西的能力很强,但他在大学两年时间里学的数学其实很局限
[16]
。正如戴森在给笔者的信中曾说起的,他的老师哈代和李特尔伍德作为英国的数学领袖甚至阻碍了英国数学的进展:
哈代和李特尔伍德是旧式的数学家,他们虽然活在二十世纪,做的却是十九世纪的数学。他们虽然做出了漂亮的工作,但他们对源于法国和德国的新的抽象思想没有兴趣。结果是,年轻一代的英国数学家,包括我,在一个远离繁荣于法国的新数学的环境下成长。
事实上数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迅猛的发展,然而哈代和李特尔伍德忙于研究经典数学(解析数论与古典分析),导致了英国下一代的数学家没有及时跟上抽象代数与拓扑学兴起的现代数学潮流。在当时的剑桥,只有霍奇是唯一的例外。他不仅跟上了现代数学的步伐,而且就在戴森入学剑桥的前后做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戴森并不为霍奇的讲课所吸引。所有这些,导致戴森对数学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戴森的数学视野和品味也就局限于哈代、李特尔伍德与拉曼纽扬的范围之内。但这些人的工作(解析数论与离散数学)都偏离主流数学太远了。特别是拉曼纽扬的工作,体现的是一种奇异美,简直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拉曼纽扬那里,你根本看不到历史和传统,拉曼纽扬就像是他的同胞诗人泰戈尔
(R. Tagore)
诗句“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中的飞鸟。“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追寻他的足迹是前途渺茫的。这种横空出世的数学确实难以为继。(当然,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是,拉曼纽扬遗失的笔记(Lost Notebook)当时尚未发现。)
戴森虽然早期在数论研究中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他对纯数学中这种曲高和寡的冷清氛围不满意,于是决定离开纯数学而转向应用数学。他在《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
[17]
一书的导言中写道:
在我后来的科学生涯中,我并未忠于哈代的理想。起初我步他的后尘进入了数论领域,并解决了几个数论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优美但无关宏旨。后来,在我作为数论专家工作了三年之后,我决定做应用数学家。我认为,比起继续证明只能引起一小撮数学家感兴趣的定理,理解自然的基本奥秘要令人激动得多。
作为物理学家,在很早的时候,由于费米的提点,戴森认识到,做物理研究不能仅仅靠纯粹的数学演算,更需要物理直觉的指引。
戴森很清楚,他缺乏物理直觉。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功得益于与物理学家的广泛交流,得益于他的数学品味和才能:他以数学家的价值观来做物理。
他在1964年发表于《科学美国人》上的文章《物理科学中的数学》
[18]
中写道:“数学之于物理,不仅是计算现象的工具,更是创造新理论的概念和原理的主要源泉。”有如共鸣,杨振宁先生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见解:“我的大多数物理学同事对数学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崇拜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巧妙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神乎奇迹的是,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19]
但是,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有不同的价值观,戴森的价值观并没有得到物理学家的广泛认同。这与数学家对他的看法恰好形成鲜明对比:数学家不认为戴森的数学工作很重要,但愿意听他的数学见解(例如当代著名数学家阿蒂亚
(M. F. Atiyah)在他的
第五卷《论文选集》序言中就提到了曾从与戴森的交谈中受益);而物理学家认可戴森的物理成就(例如他荣获了1981年的沃尔夫物理学奖),但拒绝他的数学价值观。
戴森在《不合时尚的追求》
[20]
一文中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数学物理学家。他将数学物理这门学科的宗旨理解为,用纯数学的严格风格和方法来理解物理现象;而数学物理学家的目标则是,澄清那些作为物理理论奠基石的概念的精确数学意义。
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数学物理学家,戴森得到了高度认可。在2012年的世界数学物理学家大会上,戴森获得了该领域的最高奖——国际数学物理协会颁发的庞加莱奖(Henri Poincaré Prize)。
然而,不论是作为数学家还是作为物理学家,戴森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唯有作为作家的戴森,才算是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如果要从二十世纪的数学家中挑选出一百位最有成就的数学家,戴森基本不能入围。因此,他年少时想成为二十世纪《数学精英》系列人物之一的梦想势必要落空了。而作为物理学家,虽然他早在二十五岁就名扬四海,但他从来也没有期望自己成为像他的同事杨振宁那样的伟大人物。
一直以来,物理学家好像都对戴森有更高的期许,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教授、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森
(Philip Anderson)
在对谢尔维
(P. F. Schewe)
为戴森所作的传记
[21]
的书评“一个多面手的生涯(Aniconoclast's career)”中写道:“戴森是一个能力超强的人,并且成就很大,然而,如果他术业有专攻,又会是怎样呢?”这大概是在期待戴森成为“刺猬”或“飞鸟”。但应该指出的是,戴森的广泛兴趣与大胆假设,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很能综合的人,人们也期待他成为一个能够总揽全局的人,但其实他首要的身份是数学家,更擅长的是分析和小心求证。
也许戴森在二十世纪的数学界和物理学界不能占有特别高的地位,但作为科学家中的作家,他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戴森曾回复笔者,在写作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哈代,因为他为非数学专业的读者写出了优秀的书籍《一个数学家的辩白》。哈代的写作确实吸引人,这也许是因为他曾经历过数学史上最浪漫的传奇,发现了自学成才的印度数学家拉曼纽扬,所以写作也富有激情。不过,哈代的言论比较极端,一旦绝对化,就会创造出一种奇异的美感和坚不可摧的力量,令读者往往不自觉地信以为真。例如哈代在其辩白中曾写道:
只有少部分数学有用,而即此少部分也较为乏味。“真正”数学家的“真正”数学(无论其为“应用”数学或“纯粹”数学),即费马
(Fermat)、欧拉(Euler)、高斯(Gauss)、阿贝尔(Abel)、黎曼的数
学,几乎全部无用。如能解释真正数学的存在,则应解释为艺术。
这一点哈代有点像他的同胞王尔
德(Oscar Wilde)
,另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天才。又因为哈代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他慧眼识出的天才拉曼纽扬又英年早逝,所以他暮年提笔时,处处洋溢着悲观情绪,这也许在无形中打动了某些读者。但他的有些话是经不住检验的,比如他说“费马、欧拉、高斯、阿贝尔、黎曼的数学几乎全部无用”就错得离谱
[22]
。
对于写作和数学研究,哈代完全是以美为至高法则。他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写道:“美是首要的试金石:丑陋的数学不可见于天日。”可以说哈代是一个“纯”到了极致的数学家,比外尔还要纯。笔者曾在通信中问戴森,真与美二选一,他会选择哪一个。他回复说,不同于哈代和外尔,他只是在做研究时会优先考虑真实,而在讲故事时则会优先考虑美妙。
相对而言,戴森的文字则不时闪现着睿智与幽默,其评判也较中和,对于有可能看起来矛盾的说法,他能通过玻尔的互补性原理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为哲学基础来调和。而且,戴森的视野要比哈代开阔。他早年读到的凡尔纳、托尔斯泰、韦尔
斯(O. Wells)、霍尔丹、赫胥黎(A. Huxley)、奥威尔(G. Orwell)的作品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像那些前辈一样,戴森具有非凡的想象力与洞察力。此外,戴森在写作中常常旁征博引,特别是戏剧和诗歌——这是自小受父母熏陶和中学时代受弗兰克影响的结果,为其作品增色不少。例如,在《宇宙波澜》一书的索引中,你可以看到许多诗人和作家的名字,如奥登(W. H. Auden)、布莱克(W. Blake)、歌德(J. W. von Goethe)、弥尔顿(J. Milton)、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和叶芝(W. B. Yeats)。戴森在《生命起源》中说,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因
为即便他所作的猜想或预言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布莱克的名句(引自A Vision of the Last Judgment)早就让他释然:To be an Error and to be Castout is a part of God’s design
[23]
.
哈代与戴森的共同点,也许可以用培根的名言来概括:“如果没有奇特的奇异性,也就没有与众不同的美。”而如果要指明戴森与哈代的差别,也许我们可以窃取哈代本人的话
[24]
:
假如真的能把我的雕像塑在伦敦广场的纪念碑上的话,我是希望这座碑高耸入云,以至人们见不到雕像呢,还是希望纪念碑矮得可以使人们对雕像一目了然呢?我会选择前者。可以想见,戴森(原文是斯诺
博士(Dr. Snow)
[25]
)会选择后者。
笔者曾经问戴森是否同意后面这个说法?他表示同意。事实上,戴森在《从爱神到盖娅》一书的序言中说
[26]
:“我所有的作品,其目的都是打开一扇窗,让高居科学庙堂之内的专家望一望外面的世界,让身处学术象牙塔之外的普通大众瞄一瞄里面的天地。”他成功了。

2013年戴森在IAS为他举办的90大寿暨加入IAS 60周年庆祝会的留影
戴森的著作不仅给读者以亲切感,更给人以他作为科学家的强烈使命感。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屈原的一句话来评价作为作家的戴森:“其志洁,故其称物芳”。
致谢: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杨振宁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杨先生对初稿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评论。戴森通过邮件对笔者提供了不遗余力的帮助,还
特别为本文提供了照片。作者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还得到了苏珊·希金斯(S. B. Higgins)
女士、江才健先生、陈关荣教授、汤涛教授、丁玖教授、欧阳顺湘教授、葛墨林教授、周坚教授、肖明波教授、张淑娥教授、刘云朋教授、赵振江教授、付晓青教授、崔继峰博士、张海涛博士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这是我当学生时写的第一篇人物传记,定稿后我立刻知道自己能写,到现在仍然引以为傲。特别是,因为它我结识了不少好朋友。戴森是个很可爱的人,他鼓励人不走寻常路。他文笔很好,尤其喜欢对比的手法,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我这篇文章,有意无意在拿他与杨振宁先生做比较,因为这篇文章本身就是源于这样的想法,他们在某些方面是有一拼的。杨先生告诉我,他自认为数学能力不如戴森。戴森在某些场合也承认,自己缺乏物理直觉。他们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十几年的同事。遗憾的是,我这里没有他们的合影。
本文初稿曾以《弗里曼·戴森:科学家与作家的一生》为题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3期,也曾作为附录重印于戴森的中译本著作《一面多彩的镜子》(肖明波、杨光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后来又刊登于香港《数学文化》2015年第3期和台湾《数理人文》2016年第9期。感谢一些热心读者和朋友(包括戴森本人根据英文版)的反馈,初稿中的某些错误现在得到了更正。
[1] Lewis Thomas ,1913-1993,美国医学家,生物学家,科普作家。他的许多著作都被译成中文,如《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等。关于Lewis Thomas Prize可进入维基百科获得详尽了解。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两位数学家首次摘取了这一桂冠,他们分别是斯图尔特(Ian Stewart)和斯托加茨(StevenStrogatz)。
[2] 戴森1998.
[3] Dyson 1956. “Obituary : Hermann Weyl”, Nature 177: 457-458. 戴森在给《自然》投稿时曾注明:“I asked four people in Princeton who are better qualified than I am to write it, all of them excused themselves, and so I ended by writing it myself.”(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 Faculty Files / Box 37 /Weyl, Hermann 1946-1993.)
[4] 无独有偶,中国作家汪曾祺(1920-1997)曾表达过一个类似的见解: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5] 左边的裸女代表Truth(大概是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右边穿衣服的代表Beauty。整个设计受到了济慈(John Keats)名诗《希腊古瓮颂》的启发(余光中译):
美者真,真者美——此即尔等
在人世所共知,所应共知。
[6] 戴森2013. 《反叛的科学家》. 肖明波、杨光松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7] Dyson 2015b. Dreams of Earth and Sky. New York Review Books. 中译本《天地之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8] 袁向东、李文林译.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7年. 戴森的书评见Science 27 November 1970: Vol. 170no. 3961 pp. 965-966.
[9] 吴铮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年. 戴森的书评有中译文《老牛顿,新印象》,收入戴森2013.
[10] 高博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年. 戴森的书评How We Know, The New YorkReview of Books, March 10, 2011. 收入Dyson 2015b.
[11] 刘茗引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年. 戴森的书评有中译文《弦上的世界》,收入戴森2013.
[12] 叶伟文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年. 戴森的书评有中译文《智者》,收入戴森2013.
[13] 冯国苹、张端智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年. 戴森的书评Writing Nature's Greatest Book, Th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19, 2006. 收入Dyson 2015b.
[14] 兰梅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年. 戴森的书评 Silent Quantum Geniu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25, 2010. 收入Dyson 2015b.
[15] D. J. Albers, “Freeman Dyson: Mathematician, Physicist, and Writer”,The College Mathematics Journal, Vol.25, No. 1 (1994), pp. 3-21.
[16] 一个明证可见戴森的论文“The Threefold Way. Algebraic Structure of Symmetry Groups and Ensembles in Quantum Mechanics”(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3, No. 6, 1962, pp.1199-1215),文中指出“三重方式”根源于经典的Frobenius定理(实数域上的可除代数只有三种:实数、复数和四元数),而这一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教授伯格曼向他指出的。Frobenius定理是抽象代数中的基本结果,可惜戴森在剑桥上本科时对此闻所未闻。
[17] 有两个中译本《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科学革命的工具》. 覃方明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21世纪三事——人文与科技必须展开的三章对话》,席玉苹译. 台湾: 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9.
[18] 戴森2007. 《物理科学中的数学》,收入克莱因(M. Klein)编《现代世界中的数学》,636-656页. 齐民友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C. N. Yang 1983.
[20] 戴森 1981. “Unfashionable pursuits”,有中译文《不合时尚的追求》.袁向东译.《数学译林》1985年第2期. 电子版可见清华大学数学系周坚教授的个人主页http://faculty.math.tsinghua.edu.cn/~jzhou/Buhe.htm
[21] P. F. Schewe 2013. Maverick Genius: The Pioneering Odyssey of Freeman Dyson. Thomas Dunne Books.
[22] 特别的,哈代的得意门生、日后成为MIT数学系主任的莱文森(Norman Levinson)曾撰文反驳,见“Coding Theory: A Counter example to G. H. Hardy’s Conception of Applied Mathematics,”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77 (1970): 249--258.
[23] 铸成错误并被摈弃,亦属上苍精心设计。
[24] 哈代2007.
[25] 斯诺(C. P. Snow,1905-1980),英国化学家兼作家,尤以1959年所作的《两种文化》的演讲而著称。
[26] Dyson 1992.
投稿、授权等请联系:
iscientists@126.com
您可回复"年份+月份"(如201510),
获取指定年月文章,
或返回主页点击子菜单获取或搜索往期文章。
赛先生
由百人传媒投资和创办,
文小刚、刘克峰、颜宁
三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担任主编,告诉你正在发生的科学。
上帝忘了给我们翅膀,于是,科学家带领我们飞翔。
微信号:
iscientists

▲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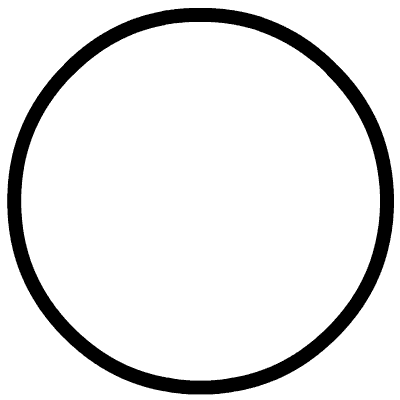 点击“
阅读原文
”购买科学好书!
点击“
阅读原文
”购买科学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