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词语秘境,在现实中又被文学圈规训的作家,潜意识里疏远大众,连文字也在刻意求险求生僻,求一种专业的腔调。但和乔伊斯这类人不同的是,它不是浑然天成的,噼里啪啦怼天怼地的,不是有自己独特的辨识度的,它是媚雅的,像一个急着要老师表扬的孩子,“看,我有多高级!”于是,出来了许许多多仿科塔萨尔、仿博尔赫斯、仿马尔克斯、仿卡尔维诺等,但作者自己的灵魂消失了,作者只能通过已经被认可的权威话语来确立自己的归属感,可这恰恰是他内心不安的一种体现。如今,当我回顾那些天才作家的代表作,他们的作品,哪怕只是随手翻一页,都给予我“王炸”的气息,让我知道,它是不同的,是捕捉到人性微暗深处的火。这是被教养出来的媚雅者所不具备的,读后者的小说,大多是“你很努力,很高级,但无法触碰我的心灵”。

在一期《十三邀》
里
,许知远和张艺谋谈起了文学和影视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相比起八十年代,今天的文学明显衰落了,尤其是长篇小说,年轻一代小说家的长篇创作力似乎远不如莫言、贾平凹、余华、陈忠实这一拨人。
这并不只是许知远和张艺谋的忧虑,八月初《腾讯
·大家》的文章《作家的病,别让时代背锅》也谈到了文学在今天的尴尬,而笔者在和出版社编辑聊天时,他们也很担心,说这一拨老作家写不动了,现在的青年人能接班吗?现在的小说数量虽然越来越多,可像《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这样浑厚有力的大部头,怎么就越来越少了呢?
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作家能力的下滑,更重要的原因
在于
:今天,浇灌厚重长篇的土壤已经越来越稀薄,在一个史诗消亡的年代,创作厚重长篇成为
“不合时宜之事”。
今天的长篇其实很多
但多是预备影视开发的商业产品
严肃文学期刊的编辑感慨长篇难产,但如果把网络文学纳入考虑版图,长篇的创作数量其实有增无减。在各大网络文学平台,写手们的小说动辄百万,一次穿越都能写上几百章,写作字数,连向来以创作高产的小说家张炜都会汗颜。但是,为什么这一批网络小说除了个别精品,大部分都成为速朽的爽文,而缺乏如《静静的顿河》《大师与玛格丽特》般经久耐磨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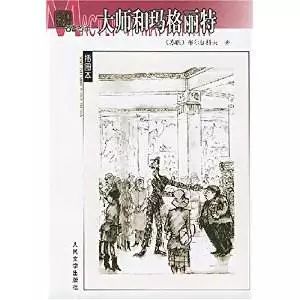
作者:
[苏联]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原作名: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译者:
钱诚
这和网文的生产规律有关。一般网文写手在更新前,都会签一个合同,规定每天至少更新多少字,如果没有达到更新量会有违约风险。同时,由于网文世界过于庞杂,又以市场反应为第一参考,以影视改编为理想愿景,作者在写作时,既要不加节制地更新,又要处处考虑大众喜好、影视趣味,所以我们会看到,成百上千的网文,扑面而来
“快找我改编”的气息,它们本质上是定位明确的商品,臣服于快速消费的逻辑,要这些作者生产出厚重长篇,便如同缘木求鱼。
不过说句公道话,网络文学才发展了二十年左右,现在就苛责
它
,有些强人所难。许多人感慨的,更多还是严肃文学圈子(虽然如此划分,有些粗线条)的青年作家,难以产出厚重长篇。近几年,有这种气势的《繁花》《山本》等作品,创作者金宇澄、贾平凹等,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家,而青年作家的长篇尝试,如《北鸢》《茧》等,固然是突破自我的写作尝试,但放到整个文学谱系里,它们的力量和深度都是不够的。《北鸢》有对《红楼梦》和民国世情小说的模仿,《茧》比张悦然早期的小说更有历史感,但总体深度并未超越八十年代的伤痕小说。与长篇相比,
中
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写作反而大步向前,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弋舟的《随园》《出警》、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有孙频、张怡微、沈诞琦、文珍等人的中短篇,都各有各的特色。他们在技巧上并不逊色于前辈,甚至在知识水平上超越了前辈,但是,这似乎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创作出更加厚重的作品。他们或是如张爱玲般,主动选择逃离厚重,书写细微的日常生活;或是尝试
厚重长篇
却力有不逮,总而言之,从他们的写作道路来看,今天的青年作家无法产出厚重长篇,与小说家的写作技巧问题关系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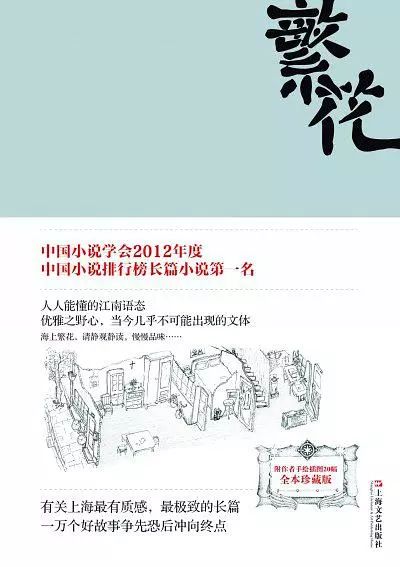
作者:
金宇澄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3-3-1
反而是整个环境
,
对书写厚重长篇的小说家太不友好,才让很多青年人望而却步。写作长篇小说,尤其是有史诗气质的大部头,是一件消耗很大的事情,需要作家有足够长的沉淀,但
“沉淀”是一个在当代很难得的事情,不只是因为人心的浮躁,还因为当代生活的紊乱和密集。乡村消亡,而城市人的生活却被压榨到分分秒秒,手机、电脑、多媒体、广场屏幕,时刻滚动的热点,随时到来的工作安排,让作者们很难空出一段足够的沉淀期,来完成厚重长篇。即便是被作协供养的专职作家,他也要面临大大小小的应酬。作者们周旋其中,只觉疲惫不堪,或者虚无乏力,急于缩进自己的小世界避难,所谓的“千千万万人”之关怀,便无暇顾及。
更世俗的原因是,写作厚重长篇给今天写作者的回报过于低廉。如果不是在圈内掌握大社资源,被评论家和出版社护着捧着的大作家,你去写长篇,大概率石沉大海,无人问津。长篇作为一项漫长的艺术,它不像抖音、快手乃至公众号热点文章,能够瞬间高密度的给予接受者快感,它往往要有漫长的铺垫,才能迎来一个击中内心深处的高潮点,这对当代读者来说难以忍受,如果没有社会事件加持(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或奖项、权威的站台,长篇几乎沦为一个人的苦旅。
由于生存的艰难,原本热爱文学的青年作者,将不得不把他们未完成的大部头搁在一边,转而生产出轻盈而适合都市人阅读的文字。我们的周遭不缺乏小村上春树、小张爱玲甚至小安妮宝贝,但你很少听说有人来模仿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布尔加科夫来写东西,《追忆似水年华》如果交给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出版中介,对方将给普鲁斯特发一个黑人问号,然后告诉他:
“你开头废话那么多,意义是什么?”所以,由于市场缩减,以及众所周知的政治的原因,书写厚重长篇的青年作者大幅减少了。留下的,只是一些受政府补贴的老作家,或者对权威奖项投其所好的作者,对伟大作品粗糙模仿。
说书人困境
长篇的故事价值被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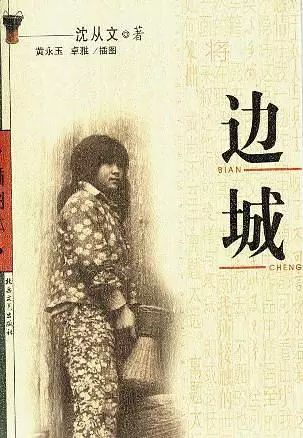
作者:
沈从文
/
黄永玉
/
绘者 卓雅
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02-4
厚重长篇的消亡,也和
“说书人”的危机有关。
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说书人从远方而来,对故人娓娓道来异邦的传说。猎奇、新颖、直击人性,这是故事原始的魅力,也是贩夫走卒购买故事的动力,因为这些故事他们闻所未闻,这些想象慰藉了他们干枯的内心,像《一千零一夜》《聊斋志异》等,都是以
“说书人”的形式展开的,乃至离我们近一些的沈从文,大众为什么爱看他的小说?除了文学性之外,隐藏于迷雾中的湘西世界——它本身的神秘和异质性也成为读者想象的对象,而沈从文幸运地了解这一神秘地域的肌理纹路,他也像远古的说书人一般,把新奇故事说给都市人听。
但网络席卷了一切。
耶路撒冷出现恐怖袭击、美国校园爆发枪击案、特朗普和艳星有染、机长的生死抉择
......这些惊奇见闻都可以在一瞬之间通过网络传到你的眼前,视频、新闻乃至段子,大众再不必等待说书人的姗姗来迟。视频的冲击力比漫长的小说、戏剧等更直接,也更节省时间成本,
长篇原本意味着一个新奇世界,赋予读者未知的快感。但如今,网络大大消解了异邦的神秘,久而久之钝化了公众对
“故事”的向往,说书人自然走在危险的十字路口。
王国维说
: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传统的文学媒介已不符合当下的要求,而浸润于传统写作培育模式中的作者还无法真正体察今天。
菲茨杰拉德说
:
“一个作家应当为他那一代青年执笔,而将作品留给下一代评论家和未来的中学校长们去评说。”
但由于权威评论席还掌握在上一代人手里,投身纯文学的青年作者为了出头,为了占据本就少得可怜的版面,只能去迎合前网络时代的审美趣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老成悲悯的农村娃儿。
久而久之,文学圈和大众越来越疏远了,和前沿的知识也疏远了。许多作家文学知识深厚,在历史、政治、哲学、经济、法学、人类学等领悟的积累却十分浅薄,文学圈子愈发熟练于关起门来过日子,清净,和睦,岁月静好
。
一个桎梏是,深陷词语秘境,在现实中又被文学圈规训的作家,潜意识里疏远大众,连文字也在刻意求险求生僻,求一种专业的腔调。但和乔伊斯这类人不同的是,它不是浑然天成的,噼里啪啦怼天怼地的,不是有自己独特的辨识度的,它是媚雅的,像一个急着要老师表扬的孩子,
“看,我有多高级!”于是,出来了许许多多仿科塔萨尔、仿博尔赫斯、仿马尔克斯、仿卡尔维诺等,但作者自己的灵魂消失了,作者只能通过已经被认可的权威话语来确立自己的归属感,可这恰恰是他内心不安的一种体现。如今,当我回顾那些天才作家的代表作,他们的作品,哪怕只是随手翻一页,都给予我“王炸”的气息,让我知道,它是不同的,是捕捉到人性微暗深处的火。这是被教养出来的媚雅者所不具备的,读后者的小说,大多是“你很努力,很高级,但无法触碰我的心灵”。
同质化生活
家族与历史感的消亡
和莫言、余华、贾平凹、陈忠实那一代作家相比,成长了市场经济时期的作家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接受国际写作班的熏陶,甚至熟读西方乃至南美的前沿著作,但他们生活的质感和丰富度是不如上一代人的。
上一代作家经历了土改、文革、改革开放,是共和国巨变再巨变的见证者,且他们大多生长于乡土社会,对中国的农耕文化和家庭关系较为了解,这些都成为他们丰富的写作素材。和年轻作家相比,他们在理论上也许略逊一筹,但在讲故事上,他们有熟练的本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大多出生于都市、原子化家庭的年轻作家,明显陷入了
“写作同质化”的困境。一样的都市,一样的教育,一样的观看媒介,一样的热点,限制了作者的想象力。远方曾是解救的温床,慰藉说书人的行囊,但发达的网络宣告它的破产。一次次的游记,运来的不再是萨哈林和古拉格,而是中产阶级的诗和远方,治愈无聊上班生活的迷魂汤。
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引经据典,可以写出一些精美的小句子,但在更大的命题前,他们不免捉襟见肘。当然,有天才作家可以凭借想象力突围,但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举世寥寥,从整体的角度而言,同质化生活对作家的磨损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