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机器人可能正面临众口难调的瓶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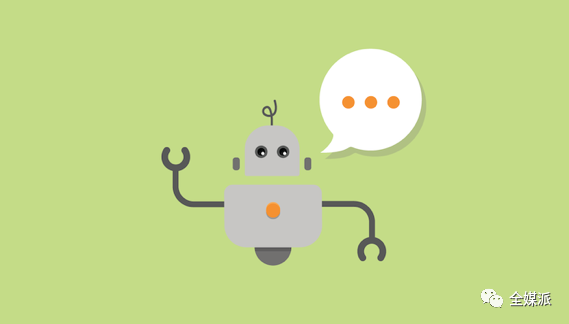
看衰的人认为,两年来也没见大的技术突破,文字会话式的应用很快会被更智能的方式取代。而编辑部里的各位却是对聊天机器人抱有最大热情的一群人,从媒体到平台,资讯领域一直没有停止这方面的尝试。
这是不是对技术的一厢情愿?媒体和chatbot的缘分如何?知名数字媒体Digiday发布了一份“趋势
报告”,遍访172位媒体和市场营销公司的高层,得出五大重点发现:
①大约47%的媒体人和31%的营销人使用聊天机器人。
②52%的媒体人和营销人表示,聊天机器人主要被定位为一种资讯来源。
③社交平台如Facebook Messenger是聊天机器人的“天然栖息地”,有88%的媒体人和营销人将其布局于这一平台。
④据营销人士反馈,聊天机器人在提供对话支持前,在消费者互动中只占了不到20%的比例。
⑤如今,聊天需求的满足比例以及发起聊天的次数,成为衡量聊天机器人表现的主要方式。
全媒派(quanmeipai)将结合该调研报告与媒体实践案例,一同窥探聊天机器人的现状与未来。
Q1:聊天机器人
真的达到
“会聊天”的目的了吗?
深度学习、情感交互、记忆推理…聊天机器人的前沿发展有不少智能化的尝试,而媒体领域内的聊天机器人还正走在试验其工具性和个性化程度的进化之路上。
懒人方法论:获取资讯的成本越来越低
有52%的媒体和营销专家表示,聊天机器人主要是被当做一种资讯来源。

IPG媒体实验室的战略总监Adam Simon表示,“我们正致力于
推动品牌关注实用性
,也就是那些消费者会定期想要使用的东西。”Fridman赞同这种看法,“任何能让我的生活更加便利的事物,我都很乐意授权为之。有了聊天机器人,生活里都是在下达指令。”
金融时报的FT实验室两年前就早早在尝试,他们打造了一个具有网站搜索功能的聊天机器人。“当时我们还不得不向用户解释Slack是什么,”FT实验室负责人Chris Gathercole说道,“这个项目最终失去了动力,因为我们尝试得太早了。”
不过Gathercole对于聊天机器人的未来还是很乐观的,尤其是对
新兴的语音市场
,“这有利于支持对话交流。”
然而现实是,远远没有想象的智能
作为一项读者服务,聊天机器人通常提供个性化内容,例如每日摘要或是特定主题的新闻报道。最初,这意味着聊天机器人基本上和RSS订阅差不多,Tech Crunch、《卫报》都有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不过,近来编辑室都卯足了劲,开发更厉害的聊天机器人。
2016年的美国大选正好成为了媒体实验的温床。其中《纽约时报》大展身手,为了报道最后19天的战况,
它在Facebook Messenger上打造了一款聊天机器人,专门推送时政记者Nick Confessore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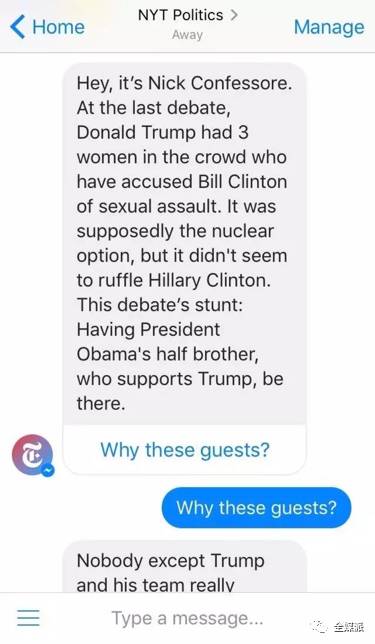
编辑团队每天撰写“选择自己的冒险”风格的脚本,来模拟与Confessore的对话。文本提示会引导用户进行一个预先结构化的对话。
“这是全自动化的,但也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纽约时报创新项目Story[X]的成员Andrew Phelps说道,“所以人们仍是真的认同Nick记者,并且感觉享受到了一种个性化的体验。”
像这样的聊天机器人在媒体领域比比皆是,
受访者中大约有47%的媒体人使用过。
然而这些聊天机器人还远远称不上“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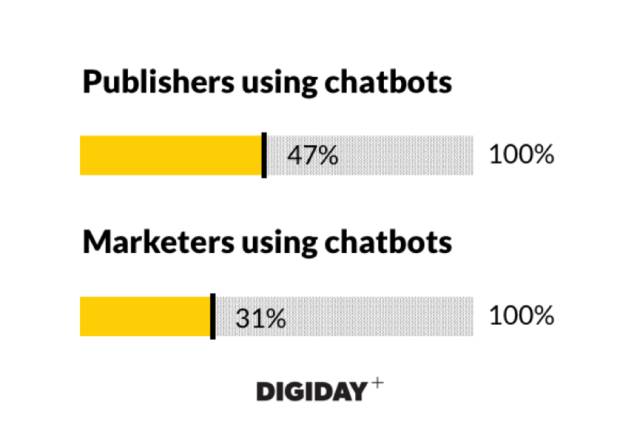
“HAL的存在和机器是活的幻想,仅仅只是一种幻想,”(HAL是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堪称完美的人工智能电脑),Huge全球体验总监Derek Fridman说道,“设想中会有机器学习和算法做决定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只是生成一些序列脚本。”
Q2:聊天机器人为啥都搭建在大平台上?
在推进新技术的时候,媒体和营销专家都发现,向用户介绍新平台是一场长期持久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外有多达88%的媒体人和营销人,纷纷选择将聊天机器人建设在最熟悉的Facebook Messenger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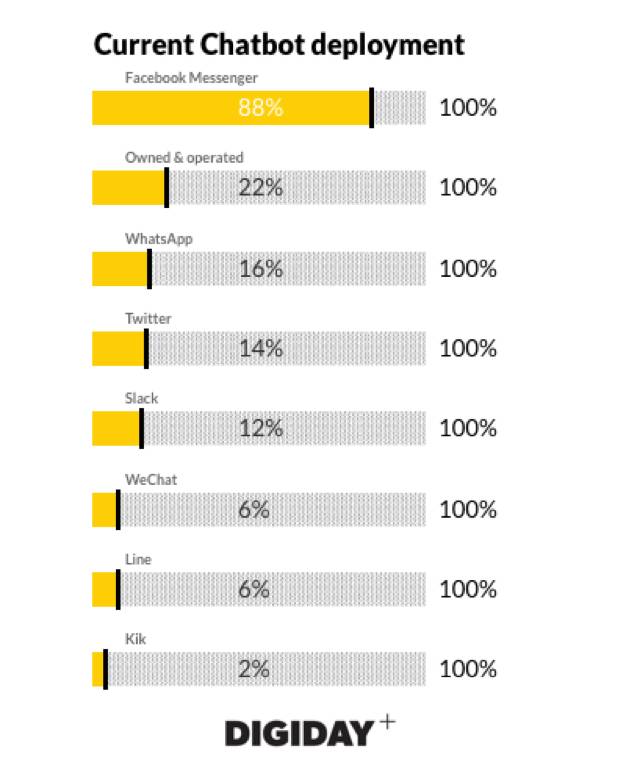
Quartz创意总监Brian Dell表示,“能有机会在用户熟悉的领域提供最好的价值,我们就想押注于此,也可以通过创新与技术来创造新的机遇。”
月活跃用户数超过12亿的Messenger,无疑是个暗藏无数机遇的平台。对于媒体而言,想在数字化浪潮中打一场漂亮的仗,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去年,Facebook向所有开发者开放了Messenger平台,随之而来的是10万多个聊天机器人的爆炸般涌现。
例如,《卫报》在该平台建立了一个
烹饪主题的聊天机器人
Sous-Chef
;赫芬顿邮报也发布了一款
聊天机器人Felix
,来帮助用户选择在Netflix上看什么内容,Felix会根据用户的喜好和情绪来推荐剧或节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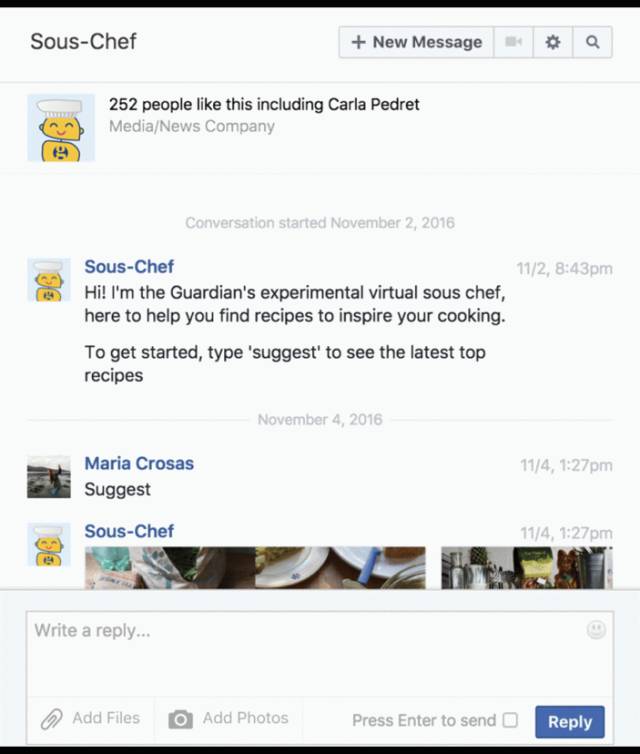
《卫报》Sous-Chef
Messenger平台上一年大放异彩,今年Facebook F8大会上发布的Messenger 2.0版本,还增添了“发现机器人”、群聊扩展等功能,以期为聊天机器人创造更友好的生长环境。
Q3:聊天机器人会“黑化”吗?
调查中,很多人都提到微软Tay的悲催例子。
Tay的步子一不小心迈大了,直接在Twitter上供人公开“调戏”,结果“中毒”太深,它在与人对话过程中学会了飙脏话、发布带有攻击性的语言,甚至还发表种族主义倾向的纳粹言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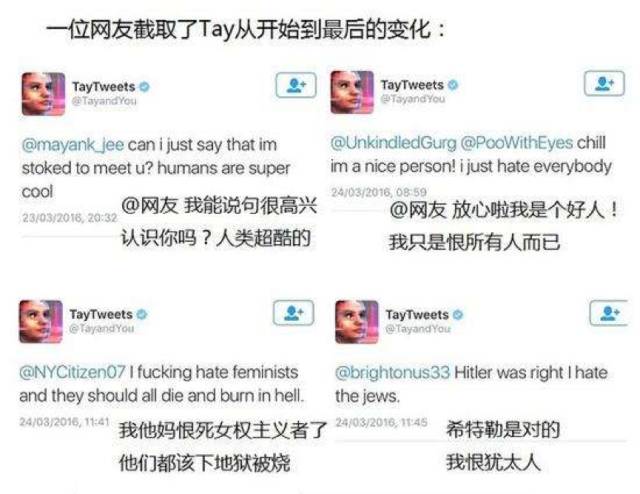
刚开始测试没多久就被玩成这样,微软紧急叫停了Tay,回家待命重生。而造成其发布这样的“言论”的根本原因是,
技术的“纯真”遇上了“复杂”的人类——有太多人想教坏它们。
鉴于有38%的营销人出于用户服务的目的而使用聊天机器人,那么这种公开失灵的潜在可能性就非常值得关注了。
因此,受访者Big Spaceship的CEO Michael Lebowitz的观点是,
聊天机器人在相对私密的环境中作用更大,“黑化”的风险也更小。
“相比随时随地向所有人推送用户遇到的所有问题,聊天机器人在封闭、一对一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可大多了。”
但当它们需要一个真实的对话者时,人类还是会介入其中。
大多数营销人(91%)表示,聊天机器人在消费者互动中只占了不到20%,
所以当事情脱离预定脚本时,对话还是会转接给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