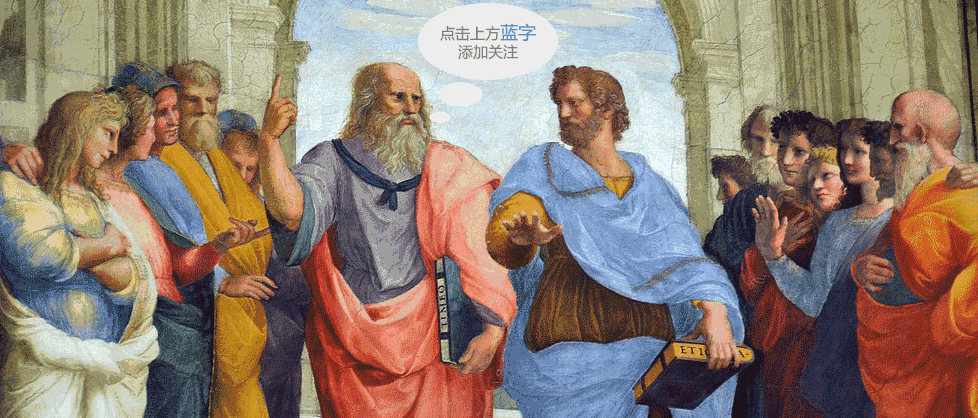
张志扬:
现代学的重审与重建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意向性分析(下)
本文
选自《学术思想评论 第二辑》
评论:
现在可以先对全书总起来说儿句了。
刘小枫在这本书中,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
“
神性
——
理性
——
感性
”
。
历史的这一下行展现是非常触目的,焦点是:世界脱魅后,神证论变成人证论,人的社会理论如何承担提供合法性论证的重负
?
然而描述它是一回事,如何看待它则是另一回事。它在不同的背景上有不同的理解,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神学末世论;一类是科学进化论;还有一类是自由主义个体论。
现代化体现社会的分化原则,即社会整体分解为若干相对独立的个体系统。所以,自由主义个体论既是对社会而言,也是对个人而言,但归根结底是对个人而言,它既是社会进步的现代性标志,同时又是社会解体意义纷呈的危机标志。由此才引出激进右倾的解决办法,如尼采;和激进左倾的解决办法,如马克思;也还引出保守主义的解决办法,如托克维尔。
托克堆尔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他和神学保守主义,如合勒,还不一样。刘小枫在两者之间徘徊,但总的看还是倾向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只是托尔维尔的神学背景很淡化,韦伯也是,而刘小枫可能要强化一些。
当然,刘小枫意识到,中国面临的问题要比托克维尔看到的复杂得多,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自然转型与重建所面临的
“
现代结构
”
缺失的困难。
有鉴于此,刘小枫才在
“
绪论
”
中把现代学分析的着眼点放到
“
现代结构
”
上。既解析
“
现代结构
”
的诸现代层次
(
如现代化题域
—
政治经济域;现代主义题域
——
个体言述思想域;现代性题域
—
个体、群体社会域
),
又勘察诸层次如何在历时性的互动中形成共时态的现代结构以显示其现代功能。
比较起来,中国传统并不乏三层次的平面关切,即以
“
独权
”
为中心的
“
重农
”
和
“
一教
”
。构成
“
宗法一体化
”,
但每一个关切点背后垂直的不平衡动力源却被中庸抑制,日趋萎廓。如,
“
现代化题域
”
中的
“
政治
”
显而
“
经济
”
隐
——
再生产的生产率冲动源缺失:
“
现代主义题域
"
中的
“
感受理念
”
显而信仰的
“
知识
”
隐
——
创生性的较真冲动超验源缺失;
“
现代性题域
”
中的
“
文化制度
”
显而
“
个体、群体的动机结构
”
隐
——
取向性的偏爱冲动欲望源缺失。如此动力源不足作为原因,导致了平面结构的超稳定状态。但作为结果缘何而致于此
?
据查,这种
“
平面结构
“
几乎是
“
第一轴心时代
”
的普世安排,问题在于,其他民族的
“
宗法一体化结构
"
能够孕育出
“
分化的
”
制度机制,而中国为何不能
?
按刘小枫的分析,盖因有两个方向的现象学还原不彻底:一个是现世的理性化不彻底,没能贯彻经验理性的逻辑实证原则:一个是超世的理性化不彻底,没能贯彻信仰理性的逻辑超验原则。因此,超世与现世的二元紧张尚不能紧张到不断分化的动力结构程度。
再问,为何不能还原彻底
?
按照刘小枫的追寻思路,恐怕要进一步审理安排
“
宗法一体化结构
”
的古代儒士的
“
宗教理念
”
的特殊差异性,方可知晓。
其实,刘小枫已预设了答案,那就是中国的宗教理念
“
天人合一的
”
人本化,即
“
天人合一
”
终
“
合天于人
”,“
天行人道
”,
超世与现世的二元紧张消解到现世中了,超越秩序的
“
天
”
被缩减而弱化到政治伦理的程度,即天理不过人伦。说白了,超验一维像
“
甄士隐
”
地被隐了去。
“
道
”
与
“
禅
”
补进
“
儒
”
的不就是一个
“
空
”
字吗,
“
空
”
成为最高的也最消极的超验之维。
难怪有一次我和刘小枫讨论舍勒的
“
空的绝对域
”
时,刘小枫不同意我将
“
空的绝对域
”
作哲学的解释取超验的中立性,他认为应该作神学的解释,即这
“
空的绝对域
”
真实如
“
上帝
”,
终应有一个亚里士多德说的
“
最高形
”,
但不是
“
最高者
”
。这就是舍勒的
“
位格上帝
”
。
这样一个通过现象学的精神意向先天性相关着的位格上帝作为超世秩序的理念之源,它既能启发人越界的自由意志,又能
对任何人为的自由意志予以超验的否定,由此永不安息。但它能否从中国传统文化独得中庸之道的
“
天命
”
中开出来呢
?
如果开不出来,中国的
“
现代结构
”
岂不无望
?
可见,
“
现代结构
”
中的超世之维乃现代性问题之关键。
至少,从刘小枫的
“
绪论
”
逻辑中,回避不了这一终极之问。与此相关的才是现世秩序的合理性安排。所谓合理性,当然是非激进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合理性。它是对超世与现世二元紧张的一个非抑制性的协调
“
绪论
”
的上限、下限及其现代结构的问题意向,我如此界定其误读与偏颇怕是难免,好在读者可以自己去读
我的评论就从上限开始,暂且侧重于理念和方法,而把事实性分析留待日后细究。
(一)从“神义论”到“人义论”,究竟是对还是错?
这样提问显得可笑,是吗
?
它似乎把问题逼到一加一等于二的天真程度上。其实不,如果人义论表现出悖论和危机,像不洁的事实,难道
“
神义论
”
就那么至真至善
?
既然神义论在神的崇高中也摆脱不掉巫术的虚伪与邪恶,为什么在向人义论演化时人证人总有负罪之感
?
科学进化的乐天派是没有根据的,身体性的穷根究底的好奇,未必就只是色情沉淀
?
什么是历史不得不走而超出善恶的真实
?
此题感受复杂,我想分五个小题来谈。
1.
历史
“
下行
”
吗
?
所谓
“
下行
”,
就是
“
神性
”—“
理性
”—“
感性
”
的日趋萎靡,一代不如一代,
“
体现人类发展的一种衰微。
”
舍勒的这一視角显然是有神学背景的。但神学背景并不一定引出下行的结论。事实上,在西方的包括神学的思想史资源中;很难找到严格意义的下行说根据。
“
希腊理性
”,
或基于宇宙循环论,或基于人的本性类型不变而断定未来周而复始。由此取得
“
逻各斯
”
的宇宙
“
智力形式
”
。
“
希伯莱精神
”
或
“
犹太精神
”
是信仰上帝启示的末世论。堕落的人类本身尽管是一种惩罚式的降解,但上帝通过
“
最后审判
”
和
“
千年王国
”
的许诺,已预设了人的救赎。到了基督教,上帝更以十字架的基督代言,赦免了人的原罪,使一切罪罚都要消融在宽恕仁爱的和解之中。
也就是说,人的下行的罪恶性拯救和上行的福祉期待都同一在基督死而复活的
“
十字架
”——“
时间中心
”
上。任何不义不幸都要在这个
“
时间中心
”
上分解为过去时的罪恶性与将来时的救赎。上帝的感召与人的回应同一了。这个同一的
“
中心时间
”
既不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也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而是许
诺了的救恩
0,(
参照李秋零译本。下同
)
所以,与逻各斯的
“
智慧形式
”
不同,上帝及其末世论乃是主宰宇宙与世界的
“
意志形式
”,
它深藏于人类历史的灾难中。有灾难就有罪恶的体验和幸福的向往,正是它构成了解释历史的最直接最根本动因。
这样两种精神,确切地说,希腊理性更多地作为希伯莱信仰的自我确证的手段,共同构成基督教教义思想,成为西方各种理论
(
包括科学进化论、历史唯物论
)
的渊源。
卡尔
·
洛维什说:
“
这两大思想体系,即循环的运动和末世论的实现,似乎穷尽了理解历史的各种原则上的可能性。所有那些阐明历史的各种最新尝试,都不过是这两种原则的各种变体或者它们的各种混合罢了
”
。
洛维什并非空洞陈言。不妨以科学进化论为例。
贯穿科学理性的历史哲学,不管以什么面貌出现,必然坚持这样一种要求: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在此原则下,历史的事件才获得秩序,并且与一个终级意义关联起来。
换句话说,科学地解释历史要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事件、秩序、关联的可实证性;二是终极目的的必然性。
然而这意味着什么呢
?
依据前者似乎可以背离神学,依据后者却不能返回神学。
再以历史唯物论为例,马克思把历史划分为
“
史前时期
”
和
“
未来历史
”
。
“
无产阶级
”
作为历史的
“
先锋队
”
所负有的特殊使命就是消灭一切剥削和阶级,结束
“
史前时期
”
而进入无产阶级的
“
未来历史
”,
即
“
共产主义自由王国
”
。
马克思的这个划分的根据是什么
?
是生产力。不同的生产力阶段所区分的生产关系表现为不同阶级的阶级斗争,一部
“
史前史
”
就是一部
“
阶级斗争史
”,
自由民与奴隶、领主与农奴、贵族与平民、行会师傅与帮工等等。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西哀士
(Sieyes)
曾宣布,
“
因为市民是无,所以市民拥有一切
”
。五十年后,马克思突然宣布这部
“
阶级斗争史
”
到了
“
最后的斗争
”,
以
“
平民
”
为前身的
“
无产阶级
”
将要用一场
“
世界革命
”
结束
“
原罪
—
剥削
”,
把人类送入
“
共产主义
”
的永恒福址。
当时的生产力,即便
“
超过了以往一切生产力的总和
”,
我们知道,同今天比较起来,仍然还是小巫见大巫,今天的生产力规模是那个时代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是,凭什么在那一个生产力阶段竟能如此断言:人类社会的原罪结束向永福降生
?
像法国平民样的无产者遂成
“
特选子民
”
独担此任
?
当然,对历史的解释还会层出不穷。我们既不能用回溯式的类比掩盖阐释的合理化,也不能把某一种解释推崇为万无一失的金科玉律。不管作何种解释,之所以总摆脱不掉循环论与末世论的影响,根本的原因恐怕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走出自己创造历史也创造灾难的不幸阴影,因而对罪恶的体验和对幸福的迫求与向往总是不可分割地根植于人的动机结构中。
由此可见,单纯的
“
下行说
”
或
“
上行说
”,
都难免把历史简化了。
2.
超世隐喻。
不管是
“
下行说
”,
还是
“
上行说
”,
都是一个共同的超验界定,它就是
“
上帝
”
信仰。下行说是背离上帝而行的,上行说是皈依上帝而行的。如果是这样,历史始终都在
“
神义论
”
中,这就是刘小枫的
“
绪论
”
即便有意走向
“
人义论
”,
也无意或无力走出
“
神义论
”
的
“
隐秘历史
”
之源。
有真正的
“
人义论
”
吗
?
即有人独立担当
“
人义论
”
吗
?
这是一个尖锐的间题,我暂时还只能观念地想象它,它包含两层意思:
a.
人是有限的,人的总和也还是有限的,在其有限性上,人不可能缘自身的有限而获自足完满的解答,在这个意义上,人不能提供自身的合理性根据的完全担当。因而,超验是人的有限性不可避免的
“
隐喻格
”
。平常的个人当然可以对隐喻格表示不关心、不切问。因为平常,就是中庸,就是既与、既定的生活,一切都在人力所及的规范中。一旦越出常规,或是太强,或是太弱,二者总是同时相关着超验域,反省与迫问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所以超常出窍而富于创造的生命自然同超验之域有直接的关联。所谓隐喻,不过是这种关联的归根结底应的无知状态。
b.
隐喻格可以隐喻已知的确定对象,成为明喻,也可以隐喻未知的甚至不可能知的不确定的对象。严格地说,隐喻的本质归根结底应是表达不可表达者、言说不可言说者的一种努力。隐喻本身就是对不可言说者的某种启示性的言说,显是为了隐,在既显且隐、显即隐的双重意义上。隐喻格明喻确定的对象如
“
上帝
”
、
“
真主
”
、
“
梵天
”
、
“
道
”,
显然是有范围的,它带着明喻者可明的前提。例如,韦伯的宗教比较学以基督教为比较尺度不确定的对象。一旦超出,明喻仍会转暗,回到隐喻格。所以,隐喻格归根结底是隐喻不确定的对象
—“
空的超验绝对域
”,
即无形之神的所在地。在这个最深层、最本质的隐喻格上,恐怕不能
“
独尊一致
”
。如此相应的
“
神义论
”
及其
“
人义论
”,
才是自由的。它在隐喻中显示着一切确定者、必然者、绝对者的暂时性与消逝性。
a
、
b
告诉我们,即便完全自足的
“
人义论
”
没有,也不能按现有的任何一种既与的
“
神义论
”
作背景构筑普世的
“
人义论
”
。否则,从
“
神义论
”
到
“
人义论
”
的设间,只能是一个民族宗教与民族文化间题。例如,基督教文化的
“
神义论
”
与
“
人义论
”,
对其他民族文化、宗教的
“
神义论
”
与
“
人义论
”,
只有
“
自律
”
的参照性,决无
“
他律
”
的强制性或权威性。
反过来说,什么时候有可能谈论宗教本身,即回到超出现存诸民族宗教的宗教本身。
“
神义论
”
的普世性从而
“
人义论
”
的普世性,才有可能。
3.
宗教的有形与无形。
这个问题并不属于
“
绪论
”
的陈述及其评论范围,它纯属我个人的引申,仅立此存照而已。
从
“
神义论
”
到
“
人义论
”,
对每个民族文化而言,都应看作从传统到现代的现代转型。在这个纵深的意义上,它是普世的现代现象,即各个民族文化都要或都在经历的现代现象。
如果一旦发生横向关联,关联者想论证某一种民族文化的
“
神义论
”
向
“
人义论
”
的转变同时就是普世性的,如基督教世界的
“
神义论
”
向
“
人义论
”
的转变,似乎也构成全世界必须接受的超世与现世的二元模式,这不仅是一个逻辑错误,更主要它是一个事实错误。概而言之,没有本体论是同一的,因为本体论本身就是无限的差异,即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存在与神的差异。
“
绪论
”
的知识学态度是清楚的,刘小枫旨在把基督教世界的
“
神义论
”
与
“
人义论
”
的转变摆出来,包括它的得与失,并以此作为
“
参照
”(
不是
“
户度
”),
提出中国文化或
“
华夏文化
”,
也必须经受从自己的
“
神义论
”
向
“
人义论
”
的现代转变。特别指出并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由于中国
“
神义论
”
向来弱势,以致弱势到
“
圣言
”
之中,麻痹了中国的老儒和新儒,以为
“
人义论
”
中国古已有之。历来如此,
“
西人今觉是,我人昨岂非
”,
近代落伍的民族中心论便重新拾头,自诩领
21
世纪之先。刘小枫把这种不正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与转型的陋儒之习,冠名之曰:
“
怨恨
”
。
但这决不是说,刘小枫主张基督教
“
神义论
”
向
“
人义论
”
转化的普世性:
“
独尊耶教
”
。虽然在揭示基督教现代转型同懦家现代转型的差距时,难免有立论的偏向性,甚至有时也表现出某种教养上的
“
价值偏爱的动机结构
”,
但这丝毫不等于说,中国乃至世界,只能走基督教的
“
神义论
”
向
“
人义论
”
转变的唯一之路。
“
中西之争
”
是一个虚假的二值逻辑,基督教之非不等于儒教之是,反过来,儒救之非也不等于基督教之是。问题在于基督教在历史上遭受的打击的毁灭性,一点不小于儒教,但基督教经受了现代转型的考验,
“
上帝
”
的形象变化之大,孔圣人是望尘莫及的。这不是贬圣衰神,而是说,中国
“
人义论
”
的现代转型,尚未完成。而其中人的神相分以揭示人的有限性以及更深的追求与获救的超越性,经从现世生活与传统命脉中开出来,取得中国独特的分合形式为普天之
“
道
”
的无形之神作出自己非他人可取代的贡献,仍是一项极艰难的现代性课题。
从我个人读
“
绪论
”
所获得的印象,刘小枫已从
“
基督教神学家
”
走向取中国现代文化视野的
“
知识社会学家
”
。简言之,角色变换了。如前所述,刘小枫的学术进路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不断变换角色意识以纵横阅历人间面相。
但他有一个限度:变到极限处,总有一双上帝的眼睛。也如前述,在
“
空的超验绝对域
”,
必须是一个有形的上帝。否则,无形而空,或坠入虚无,就必然让人或人造之神僭越而独断,造成世界化或一元化的绝对者,世界便无自由可言。二十世纪的世界现实如此,中国的现实亦如此。
此言极是。它在双重意义上。一是不能在现世把一种理想
(
一个意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
僭越为绝对者。一是不能在超世把一种宗教神如基督教上帝僭越为绝对者。让基督教的上帝在
“
诸神不和
”
的超验域实行对诸神的专制,正如人间的专制一样。
更深一层的问题的是,
“
空的超验绝对城
”
何来有
“
形
”
的上帝
?
而且这
“
形
”
既是人能想象的,又何来
“
超验
”
与
“
绝对
”
之有
?“
空的绝对域
”
所
“
绝对
”
而
“
空
”
的究竟是
“
形
”,
还是
“
灵
”?
是否在绝对域的
“
有形神
”
之上还要有一个绝对绝对域的
“
无形之神
”?
否则,
“
意义危机
”
不仅是现世的危机,它首先就是超世的即亡国的危机了。基督教的
“
圣父
——
圣子
——
圣灵
”
三位一体,在基督教史上,也有一个理解中心的转移,即从
“
圣父
”
上帝为中心
(
旧约
),
转到
“
圣子
”
耶稣为中心
(
新约
),
现代已转到
“
圣灵
”
教义为中心了
(
战后
)
。尽管每个中心都还是三位一体,毕竟这转型显示出一种脱形之势。
在人类上古史的前轴心时代,几大文明对信仰绝对域的神有一个几乎共同的初始经验:
“
逻各斯爱隐匿自身
”(
希腊
)“
太初有逻各斯
”
“
不准制造偶像
”(
犹太
)“
空空如也
”(
印度
)“
道可道非常道
”(
中国
)
也就是说,神是超出一切形之上的无名之灵,唯敬畏可以面对,即在敬畏中把自己的有形供奉其示,以求警戒、救赦与恩赐。
神断乎不可以任何形式为人所用,神没有形式、也不允许有形式为人所用。
“
不准制造偶像
”
。所以后来的人为神赋形即是神为人所用的开始。于是有各种宗教发生,人进入宗教时代,标志人的进步、僭越、堕落、拯救的轮回,其实已是人义论时代。
宗教即神的逃匿。
人只有在自身惨痛的经验中追寻神的逃匿,重新以敬畏期待神的救渡。
“
爱
”
是人义论的范畴,
“
恨
”
也是。
“
畏
”
才是神义论的。我的后宗教观是:
无形不能执
执形而能信
执形而信非信也。
爱而人
畏而神。
4.
舍勒的怨恨。
舍勒的
“
怨恨
”
论其实质是
“
人义论
”
。换句话说,怨恨是从
“
神义论
”
向
“
人义论
”
转变的一个标志,在舍勒看来,它揭示了人的动机结构中的价值偏爱,因而显明了
“
人类的衰微
”—“
怨恨归根结底是
‘
没落的生命
’
现象之一
”
。
面对人类的这种
“
没落的生命
”,“
衰微的现象
”,
其最根本的动机结构中的价值位移机制已然如此怨恨了:如何还有
“
修复的可能
”?
《道德建构中的怨恨》是舍勒的早期作品,受尼采《道德的谱系》的启发,但对尼采的怨恨论作了分解。
尼采把基督教道德骂作充满怨恨的
“
奴隶道德
”,
但尼采并不反对真正的基督徒,如耶稣。
舍勒以此为出发点,把基督耶稣的爱同世俗化的基督教的爱即
“
现代仁爱
”
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来自上帝之爱,是上帝的
“
屈尊行为
”,
它本身就是上帝之爱的充盈活动。它决无爱之外的利益目的。后者即
“
现代仁爱
”
、
“
泛爱
”
、
“
博爱
”
发自价值低位者的怨恨动机所选择的价值主体化的欲求与功利目的。平等是其表现形式,即按价值低位者的主体价值作为平等尺度。
“
平等要求总是一场
a baisse(
拉下来
)
的投机
!”
由此引申,舍勒作了一个严厉的判断:
“
全部人类历史所包含的人类活动的诸类型中,都存在着巨大的怨恨危险
”,
连最高权位的
“
祭司
”
都不例外。相反,
“
罪犯
”
因怨恨的宣泄而最少怨恨。这就是基督耶稣为什么对罪人反倒有
“
极为神秘、令人惊讶的倾向
”
。没有怨恨的忏悔离上帝最近。
“
除了你们的上帝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事
”,
那些以自己为良善的人,其实是心怀怨恨的人。
换句话说,除了上帝,世人没有价值高位者,自以为有,必然对上帝心怀怨恨,即便他是祭司,也离上帝很远。只有心存负罪感的人,才能去怨恨而忏悔,领承上帝之爱于自身。所以,罪人有福了。
但是,舍勒一旦离开了为基督徒辩护的立场,转身面对世俗,他便把尼采颠覆价值的怨恨论引向旧价值的保守。
由于面对世俗,上帝的
“
尊位
”
已经隐去,
“
上帝之爱
”
的爱行本身也随之隐去。但作为怨恨论前提的价值客观性的优劣定位是无法隐去的,它便投射到世俗的
“
等级制
”
中,如贵族和平民,显然,平民是怨恨者。从平民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精神自然以怨恨为动力结构了,无产者更每下愈况。最后,人类呈现出一种
“
衰微的现象
”,
得出
“
生命没落
”
的结论。
就在这篇《道德重建中的怨恨》里,舍勒似乎没有发现
“
上帝之国的绝对价值
”
与世俗之国等级制中的绝对价值是不相容的但它们都构成怨恨论的前提,区别仅在于卑贱者接受上帝的屈尊之爱,不接受高贵者自诩的价值优位和对低位者的警惕、压制和鄙夷。舍勒忘了,世俗等级制中的所谓价值高位是同既得利益紧紧粘连的。这同上帝之爱的非功利性根本不同。顺便说一句,上帝之爱的
“
屈尊
”
性不过是舍勒心中等级制的修辞语,它隐含着对上帝和平民同爱的怨恨。
不仅如此,为把
“
怨恨
”
推进到体系的彻底性,舍勒几乎在现代人的动机结构中把怨恨规定为
“
现代仁爱
”
的基础而排除了怨恨行为中对爱心良知本身反省的可能性。
舍勒的后期作品:《爱与认识》、《懊悔与重生》、《受苦的意义》、《爱的秩序》
,
才出现了转机。
在《爱的秩序》中,舍勒明确指出:
“
任何恨的行为皆以一种爱的行为为基础
”
。
这里说的
“
爱
”,
虽不一定是上帝之爱,但无疑作为良知的优位从属于
“
上帝之爱
”
中,或在现象学的先天性相关中意向
“
上帝之爱
”
了,总之,这种
“
爱
”,
不再以怨恨为基础,像早期怨恨论中所规定的。
事实上,或在理论上,只有如此颠倒价值优位,
“
爱
”
比
“
怨恨
”
根本,现代人也一样,舍勒才能真正完成
“
道德重建
”
的人义论。
所以,早期舍勒的怨恨论,太着迷于人性中负面价值的推论而难免之偏颇,我们在引证或引用时,必须小心对待。
5.
福柯的感性。
刘小枫按现代学的眼光认定:
由尼采提出、为福柯推进的审美主义的身体本体论,其最终结论是取消
“
义
”(
伦理
)
问题,而无论神义论还是人义论的辩护都会伤身,那么
,“
个体生命靠什么来为自己的有限的在世孤身的幸与不幸辩护
”
呢
?
的确,这是个相当棘手的思想难题。
一味靠身体来自我辩护,像后现代的行为主义者那样,不行;但一味像舍勒的身体现象学那样,把身体
“
括
”
起来,即
“
阻止
"
。
“
扭转
”
、
“
净化
”
身体对
“
精神
”
、
“
理念
”
、
“
价值
”
等身外物的怨恨,为了占有、支配身体成为
“
位格之在
”
的处身性,让身体承担不可避免的
“
受苦
”
与
“
死亡
”
而为此意向
“
永生的理念
”,
达到
“
感性共属关联
”(Sinnzusammenge
boerigeit),
最终成为身体之在与位格之在的统一整体,恐怕也不行。因为还是沿着黑格尔的老路子走,虽然用了胡塞尔现象学还原法的语言。
“
理念
”,
从古到今,变化不是很大的。尤其作为范畴,它只在上帝的理念和精神的理念之间徘徊,区别相当狭窄。它本来有无限的隐喻域,但人们无法去想象它,因为没有谁提供
“
可感的意义共属体
”(sinnzusammenge boerigeit)
。有
“
感知
”
的给予性才有
“
想象
”
的给予性,这是现象学意义还原法的原则
这只有
“
身体
”——
唯一的实在之躯,可以做到,它才能提供
“
可感之意义共属体
”
。
但是,
“
理念
”
不放行。
“
理念
”
总想将
“
身体
”
控制在自己的意义域内,即限定身体的感觉阈,它只让身体去感受理念所能理念的意义,连身体的
“
受苦
”
与
“
死亡
”
的意义,理念都已准备完毕,
“
身体
”
无非是被理念强奸的
“
意义共属体
”
。这就是一切理念优位论的逻辑,不管这逻辑是来自二元,还是一元。
于是,才有
“
身体
”
要求解放的呼声。
后现代的身体行为主义者,以解放之名,的确走到了
“
色情、冲动自由
”,
但是否是
“
人身上一切晦黯的、冲动的本能的全面造反
”,
还难说,因为,我们不能对
“
一切本能
”
作经验的检举。身体的潜能,即便有极限,那也是一个不可穷尽的极限域。所以,身体在探索自身的能在这一事实性上,它有天然的优先权。不管其后果,
“
道德、理念
”
们喜欢不喜欢。
用哲学的行话说,一个
“
在体
”,
总要
“
在出来
”,
才能在
“
在出来
”
的可感性上意向
“
位格之在
”
。而不是相反,根本就没有
“
在出来
”
。
“
位格之在
”
就把
“
身体之在
”
统一到或不如说限定到理念可理念的价值优位上。如此充当
“
身体之在
”
的保护人,很难不对身体之在的可在性即可生成性不执行保护性的刺夺。事实上,已经剥夺了。理念早就
“
拒绝
”
、
“
阻止
”
、
“
扭转
”
而被理念判定为
“
自然性的冲动
”
。这还不是放进现象学的
“
括号
”
。
现象学的
“
括号
”
并不拒绝、阻止、扭转身体之在的
“
可在性
”
本身,而只是否认身体性感知的意义自在性,即身体性感知成为意义的唯一的直接的给予者。现象学所坚持要求的,必须还要有与身体性的可在性先天性相关的给子性及直观还原的反思性。它不仅开掘可在性的意义,尤其还能激活想象在可在性的被给子性上创造出追加的剩余意义,如同
“
剩余价值
”
。这才是追随而超出的先天性相关的现象学还原法,它才能造成非强奸式的
“
可感性意义共生体
”
。
显然,这儿有一个基质,它就是
“
身体的潜在性
”
。它断然不是理念可以预设的领域,理念有权超越,但必须在追随追加之后。其
“
逻辑之先
”
是以
“
时间之后
”
为前提的。
否则,胡塞尔就把他的现象学
“
反思
”
看成绝对直接的还原法了。那才是理念的僭越。
这种没有反思预设限定的开放的现象学方法,海德格透过胡塞尔与舍勒悄悄地、狡黠地暗示着,给法国人以极大的启发。
如何探索、实证
“
身体的潜在性或能在性
”?
这全然不是一个观念问题,也不是一个理性问题,而是一个在体的可在性的冒险问题。
尼采只是说出了
“
在
”
的冒险,
“
存在的一个基本特性可能就在于:谁彻底了解了它,谁就会灭亡
”,
像美杜莎的头。福柯却是用身体之在直接投入冒险之中。
仅有此在还不够,福柯并非混迹干
“
皮革场
”
中的
“
皮革士
"
。
福柯之所以是福柯,全在于他还在身体的冒险中直观着冒险本身。
剩下的问题是,福柯直观的意向何往
?
诚然,福柯并没有在皮革场上据皮革之身面意向
“
上帝
”
的理念。他意向的只是中断自我的历史构成、中断自我的理念包括自我性别的理念,他要再造一个出自我在的自我,即使冒天下
“
非性别之在
”
的大不题。
看起来,福柯之想,是在用身体的僧在性、能在性提供
“
自我引证
”
的人证
——
人义论。但是福柯的眼光还不止于此
“
宗教曾要求人类做出肉体上的牺牲,而知识现在则号召对我们自己进行试验
”—“
敢于认识
”(
康德论何谓启蒙
)——
即使这种试验会导致
“
知识主体的牺牲
”
。如若成为
“
自己
”
会释放了一种可能的冲动
—
恶,那也挺好:
“
人需要自己最恶的一面以便实现自己最善的一面。
“
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
”
。
福柯的确不是神的追随者或皈依人,但也不是冒渎者,他借着两个抽得德尔斐神庙神谕的先哲的启示,一人独走两条路:
一个是苏格拉底:
“
认识你自己
”
一个是第欧根尼:
“
改变你自己
”
。
确切地说,福柯更钟情大儒主义者第欧根尼,唯在
“
改变自我
”
中
“
认识自我
”
。
但福柯能把
“
自我
”
改变成什么
?
这个改变了的
“
自我
”
的
“
真实性
”
在哪里
?
福柯使用的
“
改变
”
的
“
策略
”
、
“
技巧
”
、
“
途径
”:“
迷幻药
”
、
“
同性恋
”,
特别是同性恋中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