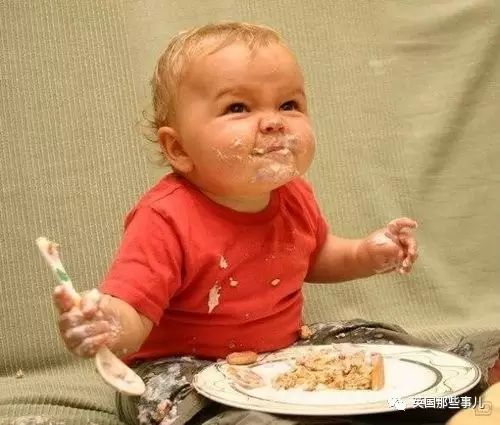精神疾病是复杂的:无论是症状本身,还是症状与健康状态的界限。因此,适当的诊断标准尤为重要。过高的标准会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隐匿在阴影中;而在过低的标准下,一切异乎寻常的行为都被打上疾病的标签,不但限制了社会的多样性,也可能对正在遭受精神苦痛的人造成伤害或干扰他们向外求助。
那么,什么时候应该进行诊断、诊断的标准是什么?目前的精神病学提出了三个界定疾病的标准,分别是功能失常、个人痛苦与损伤、不典型或非文化预期[1]。
“功能失常”:指认知、情绪、行为功能的异常。假设小A在和一个人约会。这本应是愉快的,但如果她全程感到没有来由的强烈恐惧,且这种恐惧出现在每次约会中,我们就可以推测小A的情绪存在某种程度的异常。然而,如果对方是一个危险且不可预测的人,小A的恐惧就是适应性的,并非功能失常。你或许能感受到这一标准的模糊性:研究者普遍认同功能的适应与否处于一个连续体上,没有确定的分割准则。这也是单纯的功能损害不能作为疾病诊断标准的原因之一。
“个人痛苦与损伤”:顾名思义,“个人痛苦”的标准在患者本人因自身的状态感到苦恼时才会满足。但并非所有精神疾病都满足这点,例如处于躁狂阶段的很多个体会享受这种精力充沛的状态,而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也往往不会因自己的行为而困扰。因此,“损伤”提供了很好的补充。如果症状为本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明显的困难和损害,那么这有可能是障碍的表现。
“不典型或非文化预期”:这或许是最困难的标准。异常很难通过某种现象本身界定,必须考虑它出现的背景,尤其是同一文化下其他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举个例子,“听到(或认为自己听到)不存在的声音”在一些原始文化中是神性的象征,常见于宗教仪式中。然而,在现代社会,它并非文化所预期的,因此更可能是症状。并且,这一标准需要谨慎地使用:我们不能把一切偏离平均或当前社会规范的现象划归为疾病。为此,有研究者对此标准进行了细化:这些非典型的表现需要是有害、且个体无法控制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这些标准的争论还在继续,心理层面的疾病与健康向来不存在自然状态下的二分。在临床上,更有效的方式为衡量一个人的各种症状是否符合某种特定障碍的诊断标准。国际上通用的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为每种障碍总结了一系列症状,只有满足某些特定标准时,精神科医生才能给予诊断。例如,自恋型人格障碍的诊断需要满足下列症状中至少五条[2]:
1. 自大感(夸大自身成就和才华,期望在没有相应成就的情况下被认为是卓越的)
2. 沉迷于无限成功、权力、才智、美貌或理想爱情的幻想
3. 认为自己“特别”,只有其他“特别”或地位高的人才能理解自己,或能够和自己交往
4. 对赞美有过高需求
5. 期待拥有特权(对特别优待或他人顺从自己期望的无理要求)
6. 在人际关系上具有剥削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人)
7. 缺乏同理心(不愿认同他人的感受和需求)
8. 经常嫉妒他人,或认为他人嫉妒自己
9. 表现出傲慢、轻蔑的行为或态度
尽管临床上对于不同精神障碍给出了专业的诊断标准,精神诊断的目的并不是为人们贴上某一特定标签;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对病症现象进行提炼归纳,从而辅助恰当干预方式的选择。用作者的话说,“用诊断结果来鉴定某人是一种曲解行为”:疾病概括不了一个人的身份;先于“患者”的,总是这个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