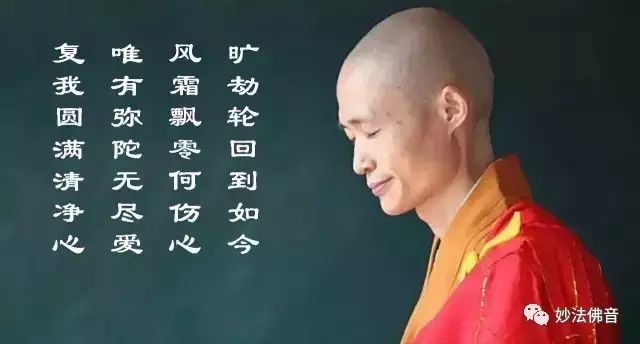提要
阿马蒂亚•森所证明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证明:两个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原则——最小自由原则和帕累托原则——之间是会存在冲突的。这一定理所蕴含的是一个元问题:确定自由边界的理据是什么?消解森定理中的悖论,需要形成某种合理的偏好。偏好的合理性、自由和权利边界是在历史过程中动态形成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是动态调整的。理解森定理,对于分析当下中国面对的种种权利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森定理 自由 权利
一、问题的提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人是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提出的这一著名命题应该如何解读?本文的理解是:在观念上人应该是自由的,但在现实社会活动中,人的自由要受到诸多的限制。沿袭这一命题马上可以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人享有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可以先看一个真实的案例。2002年8月,陕西延安有一对夫妻在家中观看黄碟被举报,于是警察破门而入带走了当事人。这一事件在当年轰动一时,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其处理结果是以执法警察受到处分而告终。当时形成的主流共识是,公民应当拥有一些不受侵犯的私人领域,夫妻在家中观看黄碟属私人领域的活动,是不容公权介入的,这是基本的自由理念。然而,苏力(2003)却同样基于自由主义的知识谱系对此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第一,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自由是以不损害他人同样的自由为前提的,而这一事件缘起于举报,表明存在着他人的自由被损害,须知,举报人得知了这对夫妻的行为完全可能因此受到伤害,在他看来,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违背了他内心的价值准则。第二,自由主义并不预先设定各种自由的价值高低,儿童的游戏和哲学具有同样的价值、国王的自由与庶民的自由同样重要。所以简单地认定政府对夫妻在家看黄碟完全没有理由干预的说法是过于草率了,因为很难确定当事人看碟的自由与举报人避免内心感受到的被伤害的自由哪一种更具正当性。第三,在道德层面上如果大致同意看黄碟在特定群体中是被非议的行为,而社群的观念与情感是维系社群内部秩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则本案中在那时那地看黄碟是侵犯了整个社群的并非毫无理由的偏好,邻居的诉求是应当被尊重的。
苏力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普遍性问题,仅仅立足于夫妻当拥有看碟的自由而为其进行辩护的“自由主义”是有缺陷的:第一,它是不完整的,忽略了自由的限度,忽视了自由主义总是坚持考虑的一些其他因素;第二,这种不完整的自由主义被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了,成了对自由主义教义的重复,失去了对生活本身的关切。
与之类似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其实非常多。如广受关注的例子还有:2003年前后,北京、杭州、苏州等很多地方的政府出台了禁止乞丐行乞的规定;在2005年,鉴于广州市治安的糟糕,很多抢劫案件都是外来“无业人员”所为,于是钟南山院士提出要恢复强制收容制度。这些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讨论,但有关的评论并不是一边倒地批评,而是批评与支持并存,且论证的理据居然都是援引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从此类事件中可以抽象出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是:在观念上视自由为最高价值是容易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落实观念上的自由是困难的。为什么在终极理念完全一致时,却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存在如此大的反差呢?因为有一个问题实在太令人困惑: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进而,只有确立了自由的边界,才能为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划出一道边界,即政府所管理的领域只能是在个人自由之外。
二、自由悖论: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阐释
何谓“自由”、如何确立“自由”的边界,是政治哲学中的基础性问题。古典自由主义倾向于从否定的角度对自由进行界定,如哈耶克的看法是,自由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哈耶克,1997:3)。就这一看法而论,所谓自由,指称的是个人所拥有的免于种种限制的活动空间。由此引申开去,伯林所定义的“消极自由”仍然是作如是观,“如果别人阻止我本来能够做的事情,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的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到某种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奴役状态的”(伯林,2003:189)。
然而,凡此种种从否定的层面对自由的理解,并没有给出一个界定自由之边界的确定性原则。故而在现实生活中举凡遇到前述的特定案例,解决之道往往是诉求于生活常识和一些“公认”的判定准则。可是,据此来确定自由之限度并不是完美的解决办法,甚至,人们思维中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自由准则”之间会彼此矛盾。阿马蒂亚•森(下文简称为森)1970年证明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揭示了其中的吊诡之处(Sen,1970)。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代表作有:《贫困与饥荒》《以自由看待发展》《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等。[图源:bing.com]
森首先提出,有两类确立自由之限度的原则应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其一是最小自由原则(也叫自由至上原则),即每个人应该拥有一些“起码”的自由,比如睡觉时选择侧着睡还是躺着睡、自己房间里墙壁的颜色是涂成白色还是黄色。这一原则应不会引起多少争议,因为这类行为既没有冒犯他人更没有侵害他人,可以把这些行为选择称之为每个人可以拥有的最小限度的自由。即是说,如果每个人都偏好某一备选项x甚于另一备选项y,则社会必定偏好x甚于y。这项原则应该也不会引起争议。
可是,森却证明了,这两项原则可能是会相互冲突的。他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有两个读者A和B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的看法很不一致,在选择是否读这本小说时可以有三种状态组合:状态x是A读而B不读,状态y是B读而A不读,状态z是两个人都不读。A先生是一个“思想保守”的卫道士,他希望最好谁也不读这本带有色情意味的书;但如果一定要有人读时,他宁愿自己读而不愿让B读,因为他坚信自己有足够的意志控制力来拒绝这本书的不良教化;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只有B读,因为他担心B会从中受到精神毒害。因此,A先生对这三种状态的偏好顺序是z>x>y(“>”指的是状态的排序)。读者B则是个“思想解放”的前卫青年,他希望人人都能欣赏这部小说,尤其是愿意看到像A这样的卫道士也放下架子读它;要是A实在不情愿读他也愿意自己读;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这部小说被查禁。因此,B的偏好顺序为x>y>z。
按照个人自由至上原则,现在对这三种状态进行比较。(1)比较x和z,状态x是想读的人读不成,不想读的人却偏要读;状态z是两人都不读。根据自由至上原则,A先生不喜欢读这本书的意愿属于被尊重的最小自由,他不应该被强迫阅读这本书,因此,社会评价应该认为状态z要优于状态x。(2)状态y和z比较,状态y是思想开放的B先生读这本书,按照自由至上原则,B先生读这本书是与他人无关的,既然他喜欢读这本书,那么他的这一自由应该首先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社会评价是认为状态y优于状态z。所以,按照自由至上原则,状态z即两人都不读比x即不愿读的人却被强迫读要好,而且,状态y即愿意读的人读要比状态z要好。这就是说,从自由至上原则出发,社会对三种状态的评价是y好于z且z好于x,可以将其表达为y>z>x,去掉中间状态z,则y>x也成立,其涵义是把书交给B先生。
而如果遵循帕累托最优原则,却得到相反的结果。因为根据两个人对三种状态的偏好排序,A先生的选择是认为状态z优于x且x优于y,表达为z>x>y;B先生认为状态x优于y且y优于z,表达为x>y>z。观察这两组个人偏好的顺序,可以看出,两个人都同意状态x优于状态y即x>y,根据帕累托原则,则社会的选择是x>y。这与根据个人自由至上原则得到的结论恰好相反。
森证明的这个结论即是著名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也被称之为“森定理”或“自由悖论”)。这则定理背后的寓意是:帕累托原则与个人自由至上原则可能是不能同时存在的,要么帕累托原则被违背,要么是自由至上原则被放弃。可是,在人们的常识中,这两个原则显然是不证自明的。
当然,有论者或许会反驳说,在森定理中,造成个人自由与帕累托原则不相容的原因是个人偏好的某种“外部性”。一般来说,个人偏好只能是自我的,不能将自己的偏好强加给其他人,且更不能以强加给其他人的偏好来进行社会层面的选择。比如在这则故事中,偏好的外部性表现在几个方面:(1)卫道士A对B(其他人)是否阅读该书的关注程度即对方案z和y的选择,甚至超过了他自己是否阅读该书的关注程度即对方案z和x的选择。(2)卫道士A对本应该属于由思想解放者B自己决定的方案选择,即对于z和y的比较,莫名其妙地持反对的态度,即他坚决不希望B读这本书,而不管B自己意下如何。(3)同样,思想解放者B对A(其他人)是否阅读该书的关注程度即对方案z和x的选择,甚至超过了他自己是否阅读该书的关注程度即对方案z和y的选择。(4)同样,思想解放者B对本应该属于由卫道士A自己决定的方案选择,即对于x和z的比较,持反对的立场,即他坚决希望A读这本书,而不管A自己意下如何。故而自由悖论的出现是由两位“关心他人甚于关心自己”的外部性行为造成的,如果两位都只是管好自己的事情而不去关心他人的选择是什么,尊重一下他人的自由选择,则不会出现不可能性。
不错,如果能对个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界定好个人自由的范围,不将这种具有“外部性”的偏好视为个人自由并纳入到社会层面的选择范围之中,的确是可以消解不可能性。可是,这一批评并不是多么的有效,正如许多论者曾经指出的,消解森定理,只须回到“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分就可以了,在私人领域之内,私人之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但依然要追问的是,某种私人领域之内的确之无疑的“自由”是如何确定的?或曰,是社会公认的结果。可是,“社会公认”不就是帕累托原则么?事实上,森定理中蕴含的问题在逻辑上是先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二分的,只有先确立了确认自由的原则,才能据此将“公共领域”从“私人领域”中分离出去。
森定理的提出对固有的关于自由的知识和理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可以说,这一定理是对关于自由的种种争议的高度抽象和总结,它所蕴含的是一个元问题:确定自由的准则到底应该是什么?
三、自由悖论的实质:群己权界的再阐释
按照伯林的经典分析,自由被区分为否定性自由和肯定性自由。否定性自由是“免于什么束缚的自由”,强调的是保护个人权利并且抵抗权力,落实为各种个人权利;积极自由则是“做什么的自由”,强调的是各种参与性的权利。否定性自由和肯定性自由的两分法是理解自由的经典模式,但是,根据这种两分法并不能赋予自由以实质性内容,故并不能回应森定理中的问题。
森定理的被发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分析与批评》(Analyse & Kritik)甚至在1996年第18期组织了关于森定理的专题讨论。在对森定理的诸多讨论中,形成了几类看法。
其一,对权利本质的探讨。如诺齐克(Nozick,1974:165-166)指出,森对权利的理解是不合适的,权利应该蕴含个人在特殊领域中独立行动的权限。萨格登(Sugden,1985)、吉尔特纳(Gaertner et al.,1992)等也持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将权利视为“个人行动或策略的可容许性”,将社会结果视为“各种n元可行策略的执行的(同时的或序贯)结果,其中n是拥有各种权利的个人的数目”(Fleurbaey & Gaertner,1996)。这一看法的含义是,权利表征的是个人可自由行动的领域,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各种权利,社会状态就是各自拥有各自的各种权利的一个集合。诺齐克(Nozick,1974:165-166)认为,最小自由与帕累托原则并非不可相容,最小自由是一种权利,权利是在社会选择之外的,即社会选择只能是在权利之外进行,而帕累托原则是“模式化”的一种方式,对“模式化”的运用须受到权利的约束,只能是在权利之外进行,帕累托原则相对于权利而言并不具有任何优先性。
其二,以博弈的形式界定权利。弗勒拜尔等(Fleurbaey & Gaertner,1996)提出了博弈形式的自由观和权利观,他们认为以博弈的形式来界定权利时可以消解自由悖论。博弈形式对自由和权利的理解是,每个人拥有一个可行的行动策略集合,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行为策略,在这里自由体现为对可行的行为策略的限制。博弈形式界定自由或权利的大致模式是,个人做某件事情的权利取决于其他发生或者没有发生的事情。在人们的行为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时,尤其是在发生“侵犯性行动”时,这种界定权利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处理某人拥有不被其他人对自己吞云吐雾之类权利与人们拥有抽烟的权利之间的冲突时,博弈形式的处理方式是,一般意义上吸烟是被允许的,但禁止有他人在场时吸烟,或者如果有人反对在他被影响的范围内吸烟则就应该禁止,以此来保障讨厌被动吸烟的人的权利不被侵犯。这是一种依照某种正当程序来界定自由和权利的方式。在处理卫道士和前卫青年阅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发生的冲突时,博弈形式会要求对某人的行为加以限制,比如前卫青年不得在面对卫道士时阅读这本著作,或前卫青年不得要求卫道士阅读这本著作即可消除自由悖论。
其三,以缔结契约的方式消解自由悖论。相关人缔结契约改善所有人的自由状态,是一种最为通常的消除自由悖论的解决思路。如在阅读著作的例子中,如果两人达成一个契约,前卫青年承诺不读这本书,卫道士承诺读这本书,那么两个人的最优自由状态就都实现了。
但森(Sen,1996)对所有这些批评皆不同意,并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一一进行了批评性回应。如森(Sen,1996)对诺齐克等所主张的“权利本质论”的批评是:诺齐克把权利界定为一个人可以自由行动的选择集,要求权利在认识序列上先于帕累托原则和公认的“社会排序”,即任何人不能对权利进行干预;可是,任何人都尊重权利原则,这不恰恰正是社会选择和帕累托原则么?森(Sen,1992)对以博弈的形式界定权利的批评是:博弈形式在界定自由时的出发点是考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因素,以避免人与人之间可能的侵犯性行为,这实质上是根据别人的行为来定义可行策略集合,其目的是使人们避免一些结果,如避免被动吸烟的权利和自由;所有这些策略选择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权利集合,这个权利集合应为所有人等度享有,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人同意的社会状态,而某种人人认同的“社会状态”无非也就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故而以博弈形式来消解自由悖论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而已。对于以缔结契约的方式消解自由悖论,森的看法(Sen,1992)是:两个人为什么要缔结这样一个违背了他们本来意愿的契约呢?其中保守者非得同意阅读一本他很痛恨的书,以免前卫青年阅读它;而前卫青年反过来同意放弃读一本他原本很希望去读的书,从而诱使本来非常不情愿的保守者去读它。如果人们认同每个人只需要照管好自己的事,就不应该缔结这样一份干预他人行为的契约,一个信奉自由的人固然希望他人阅读自己所喜欢的书,但不应该缔结这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契约,故而缔结契约的理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森定理到底指向的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呢?正如森自己所说,他提出自由悖论的目的在于:帕累托自由的不可逆性以及相关的结论的益处不在于它们作为悖论或难题的价值,而在于重新审视对个人和群体权利的各种通常表述以及普遍接受的决策原则(Sen,1996)。
不错,森定理正是再一次提出了如何确认“群己权界”的问题。他(Sen,1970)指出,在存在某种外部性的情况下,坚持某些特定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那么将不得不规避对帕累托原则的支持。其中某种自由主义价值观指的是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帕累托原则是群体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确认,群体所确认的个人自由的边界与个体自己坚持的自由之间的冲突构成所谓“群己权界”。严复先生曾将密尔的《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论》,他在这部书的《译凡例》中极其精当地阐释了“群己权界”的含义,他说
“自由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由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穆勒,1981:Ⅶ)。
将“自由”译为“群己权界”,笔者以为,这是达致了“信达雅”的至高境界。
四、消解自由悖论路径之一:群己权界是一个演进过程
森定理实质上提出的是这样的问题:应该同意最小自由原则吗?卫道士和前卫青年可以相互干预对方的偏好吗?理据何在?一言以蔽之,确立群己权界的原则是什么?
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了“伤害原则”,以之作为界定“群己权界”的原则,用以保障个人免受他人或政府不当干预的自主领域。“伤害原则”指的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成员的行为自由进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就是自我保护。权力能够违背文明共同体任何成员的意志而对他进行正当干涉的惟一目的,便在于防止他对于他人的伤害……任何人的行为,他对社会负有责任的部分只能是那些与他人相关涉的行为。在仅仅关涉自身的部分中,他的独立性是绝对正当的。对于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心,个人便是最高统治者”(密尔,2009:14)。
《论自由》是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59年。密尔与穆勒是同一人,即英国哲学家John Stuart Mill(1806-1875),严复先生最早翻译了他的《On Liberty》一书,将作者翻译为“穆勒”,现在一般是将其翻译为“密尔”。[图源:zhihu.com]
然而,落实密尔提出的这一原则,首先必须界定何为“伤害”。森定理事实上给出了一个和阿罗定理相同的“个人偏好非限制域”假设,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定义自己的偏好而不受任何限制。如果尊重每个个体都可以有任何偏好,那么“伤害原则”就无法定义了,因为是否受到“伤害”须由当事人自己来定义,而任何行为都是可能会让他人感受到伤害的。如同网络世界里的一句话“长的难看不是你的错,但出来满世界溜达就不对了”,因他人“长的难看”而产生厌恶感不是很常见吗,当然,何谓“难看”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定义的。是的,抢劫杀人固然是一种得到广泛共识的伤害,而看黄碟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也是可能会对他者形成伤害的。故而,密尔的“伤害原则”并不足以作为界分群己权界的可操作性原则,也不能够消解自由悖论。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伤害”行为是在群己权界明晰之后才能得以认定的,即只有先界定了人之权利,而后才能将侵犯权利的行为认定为“伤害”。
面对自由悖论,首先,森(Sen,1970)很谨慎地表示,在处理如家里墙壁的颜色选择之类的最小自由与帕累托原则的冲突时,还是应该坚持最小自由原则。此外,他(Sen,1996)还指出要消解自由悖论中的冲突,最终的途径还是在于改变人之偏好,人之偏好应尊重他人选择认为对自己有价值的生活的自由,便如前卫青年和卫道士都尊重对方的偏好即可消解自由悖论,这一点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进而,森(Sen,1996)指出,偏好改变有两种可能的途径:其一,这是长期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其二,对偏好的自觉反思也将促进偏好的改变。
偏好可以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中得以改变的看法,与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的思想是共通的。在政治思想史上,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界定人之权利和政治的合法性,是主流的论证思路,但19世纪以来,自然法思想受到了实证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和纯粹法学派等学派的大力批判,原因显而易见:自然法不管是根源于上帝的意志、还是人类的理性、亦或是客观的正义准则,都是不可论证的。这是对自然法最有力的批评,卢梭和康德在面对此类置疑时,都没有正面论证自然状态或社会契约的存在,只是含糊地说它应该存在。一般认为,应该将自然法看作是应然的存在,而不是历史事实的存在,对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的理解亦复如此。但倘若不能消除观念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鸿沟,以自然法作为确定群己权界的来源,其说服力显然是不够的。
与以往的自然法理论家们不同,哈耶克对自然法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哈耶克并不彻底否定传统自然法理论,但他认为不能把自然法仅仅看成是“应然的”存在。为了更好地厘清“自然法”的实质,哈耶克(2000:20)首先对传统的“自然”与“人为”的规则二分法进行了批判。通常人们把规则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形成的规则,另一种是人们刻意制定的规则。以此分类的话,按照字面上的理解,“自然法”应该理解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它的确又是为人们所遵循的,故而也可以说它也是人为的。自然法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呢?哈耶克认为,把自然法进行这种二分理解是错误的,这源于人们对“自然的”与“人为的”这两个术语进行截然的二分的错误认识,这其实是受到了这两个术语的字面意义的误导,以为“自然的”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哈耶克认为,“自然法”并不能理解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能理解为是人之刻意设计形成的,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哈耶克把它称之为“人之行为而非设计”的产物,它是在历史过程中,经由人们的选择而形成的普遍为人所遵循的规则,哈耶克也称之为“自发秩序”。这不是说人的行为具有自然的属性,而是说经过历史的沉淀,人们在无意识之中选择而形成了那种普遍为人们所遵守的行为规则。哈耶克认为,传统的规则二分法忽视了此类被人们实际所遵循的、但又非人们刻意设计的规则。这一意义上的自然法,有几个基本属性。其一,这是在人类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它不是自然的东西,它的普遍性和正义性,来自于人们因为遵循这种规则而获得了益处,故而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其二,这种规则的形成综合了大量的人的行为和智慧,故而人类必须遵循这些规则的原因甚至并不能为所有人理性认知。这层意义上的规则或曰自然法,即为人类的行为划定了边界。这种对自然法的解释,颇能有效回应自然法到底是应然存在还是历史事实的诘难。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又译为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社会思想家之一。他被广泛视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但与芝加哥经济学派关系密切。他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作为《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图源:bing.com]
既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遵循这种“自发秩序”,当然也就消解了群己权界之间的紧张。由此反观自由悖论,卫道士和前卫青年在看书问题上的行为选择,总会有一个人是违背了自发秩序传统的。森在自己的论文中,并没有引述哈耶克的著作,但笔者认为,森所指出的“偏好的改变可能是长期的自然选择的结果”的看法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思想是共通的。
倘若遵循哈耶克的论断,自由边界的确立或曰权利的界定乃是人之行为所形成的一种自发秩序,这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如果因此而形成了某种被普遍遵从的偏好结构,自然是可以消解自由悖论的。但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如此的繁杂且变动不居,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能够有效地预见所有可能出现的冲突并一一形成一个相对应的规则体系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当某种从未出现的冲突来临时,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处理呢?
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哈耶克(2000:180-187)曾指出:第一,人之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建构出一套“个人权利表”以应对人类社会所有可能的繁杂情势;第二,以先验的自然权利或绝对权利为理据的自由观的说服力是不够的,自然权利具体落实为怎样的权利组合内容是有争议的,在某种权利组合面对其他权利组合时,二者皆变得毫无意义。这些论述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权利或自由的边界是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不是先验给定的。
可以再进一步阐释,为什么先验的自然权利的自由观的理据是不足的呢?这与哈耶克对个人主义的理解有关。哈耶克(2003:1)的“真”个人主义是在既批判社群主义或集体主义,又批判原子式的伪个人主义两个向度上展开的。关于后一点,他反对将个人视为一种孤立的、自足的原子式本体,而且这种孤立的原子还被赋予了道德与智识上的全涉性禀赋。这一批判,是立足于如下事实的,即个人是生活于社会之中、而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是存在普遍联系的,离开社会来讨论个人是没有意义的,据此,个人的权利也就不是一种孤立的、抽象的存在,而是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看法与亚里士多德所洞识的“人是一种政治动物”的含义是相同的,同样强调人是生活在社会和政治之中的,是不能脱离社会和政治而存在的。当代新自然法学家德沃金对权利的理解亦复如此,他说:
“权利理论是关于法律发展的理论……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总是变化的,因此法律必须随之变化”(德沃金,2002:22)。
而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也作如是观。关于人权产生的基础,马克思有三个基本论断。其一,人权内在于人的本性,是人之本性的一种需求,这一点自然无须多论。其二,人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曾系统地考察了自原始社会以来人之权利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人之权利具有不同特点这一历史事实。其三,权利和自由离不开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必然形成复杂的社会联系,这是人权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故而,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1972:12)。
也正是因为如此,罗尔斯所构建的人们在无知之幕背后缔结社会契约,以形成普遍性的正义原则的理论论说,脱离了现实的历史场景,从而削弱了其理论的可信性。
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出自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意思是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它也不会得到过多的利益,因为在定规则的时候幕布下的人们会认同那是不必要的。[图源:zhihu.com]
五、消解自由悖论路径之二:基于程序和理性审视的共识形成
诉诸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以厘定自由之边界的理路,仍然也只是一种哲学观念,还需要寻找一种现实的落实机制。试问,随着社会的演进,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会呈现新的情势,则自由边界须随之调整,面对多元化的个体偏好和多元化的价值认同,与时俱进地调整自由边界,必然要求调整人之偏好,如卫道士和前卫青年双方至少一方要改变自己的偏好,他们为什么会改变偏好以及如何改变偏好,其中的理据与实现机制是什么?
理据与实现机制之一,来自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想。森(Sen,1996)指出,布坎南1954年的文章的主张是合理的。这须从阿罗定理说起。
阿罗(Arrow,1951)所提出的问题是:可否遵循某种规则如多数票原则,将个体的偏好或判断加总成一个社会偏好或社会判断。他的经典研究证明,如果以五个常识性公理为前提,则将个人偏好集结为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会出现“投票悖论”,这就是著名的阿罗定理。拯救阿罗定理的努力一直都在进行,但已有的研究表明,只要坚持阿罗的基本分析框架,所有的努力都只不过是遇到的一些新困惑、导致了新的不可能性定理不断被发现而已。
针对阿罗定理的论证逻辑,布坎南(Buchanan,1954)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批评。第一,阿罗提出的“社会偏好”概念是不成立的。布坎南指出,阿罗在这里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他假定了“社会偏好”的存在性,这是一种拟人化思维的谬误,即认定所谓“国家”、“社会”、“秩序”之类的现象具有整体性的实体地位,如同具有感知能力的有机体一样。而事实上,社会只不过是个人的某种集结而已,社会并无行为能力和感知能力,故社会并不是有效的偏好主体;若将社会偏好理解为个体偏好的某种集结,则社会偏好也不过是立足于个体偏好而派生出来的某种现象描述,不可以将社会偏好理解为独立的、甚至是脱离于个体的客观存在。由此,阿罗试图求得某种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偏好的想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其次,布坎南(Buchanan,1954)认为,社会选择应该是一个“过程”。尽管阿罗声明他所研究的是“集结社会决策的过程”,但事实上却偏离了这一点。无论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规则还是市场选择,本质上都是一个自由选择过程,有意义的问题是“过程”,研究的核心应该是“投票过程”或“市场交易过程”、分析过程中的人之行为如何呈现。一言以蔽之,布坎南的核心看法是,改变、集结个体偏好是可以在一个“过程”中实现的(布坎南、塔洛克,2000:90)。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其一,这是一个规则或程序之下的行为。与社会选择直接在不同偏好、既定规则之中求解一致同意不同,公共选择区分了两类行为选择(布坎南、塔洛克,2000):对规则的选择和规则之下的行为选择。首先确认一个规则(具有立宪意义的原则),这个规则规定了采取集体行动必须满足的条件和程序,如果这个规则得到了一致同意,那么执行这个规则而形成的任何决议逻辑上也就是一致同意的结果。首先是确认规则,而后是在规则之下采取行动,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这是两类不同的行为逻辑。其二,布坎南(Buchanan,1954)认为,决策过程中的讨论是重要的,个人价值观能够并的确会在讨论过程中发生变化从而达致共识。在阿罗定理中,投票过程中人的行为、目标和偏好是被假定为不变的,但布坎南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在决策过程中,经过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人与人之间会相互妥协、偏好会随之改变,从而会达成事实上的一致同意,据此不会出现不可能性悖论。这也诚如奈特(Knight,1947:280)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