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按:今天看到泸县太伏中学一学生死亡事件的相关视频,整个人心情都不好了,惨不忍睹。真想一头栽进历史里,不愿看这样残酷的现实。
网络上流传的视频
泸州少年校园"坠亡“事件,到底谁在造谣?
原文
http://mp.weixin.qq.com/s/fCps7PdF76HU1GJa8LTXj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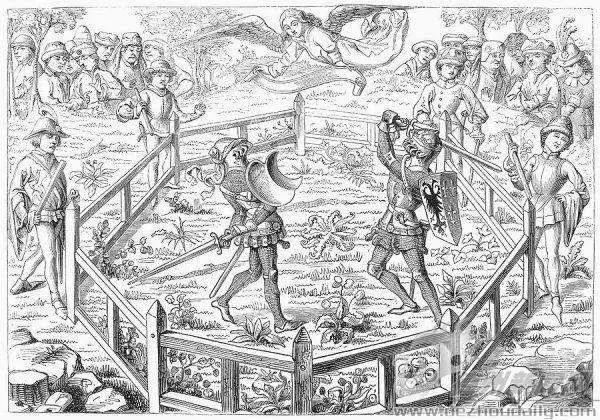
罗伯特•巴特莱特:《中世纪审判》,徐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神判的替代
本书第三章所提出的论点是:神判的功能并非潜在的或不明确的,对神判使用者的同时代人而言,它是相当明确的某种事物。其功能是在常规方式无法提供证明的情况下确保证明。那么,人们自然会追问
13
世纪神判废除后,如何满足这一功能。需加以解决的疑难案件依然存在。倘若不再适用神判,必然要运用其他方法。
作为对神判消亡的回应,证明领域出现了三大发展:现行证明方式扩展至先前由神判解决的案件;在英格兰和其他一些国家,则迅速向审判陪审团发展;而最重要的一种是,替代神判的刑讯之兴起。
首先出现的过程即现行证明方式的扩展,可通过图尔奈和佩罗纳
(Péronne)
特许状中的奇特情形加以说明。
1188
年授予图尔奈的特许状规定冷水神判适用于两种情形:无证人的杀人和无证人的夜间伤害。第二项规定尤具启发性。相关条款的内容如下:
若一位持有武器之人在日间或夜间伤害他人,而受伤者可就此提出证人,则行凶者须赔偿
10
镑
……
但若其无法提出证人,且该行为发生于日间,则被告应以七倍的共誓涤罪洗刷嫌疑。然而,若该行为发生于夜间,则被告应以冷水神判洗刷嫌疑。
依照环境所容许的确定性程度,此处存在证明形式的一种敏感的阶段性变化。提出证人显然是决定性的,并对案件一锤定音。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情势则更为困难,但即便如此,仍可做出合理区分。日间袭击不同于夜间袭击,而在日间袭击案件中,允许共誓涤罪似乎合情入理。共同宣誓人将证明被告的良好声誉,甚至可能有详尽可靠的理由确信其无罪。夜间伤害则更为棘手。在无证人的夜间袭击案件中,确实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诱惑,即想弄明白谁能知晓事实真相。恰恰在这点上,神判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上帝知晓真相,且被请求昭显
。
图尔奈的特权形构了佩罗纳和其他一些法国北方城镇的那些特权模式。然而,在晚于其图尔奈范本
20
年或更长时间之后,该佩罗纳的特许状家族显示了对其范本的惊人背离;出于我们的目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它们排除了神判。图尔奈特许状规定神判适用于无证人的杀人,而后来的特许状仅明确规定被告
“
应通过市镇司法官
(
échevins
)
的正当审判来洗刷嫌疑
”
——一则给法庭留下太多裁量余地的含糊其词的惯用语。在图尔奈特许状规定神判的另一种情形即无证人的夜间伤害中,神判的遗漏既留下了文法上的空白,又导致了程序的缺失。比较佩罗纳的规则与上文引述的图尔奈的规定,这一点便跃然眼前:
若一位持有武器之人在日间或夜间伤害他人,而受伤者可就此提出证人,则行凶者须赔偿
10
磅
……
但若其无法提出证人,且该行为发生于日间,则被告应以七倍的共誓涤罪洗刷嫌疑。然而,若该行为发生于夜间,他同样应以七倍的共誓涤罪洗刷嫌疑。
这一规定的前后矛盾和尴尬显示了神判被废除后所遗留的空白。神判废除的结果之一,便是先前已作区分的情形——无证人的日间袭击与夜间袭击——如今被等同视之。证明尺度的微妙转化已变得更为粗糙。
许多其他例证表明,在神判废除之处清楚地扩大了共誓涤罪的范围。而且更一般而言,特别是在教会法院和城市法院,共誓涤罪在神判遭受谴责后的时代中必定已成为最常见的证明形式之一。正如我们所见,在某些
12
世纪的城市特许状中,业已存在以共誓涤罪取代神判之动向。事实上,通过共誓涤罪来证明的制度在整个中世纪都非常重要。历史学家早已倾向于将其衰落期提前,并倾向于将其与神判联系起来置于
“
非理性和形式化的证明
”
之名目下,设想它们历经岁月流逝而为理性的证明所取代。这一点模糊了共誓涤罪有时取代神判的事实:
“
若一位女子被提起某项指控且该指控无法证实,我命令,她须以誓言而非热铁来洗刷嫌疑。
”
神判的废除可能会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交于法官之手:在某个弗兰德斯人的市镇,神判为一种
“
在法官看来可与热铁神判相匹敌的
”
证明所取代;但还有一种发展,赋予法庭上另一群体甚至更大的权力,即刑事审判陪审团的兴起。陪审团在
12
和
13
世纪的数个欧洲国家中得以发展,但最著名且最具历史影响的例证是英国的陪审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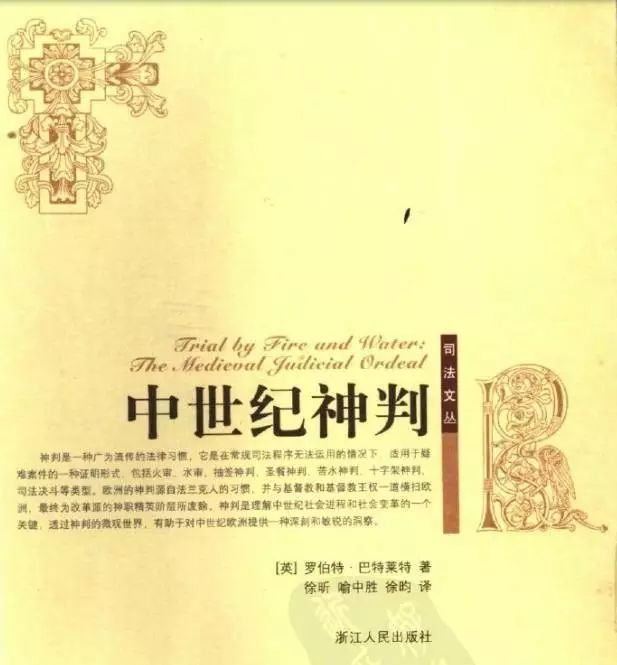
起诉陪审团存在于
12
世纪的英格兰
(
可能还更为古老
)
。其任务是起诉重罪犯
,即证明指定的个人被普遍认为犯有重罪。
不过,他们并不决定那些被指控者有罪或无罪。这一点要么通过
“
在法官面前的咨审调查与纠问
”
来实现,要么通过神判来证实。起诉陪审团因此不是审判陪审团。然而,经过
13
世纪早期的进程,它们发展为审判陪审团。被指控的重罪犯如今可“将自身托付给陪审团”,即同意接受陪审团的裁决。随着该程序最终明确定型,布雷克顿以如下方式对其进行描述:法官向陪审员们致辞,
“
此人……被控死刑的此人……否认死刑指控……而在该问题上,其有罪或无罪取决于诸位的金口玉言……因此,我们告诫你们,基于那约束你们的上帝信仰和凭你们宣告之誓言,你们须让我们知晓事实的真相。
”
裁决之后立即
“
释放或定罪
”。
许多法律史学家业已评论过神判废除与审判陪审团兴起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主张,
1215
年的决定
“
留下了一处空白
”
、“扰乱了所有
(
法律上的
)
安排
”
,并导致
“
实践和智识上的混乱
”
。陪审团填补了这一空白:
“
英国人所倾向的进路因此是扩展陪审程序,以填补神判废除所遗留的巨大空白。
”
神判废除所导致的最初混乱,体现在
1219
年向法官颁发的王室训令中。在禁止神判后,它继续提供某些特别措施以处理刑事被告人,并做出决定:
“
由于我们的议事会目前尚不会就此事项做出任何更明确的安排,因而对你们如何在你们的巡回法庭上遵循这些指令,我们将其留待你们自由裁量。依你们的自由裁量及良知处理此事,尽你们所能查明涉案人的品格、犯罪性质以及事实真相。
”
此时,正如我们在其他国家所观察到的,该证明方式的废除将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交托法官之手,至少暂时如此。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
(1216~1272
年
)
,审判陪审团的发展又再次限制了这一权力,陪审团替代神判这一旧的独立来源,而成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裁决来源。
1231
年,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总管解释说,在修道院的法庭,陪审团的选任
“
合乎自战争
(
即
1215
年至
1217
年的内战
)
以来的习俗,因为他们在战前进行火审和水审
”
。依此人所见,
1215
年前后是神判时代向陪审团时代过渡的时期。
神判的消亡直接导致审判陪审团的产生并非仅限于英格兰。一种非常类似的发展也出现在丹麦,而且在这一点上有着明确的书面证据,它说明了审判陪审团实际上被设计来取代神判之事实。在瓦尔德马二世于
1216
年或稍后发布的一项命令中,我们看到:
由于教皇业已禁止所有基督徒进行热铁神判,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将自身排除在该一般规则之外。因此,就我们应颁布何种更为普遍接受的证明形式来替代热铁的裁决,我们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征询了我们重臣的意见
……
我们命令,任何被控杀人者皆应被带至法庭,原告应指定来自被告所在地的
15
人;被告可否决
3
人;其余
12
人将宣誓,
15
日后,他将会因无故杀人而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或是他将会因杀死仇敌而支付赔偿金,或是他们应以誓言彻底洗刷其嫌疑。
有关创设新的法律程序以填补
1215
年决定所遗留空白的明确证据,必定使得维持神判在
12
世纪业已消亡或衰退的观点更为困难。
关于陪审团取代神判,还需提出最后一点。有一种观念认为,陪审团不仅实现了与神判相同的功能,而且带有相同的性质。特别是,陪审团裁决的不可预测性令人联想起神判程序。就像茹翁·德·隆格雷
(F. Joüon de Longrais)
所指出的那样,
“
他们的裁决无需讨论而形式化地予以认可
。它具有古老的证明方式所有陈旧的顽固性。它作用于实质性问题,即事实问题
,就像是一种神判。人们无法质询其理由,更不用说重新启动它
”
。它约束法官,正如神判曾约束他们一样。正是这种无法预测并具有拘束力的特性,使我们得以弄清
“
陪审团最初被视为一类新型神判
”
的主张之含义。
然而,审判陪审团这种
“
更新的神判类型
”
仅在少数国家得以发展。
13
世纪真正蓬勃发展、填补了早期神判所扮演角色的程序是刑讯
(judicial torture)
。
1228
年维罗纳
(Verona)
的《民法文集》
(
Liber juris civilis
)
最早在立法上提及刑讯,它显示了刑讯何以被明确视作神明裁判的一项替代物。随着
13
世纪的逐步推进,刑讯的运用日益频繁,最初针对意大利城市中的刑事被告人,后来则在圣路易时代的法国为宗教裁判所
*
和王室法官所采用。
刑讯兴起的一个重要激励是罗马法日益增长的权威和对罗马法的精通。不同于中世纪早期欧洲的习惯法,罗马法针对证人和嫌疑人的刑讯有明确而正规的定位——
“
为侦查犯罪之目的而使用刑讯合乎习惯
”
。在很大程度上,这仅意味着对奴隶的刑讯,但在特定情形下,自由人亦可能遭受刑讯。
正如神判在罗马法中的缺席严重损害了神判在
12
和
13
世纪的可信度一样,罗马法对刑讯的规定促进了此习惯在上述时期内的复兴。学院派的法律学者、教会法学家和世俗立法者甚至一致认可他们所敬畏的这一罗马法的构成要素。他们对罗马法文本的解释使之确信,
“
古代的智者们认为实施刑讯以榨取真相是正当的
”
。
然而,
13
世纪刑讯的复兴不能完全归因于罗马法的诱惑。刑讯不仅规定于罗马法的文本中,它对于新近发展起来的纠问式程序的机能同样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其精致的证明理论完备之后。因为伴随着罗马法的学术研究,
12
和
13
世纪见证了新型司法程序的产生,这些程序极大地改变了法庭上的权力平衡。在那个时代之前,刑事和民事案件通常由受害人提出和追诉;法庭随后决定应适用何种证明方式;而倘若案件不利于原告,原告则可能遭受惩罚。随着纠问技术的发展,教会和国家的官员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得了启动程序和在法庭上扮演更为积极角色的权利。
“
纠问式程序最重要的方面
”
,爱德华·彼得斯
(Edward Peters)
写道,
“
在于排除了原告的法律责任,并日益提升了法院及其代表的权威之行动自由和权力
”
。因此,一位积极的纠问式法官如今是在便于调查、威吓和折磨嫌疑人的情况下面对嫌疑人。
因此,中世纪后期散布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的纠问式程序,造就了一种负有刑讯嫌疑人之义务的法庭氛围。然而,罗马
-
教会法相结合的证明制度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因为尽管法官在纠问式程序中的权力不断增长,他仍受制于极为严格的证明规则。罗马法学家和教会法学家的共同观点是,
“
在刑事案件中,证明应清楚明确
”
,而在成熟的制度内,这意味着在不能对犯罪提供一人以上的目击证人的情况下,只有犯罪嫌疑人的招供可视为充分的证明。进而,在许多制度中,惟有嫌疑人招供,方可处以死刑。严格适用所谓的
“
法定证据
”
,因而极大地强调了榨取口供:
“
发明它的法律学者通过制造另一问题来解决某个问题。他们建构了一种可处理简单案件但无法解决疑难案件的证明制度。他们的制度可处理大多数公开犯罪案件,但很少能应对隐秘犯罪案件……有关证明的罗马
-
教会法无法孤立地使用。
”
因其无法孤立使用,便由刑讯加以补充。在
“
疑难案件
”
中,当嫌疑人名声不好或存在环境证据
*
时,刑讯便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大多数欧洲国家通用的司法诉诸手段。
这种对疑难案件的新型解决方法在几个方面不同于神判这种旧方法。它旨在榨取口供,而非即刻揭示有罪或无罪。它并不诉诸上帝,也不依赖牧师的参与
(
尽管刑讯的工具也可能被祝福
)
。它对被告怀有严重的偏见,因为被告唯一的救济便是忍受可能经常翻来覆去的拷打。相反,当被告承受神判时,它几乎总是一次性的考验,倘若通过则会导致一项明确的无罪宣判。刑讯,一种操纵于人类之手的司法程序,比上帝的审判更为冷酷无情。
尽管有这些差异,但相当明确的是,刑讯在
1200~1700
年期间履行了神判在
800~1200
年期间同样的功能。例如,
1200
年前使用神判的案件与
1200
年后采用刑讯的那些案件存在惊人的相似。如同神判一样,刑讯也是一种最后的诉诸手段:
“
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当真相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发现时,人们便被施以刑讯。
”
它适用于像异端一样
“
不可见的
”
信仰犯罪。
12
世纪的异端审判经常在戏剧性的火审或水审中达到高潮;中世纪后期那些异端审判导致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室和刑讯室的秘密行动。甚至在像英格兰这样刑讯极为罕见的国家中,过去常以神判审理的叛逆罪也往往通过刑讯来处理。巫术审判是另一例证,下文将更充分地予以讨论。
1231
年腓特烈二世对其西西里王国发布的《梅尔菲宪法》或《奥古斯都法典》,提供了刑讯取代神判之方式的一个恰当例证。在深深烙下罗马法印记的此部法典中,腓特烈轻蔑地批评并禁止神明裁判。他同样就某些情形下对嫌疑人实施刑讯作出了规定:
如果,通过因吾皇之关爱而提供的救济方法,在不能利用明确的证据来发现犯罪者时,我们已正当地救济了那些遭受秘密损失或伤害之人……那么,我们更加坚定地确信,对于任何一方的父、子、亲属在任何地点被秘密杀害的那些人,若不论如何查探,这种十恶不赦罪行的凶手皆无法通过任何调查而被发现,将其置于我们的保护之外是不合适的……
(
在明确规定了纠问程序后,腓特烈的法令继续规定
)
但倘若在此纠问程序期间,任何不名誉之人被指责犯有该杀人罪,即便纠问程序不能完全证明对其不利,我们仍责令,应继续对那些下等阶层的不名誉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