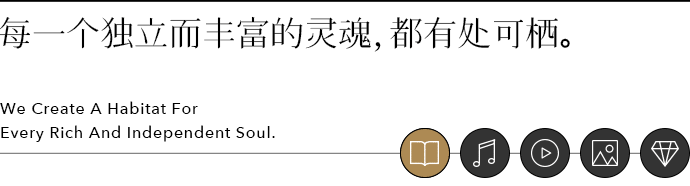
【每周一书】是由单向空间编辑部推出,代表着单向空间选书标准的栏目。每周,由单读公号、单读 App、单向街书店公号三个平台发布,每一本书都是我们的郑重之荐。我们希望通过【每周一书】,带你在新书之海拾贝;更希望通过【每周一书】,我们能共同跃出书海,奔向这个时而躁动不安,时而寂静无语的世界。
2017 年初,李静睿获得第二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奖,今年 6 月份,她出版了最新作品《北方大道》。书中收录了八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这些故事表面上没有什么关联,写政治写爱情,有世道有人心。然而,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这是关于年轻人的故事,关于软弱和犹疑的故事,关于选择的故事。
李静睿的语言,始终保持着沉稳、细致、柔长的节奏,但是温柔中藏着锋芒。她用简单的文字,写冷淡的场景,和模糊的情绪。但就在这一片含糊中,仍能看到她面对人生时,那种严肃而清明的勇气。

一个小说家/而非记者的位置
吴琦
我总觉得,跨越“界限”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因为它锻炼的是这样一种能力,你突然从自己埋头呼吸的空气中抬起头来,获得一种耐心和兴趣,去阅读他人的生活,那些离你很近或很远的地方,那些平常你自己经常忽略或视而不见的细碎繁琐的事和感情,他人的容貌和衣装,动作和表情,以及他们一生跌宕起伏或者平淡无奇的轨迹。
但有时候,文学的现实和社会的现实一样令人沮丧,那些阅读文学作品、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最后并没有完全习得文学教给我们的道理,他们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听得懂人心、看得见世界。最坏的状况,文学成了一少部分人的战利品,成了他们的权力和面具,用来划分敌我,排斥他人——那不正是文学以及阅读过程本身所反对的事情?

《北方大道》封面
话扯远了,其实是要推荐李静睿的新书《北方大道》。她就是那类打破界限的作者,包括她的经历,她写的东西。从记者到作家,看上去顺理成章,实践起来没那么容易,能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和内容,这不是大众传媒工作必然携带的任务;能不能被所谓的文学界接受,那是另一个问题。她的小说偶尔也以新闻业为背景,但叙事者的角色已经脱离记者的身份和语境,没有陷入一个传媒工作者喋喋不休的自我陈述。新闻业成为文学的容器,打开丰富的社会断层,撑开了人的感受与观察的毛孔,也可以说,成了故事的哨所。而最终完成文学构筑的,是她的写作在与过往身份保持血肉关系之外,又与其保持了柔软的距离,呈现出文学而非新闻所具有的那种质地,像一层轻薄透明的覆膜,裹在杂乱粗糙的现实表面,不再等同于生活,而成了生活的陈列。
在我的了解里,李静睿是个沉默但不寡言的人。她在人前害羞,不习惯公共讲话,但在微博、微信这样其实广泛得多的互联网平台上,她言辞犀利,从不忌惮什么。另一个发现是,无论是公共言论还是私人写作,无论是讲述角色还是她自己的生活,她的语言都没有什么摇摆或分裂,始终保持着一个沉稳、细致、柔长的语言节奏,温柔中露出锋芒。那已然是一个小说家的位置。
我也总是很喜欢她给书起的名字,比如《微小的命运》,再比如这一本新书《北方大道》。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设置,也没有妄语,但读过小说之后,你悄悄地沉默地从中读出了隐喻。

▍下文节选自《北方大道》
《北方大道》
李静睿
北方大道
纽约大概从早上六点开始下雨,明明睡得黑沉,却清晰无误听见水声。
林立成梦见自己要把水龙头拧上,但无论如何拧不紧,梦境有一种切实的焦虑,让他渐渐下沉,一路坠至噩梦,又终于挣扎着醒过来。黑暗中他睁开眼,又望向黑暗,他倒是习惯,反正不是这个噩梦,也会是另外一个,相形之下,他愿意去拧一个永远拧不紧的水龙头。
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刚好六点半,林立成发现自己忘记关窗,天光渐亮,书桌上站着一只鸟,淋湿了翅膀,正在一口口啄食他最后两片全麦面包。面包本来应该放进冰箱,但前几天冰箱坏了。家里的东西分批坏掉,厕所里总是黑着灯,四个灶眼有三个出不了气,沙发的一只腿瘸了。每天晚上林立成读一会儿书会突然歪一下,随后又调整回来继续读。
房东是个中年广东男人,舍不得花钱请工人,被林立成逼紧了会自己拎个工具箱过来,敲敲打打一会儿,有时候灯就又能亮几天。林立成站在边上看着,也会微弱地表示一下意见:“你这样不行,美国的房东都是包修理的……你再这样我就去投诉了。”其实他也不知道去哪里投诉,他是没有毕业证的北大国际政治系学生,来美国后四处做了一通访问学者:哈佛、耶鲁、哥大,最好的大学,最高的奖学金。他最远去到芝加哥,夏日清晨,和当时的女朋友在密歇根湖边做爱,两只海鸥远远看着他们,叽叽咕咕,表达好奇和疑问,林立成竭力想集中精神,却还是渐渐疲软下来,最后只能拉上拉链。他忘记那个女朋友的模样,却记得她温柔地握住他的手,说:“没关系,以后还有时间。”但他们很快分了手。走了大半个美国,最后回到纽约,却也只是每天打开中文的《世界日报》,林立成没有住在纽约,他只是住在法拉盛。

房东赶紧递上两根烟,广东话夹杂着普通话说:“不要这样啦,大家都不容易啦,我还欠着移民律师两万块啦,请个工人,什么都不做,上门就是八十啦,大家都不容易啦……来,抽支烟,我表哥从国内带过来的软中华。”烟还没抽完,林立成又已经软了,他总是太容易软下来,所以去厕所还是得拿上手机,APP 里有一款手电筒,白晃晃地照出前路,强光灼人,让阴影处更显黑暗。
上完厕所后他彻底醒了,索性抽了支烟,十四块一包的硬中华。那只小鸟还在,面包已经被啄出一个洞,林立成吐出烟圈,又努力想让烟圈穿过面包上的洞。小鸟停下来,歪头凝神看那烟圈渐渐散开,林立成突然认出,这是一只普通燕鸥。他前一个女朋友——可能只称得上女人——喜欢鸟,上过大概十次床之后,拉着他去过一次中央公园。两个人坐七号线到时代广场,然后一路往北走进公园,因为坐的是慢车,晃晃荡荡快一个小时才到。走到一半林立成就开始坐立不安,许久没有出过法拉盛,一出地铁,他惊恐地只想找地方撒尿,好像他是一只养在皇后区的猫,唯有如此才能划定活动范围。最后他是在 AMC 电影院边上的一家麦当劳里完成这件事,撒到一半进来一个黑人,林立成赶紧穿上裤子出门,导致整个下午他都觉得自己处于未完成状态,肚子里哐当作响,进了几次卫生间还是如此。
沿着第五大道走到尽头,中央公园照例弥漫着酸酸的马粪味,混杂一股法拉盛韩国餐馆里常有的野葱香。马车上安着污脏的红色丝绒座椅,林立成担心女人想坐马车,他不想出那五十美元,更不想在曼哈顿上城这样明目张胆地存在;公园附近住着不少他认识的人:哥大的访问学者,对八十年代满怀想象的留学生,那些搞东亚研究的美国人。林立成担心会在这里遇到他们,在草地、落叶和有蓬松大尾巴的松鼠前尴尬冷场;中央公园有一种明亮的柔情,让人难以启动对往事的回忆,而除了往事,林立成觉得自己和他们无话可说。到了现在,他和谁都是无话可说。

还好女人只是拉着他一路走到湖边,指着地上的一只鸟说:“看到没有,那是普通燕鸥,Common tern,还有一种有黑眼圈,叫加拿大燕鸥,Forster's tern。”林立成竭力表达兴趣,燕鸥浑身雪白,鲜红色的尖嘴和爪子,头顶是一片漆黑羽毛,林立成想,配色倒是不错,像一套性感内衣,也许女人穿上会好看。做爱时林立成喜欢开灯,看她苍白皮肤下的青色血管,和眼窝下面的淡青痕迹,她可能更接近于加拿大燕鸥。过了一会儿那只燕鸥飞走了,又过了几天,那个女人也离开了法拉盛,林立成没有留她,他喜欢晚上睡觉前反复抚摸女人的大腿,也舍得周末带她去东王朝吃个海鲜自助餐,但他并不知道如此往下,他们还能走到哪里。两个人在一起刚好三个月,一段既不让人尴尬、也说不上遗憾的关系。
林立成半年没有做爱了。大年三十前后那几天下大雪,他把暖气开到 72 度,还是每晚三点准时被冻醒,下半身尤其冰凉。大年初三他想找个妓女,算是过年,走到缅街上茫然逛了半个小时,平时无处不在的小广告此时却齐整整地失踪,好像这个行业也在休春假,街头锣鼓喧天,几只短短的龙跳进商铺讨要利是。晃了半天一无所获,林立成只好在新世界商场楼下胡乱吃了碗羊肉烩面,之后回家继续上网找,他斟酌良久,却不知道用什么关键词搜索。正打算放弃,却在门缝里看见一张彩色小广告,上面印着一个看不清样子的大胸少女,穿玫红色三点式,广告词是“少女上门服务,小身体好酥”,下面跟着英文和西班牙语。法拉盛有时候会有墨西哥人过来,但据说他们喜欢胖胖黑黑的中国女人,并不是眼前这个雪白少女。广告上的电话林立成最后没有打,当天晚上雪就停了,气温慢慢往上走,有时候半夜醒过来,也会思念很酥的小身体,他就竭力回想那张广告上的大胸少女:浑身上下 P 成一片惨白,隐隐约约露出粉红色乳头,然后自己完成了这件事。那张小广告林立成没有扔掉,一直放在窗台上,他想,还会有下一个冰凉冬天。
今天晚上林立成要去见王凌薇,大四冬天他们在博雅塔下接吻,嘴唇触及嘴唇,林立成没有伸出舌头,他想,没关系,以后还有时间。燕鸥飞走之后不久,雨也渐渐停下来,林立成犹豫了几分钟,坐下来把中间有洞的面包片吃了,口中的食物略微潮湿,但他并没有别的选择,这是最后的面包。他看见窗下的荆条正开出第一朵黄色小花,春天已经到了,这是另一个春天,原来他总是没有选择,原来他和王凌薇不再有时间。
失踪
早上十点,黑霾沉沉。我在八里桥批发市场买了螃蟹,进小区门禁前又去看了看邮箱,九点出门时我已经看过一次。过去两个多月里,我每天下楼十几次查看邮箱,除了买菜往返,我还热衷于下楼倒垃圾,吃一粒橙子倒一次,扔两张纸又是一次。
这次里面多了一个黑信封,终于,夹在我的信用卡账单、梁一宁收到的圣诞贺卡和宜家新品目录中间。略带磨砺手感的黑色纸张,没有封口,没有邮戳,没有收信人和寄信人。我进房间后来不及换鞋,坐在地板上打开信封,孤零零一张 A4 纸,宋体四号字加黑加粗:
梁一宁,法定失踪。阅后即焚,不得拍照,一经发现,状态失效。”
就这么些,我心里知道,二十个字加上人名。又读了一遍,反复确认“法定失踪”四个字。蒸螃蟹的时候才把它烧了,变成一小撮黑灰,冲进下水道。螃蟹很肥,膏满溢出来,我坐下来吃螃蟹,姜醋里加糖。又一个螃蟹。
梁一宁失踪那天,十月十七日,早上赖床,他从后面抱住我,说:“我们今天吃螃蟹好不好?我突然有点馋,等会儿一起去八里桥?”最后我一个人去了,梁一宁有邮件要回,没人替我拎菜,我穿平跟鞋出门,习惯了两个人,只觉得右边空荡,好像被人生生砍掉一只手。市场上太湖蟹四十五一斤,我买了四个,两公两母,刚好两斤。又走五分钟到花鸟市场,买绿色龙胆和绿色百合,梁一宁喜欢奇怪的植物,绿色的花,红色的叶子。

回到家里不见梁一宁,没带手机,穿走皮鞋,拖鞋整整齐齐摆在地毯上,电脑停在他回信的页面,我出门前给他泡的竹叶青浅下去三分之一,烟灰缸里有两个烟蒂。我把那四只螃蟹养在汤锅里,蟹钳疯狂划过不锈钢锅壁,我整夜不睡,听那尖刺的声音,龙胆和百合散放出悠悠香气。
第三天螃蟹终于死了,我终于接受这件事:梁一宁失踪了。那天晚上把四个螃蟹都蒸来吃掉,死螃蟹有腥味,蘸剁椒也压不下去。半夜胃痛,起来呕吐,房间漆黑,只有无线路由器闪着蓝光,我坐回床上,黑暗中望着前方,并没有哭,万物理应寂静,我还是听到扰人的声音。
我惦记梁一宁想吃螃蟹,就每天去买一只,把他的拖鞋摆好再出门。去八里桥要坐三轮车,相熟的师傅只收我八块,他开始几天问我“你老公呢”,我说“他今天有点事”,持续了一段“今天有点事后”,他不再问了,把价钱调整为往返十五,在市场门口等我二十分钟。寒风勾走魂魄,我坐上一辆能拉上玻璃小窗的电动三轮车,马达声突突,我靠着左边坐,右边是师傅的抱枕,红布污脏,上面绣着两只鸟。回到家里,拖鞋原地不动,我把它放回鞋柜,装作这件事并未发生,又一天过去了。
太湖蟹下市,变成梭子蟹,前缘有锐齿,末齿带倒刺,我两次戳破指头,血滴成花朵形状,渗进米白色餐盘。吃了太多螃蟹,胃寒如冰,暖气片烫手,我还是整日喝滚水。今天这只梭子蟹重六两,卖蟹的人打包票说是满黄,我在厨房里犹豫片刻,打开门把它放了,看它歪歪扭扭穿过走廊,我希望它恰好搭上电梯,带着满肚子蟹黄,去到自由之地。出小区左拐就是通惠河,它只需走三百米,穿过垃圾箱、停车场以及一个复杂的十字路口,垃圾车呼啸而过,郊区中巴车强行变道,也许它能躲开这一切,抵达三百米外的清澈小河。
没有螃蟹,我煮了碗素面,泡在酱油汤中。这是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傍晚,窗外有混沌灯光,困意袭来,我突然意识到梭子蟹长在海里,我不过放它走向死亡。
法定失踪是最好的一种失踪。梁一宁说,缩在被子里,咬着我的耳朵。手机放在老远的地方,房间漆黑,拉上密密窗帘挡住月光。
除了法定失踪还有什么?我问,紧紧搂住梁一宁的腰。盛夏,两个人身体濡湿,耳垂火烫。让我们激动的不是性欲,而是禁忌与秘密。
非法定失踪。梁一宁悄悄说。
那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反正法定失踪更好。
我“哦”了一声,从被子里钻出来透气,梁一宁也起身抽烟,烟气在空调房里缭绕不散,我们开始大声说话,讨论英剧 Black Mirror 的剧情。在自己家里,我们的声音也太大了。
那天晚上本来邱永和林零要来吃晚饭,他们住西边,我们住东边,隔着整条长安街。两个月没见,饭局是林零临时约的,中午打电话过来,时间紧张,我只买了条鱼,烧一锅邱永爱吃的红烧肉,手一抖,放多了冰糖。
六点半,我刚把桂鱼放进蒸锅,撒上姜丝,林零到了。她一个人,打扮齐整,真丝印花连衣裙,五厘米高跟鞋,涂着玫红唇彩,更显脸色恰白,拎一袋子葡萄。我以为邱永在楼下停车,桂鱼熟了,人还是没上来。梁一宁对我使眼色,我悄悄撤掉一副碗筷。

三个人默默吃饭,红烧肉没人动,空调开得低,油渐渐半凝,让肥肉更不可下咽。林零急切地吃鱼,最后只剩一副骨架,她把骨架夹到盘子里,放下筷子,神经质地鼓捣那些鱼刺。我在边上替她剥好葡萄,浅绿色果肉,看起来极酸,她并没有吃。
梁一宁打算收拾桌子,林零示意我们过去,盘子里鱼刺摆成一个“法”字。她抬头看我们,两腮微红,眼睛闪光,又随手把鱼刺拨乱。梁一宁洗碗,我把垃圾拿下楼,林零也要走了,跟着我下去,我们在小区垃圾桶前拥抱,食物即将腐败的味道逃无可逃,两只流浪猫蹲坐一堆香蕉皮上,眼巴巴看着我们,林零小声说:“你让梁一宁好好的。”猫喵呜跑远,又回头望过来,绿眼睛闪出鬼光。
后来就到了晚上,梁一宁告诉我“法定失踪”这个词,床上突然漫出鱼腥味。我们重新躺下去,他又把我拉进被子里,压低声音说:“听说会有个黑信封。”
“什么黑信封?”
“法定失踪,家人会收到一个黑信封。”
“有什么用?”
“不知道。反正会有这么个黑信封。”
“林零收到了?她为什么不说?”
“她不敢。”
现在我知道了,的确不敢。我半夜醒过来,默背那二十个字,反复回忆前面的人名到底是不是“梁一宁”,想得越细,越失去信心,到最后忘记“梁”字的正确写法。我不喜欢他的名字,因为“宁”字又有 N 又有 G,四川人读不出这个音,我总读成”一林”。
这么一听又像在叫潘意林,经济系 99 届的那个男生,个子算高,脸上长痘,剃平头打篮球。潘追过我一段,认真地追求,去自习室堵我,情人节送花,平安夜给我在学校电台点歌,Sarah Connor 的 Christmas In My Heart,我在食堂里打饭,大喇叭里传出沙沙歌声 “ Tomorrow may be grey,We may be torn apart,But if you stay tonight,It’s Christmas in my heart ”。
我挺感动,但我已经有了梁一宁,他知道有人追我,不怎么高兴,却也没有太不高兴,毕竟平安夜我们住在一起,学校外的小宾馆,我们存了一周钱,两个人合吃一份蔬菜三两饭,才够钱去开房间。为了和潘意林区分开,我后来习惯了连名带姓叫他,梁一宁,梁一宁。现在四下寂静,我叫出声来,梁一宁。
房间有回声,我们买了一套大房子,我突然想起来,今年的圣诞节已经过了。那天我做了什么?吃了螃蟹,通宵不睡,大概如此,唯有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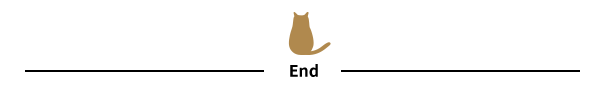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北方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