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点链接,以
语音重温最新节目
内容
“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中共
18
届六中全会提出来之后,习近平总书记
19
大的政治报告中给予了再一度的确认与强调,相信此一有关房屋及房屋产业的新定位,必将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从
1949
年开始算起,新中国的房屋政策迄今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从
1949
到
1998
,是阶段
1.0
。在这个阶段中,虽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了市场经济,但基本上不存在民营的房屋产业,房屋的生产与供给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是典型的稀缺经济,于是从
1998
年开始,决定把房屋并同教育与医疗,开始启动三大民生改革,分别叫房政、教政与医政,这就进入到房屋政策的阶段
2.0
;(二)阶段
2.0
从
1998
到
2016
,所谓的房改就是把基本上仍处于计划与公有体制的房屋产业大力地扭转,转型为市场及民营体制,这种改革与转型,大方向是正确的,生产力、效率乃至于供给都可以获得提升,但问题出在把房屋产业过多地交给了市场与民企,政府应有的角色与功能都缺位了,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初期阶段是不合适的。试想从
1949
年到
1998
年,人口从四、五个亿大幅增加到九、十个亿,房屋增加却极为有限,换言之,到
1998
年为止的四十年中,潜在而不能获得满足的需求已“蓄积”到极为巨大的能量,这个时候,房改把它一下子推向
100%
的市场化与民营化,结果当然导致房价的持续飙涨,后者再形成房价上涨的预期,于是自然就进入了“房价涨
→
买房及炒房
→
房价进一步涨
→
进一步买房及炒房”的螺旋循环。
2.0
阶段迄今为止
20
年,综合评估其利弊得失,应是:
(一)利与得——房屋产业通过其巨大的联锁效果,长时间,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带动了就业,也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住的问题;但与此对应,不可忽略的是——
(二)弊与失。主要有:(
1
)在不同地区形成了程度不一的楼市泡沫现象,对金融安定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2
)在解决了一部分人的住的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另一部分人(低收入者、年轻一代)更大的住的困难;(
3
)与此同时,也对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推波助澜的效应;(
4
)还不断地加剧资源的错配,不仅大量的物资资源变成了阑尾资源,还把大量的需求购买力如黑洞现象一般吸了进来并加以冻结。
所以,总的来讲,似乎是负面效应越来越大于正面效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当局对相关政策有所反思,进行调整,并重新定位,确属必要。关键在于有了新定位,是否就一定有合宜的、能与新定位配套的新政策,将新定位落实。

最近以来,从中央到各地方,为了遏抑房价的持续上涨,先后采取过限购、限贷、限售等措施,但都只能见到暂时性的效果,且这些行政干预手段还不免进一步加剧资源的错配。
最新的一个思路是鼓励“租”而非“购”,或租购并行,坦白说,这也未必切中要害,因为人们之所以弃租而购,正是因为房价涨势不止,不得不买,进一步买而炒之。所以,要真能够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房屋政策,作为第一步,首先就要找到此等现象形成的源头,并从源头下手加以改革才成。源头为何,主要有三:
(一)持续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严格地说,这个问题不仅限于中国,是一个全球大范围现象,也是
2008
世纪金融海啸的后遗症,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德国、北欧与新加坡,这些国家深知过于宽松之货币政策(如
QE
)一如鸦片,只能产生短期的减疼或舒适效果,却要付出长期的沉痛代价。中国学步市场经济未久,应多借鉴这些少数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严守货币纪律,正本清源。
(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地少人稠的如中国,在解决房屋问题的初期,政府不能缺位,必须妥善运用各种政策为刚打中低收入户解决住的问题,新加坡模式(
85%
人民住在“组屋”)及香港特区模式(
50%
住在公屋或居屋)可谓参考。
(三)改革健全地方财政制度,使地方能从税收及中央移转支付两方面就可以获得稳定的财源,从而不致有强烈的动机去搞“土地财政”。
能够在这三方面三管齐下,才能真正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新定位,是为中国房屋政策
3.0
。
所有图片来源自网站,特此鸣谢各原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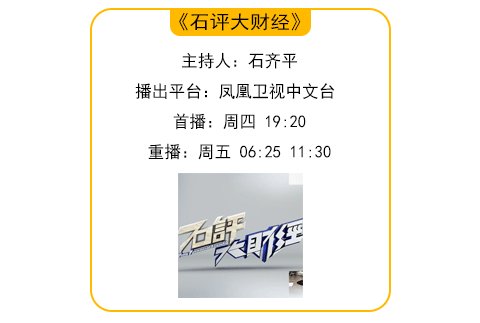
编辑:黄春燕、蒙小度
推荐阅读:
·
员工福利变暴力,除了愤怒我们还能做什么?
·
月薪过万上手快!双十一前这份工作招聘急急急!
·
这一次换南方人懵了:你们北方囤大白菜可以发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