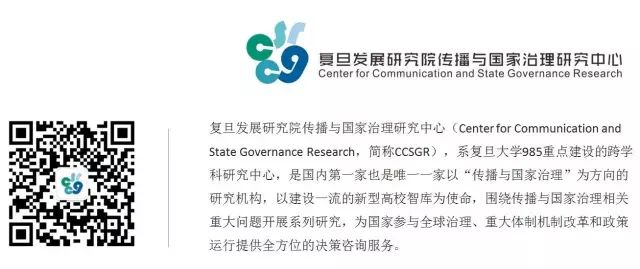欢迎点击上方订阅本公众号。
欢迎点击上方订阅本公众号。
导读
本文为CCSGR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张涛甫
的《当下中国的声音政治》一文摘要,获取全文请参阅刊发杂志。
本文认为,中国声音政治有其特殊演变轨迹和逻辑。当下中国声音政治的关系变量非常复杂,其受到政治民主化、媒介技术、媒介专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等变量的影响,从而出现如下特征:主流声音从弱势到强势;从单调到复调;从单一逻辑到多元逻辑。不过,互联网崛起赋予声音政治诸多变数,媒介技术具有极强的活性,创造出新的表达机会和空间,在资本和公民社会力量的推动之下,媒介技术会释放巨大的“破窗”效应,因此,未来声音政治的确定性究竟如何,尚难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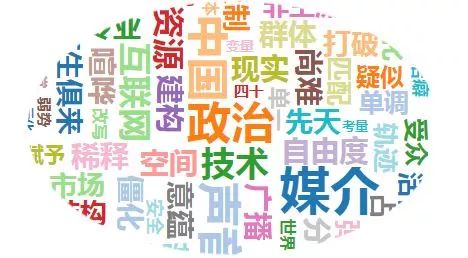
人类交往离不开声音这种媒介,在各种形态传达意义的介质当中,声音媒介的历史应是最久远的。有声媒介是一种稀缺资源,不是人人均可占有的,相比而言,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或有权力接近这种稀缺资源的人,会拥有某种特权或优势,接近或占有这种声音媒介,去影响他人,推销价值观或倾向性信息,获得政治认同或市场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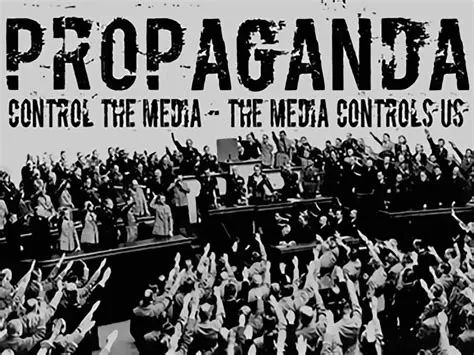
有一个有趣且普遍的现象: 那些拥有政治权力或社会权力的个人或群体,在获取或占有媒介资源上拥有先天优势,权力容易接近媒介,媒介对权力亦有与生俱来的偏好。
表现在声音媒介上,那些拥有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个人或群体,在接近或占有声音媒介方面会有显著的优势。那些拥有权力的个人或群体常常主宰资源的分配,也控制媒介资源的分配; 同时他们也往往具有相对较强的媒体学习和使用能力,善于利用媒体为自己服务。
互联网的崛起带来媒介功能的全面升级。
互联网技术使得媒介对于时间与空间的依附实现革命性的跨越。由于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网络空间行为主体具有空前的自由性,不再受制于传统社会关系的束缚,他们可按照互联网关系逻辑,重新建构新的社会关系,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互联网的崛起,深度改写了完全由精英主宰媒介政治的局面。
在互联网空间,原先“沉默的大多数”获得了发声机会,新媒体赋权使得此前那些没机会以及没能力发声的群体终于可以发声,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草根群体获得了发声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媒介政治即是大众政治。
但相比之下,精英们控制互联网的能力也在同步提升,互联网赋权给精英之外的群体以更多的机会,但精英们的“反制”能力更强。
网络社会不是一片自由王国。虽说,互联网空间不再复制现实空间的秩序和规则,可以突破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规约进行新的社会关系布局,但网络生活的行为主体仍是现实社会的那些人,现实社会关系不会机械复制到网络空间,但会影响网络空间。网络行为的自由度虽大,但并不意味着在网络空间可以为所欲为。
网络媒介同样面临着被社会化规训问题。

新中国成立开启媒介政治新时代。
应新政治逻辑之需,新政权对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格式化”。所有媒体由执政党统一管理,规定整齐划一的主旋律,要求舆论一律。在这种背景下,声音媒介被要求扮演“喉舌”: 新闻须要“新闻联播”,音乐必须是“颂歌”,电影也被“主旋律”……如此“异口同声”,为了达致“万众一心”的政治效果。为了确保意识形态安全,需要过滤、隔离、封杀那些有风险或疑似有风险的声音。为此,对外不惜一切代价展开声音封锁,将国民封闭在一个巨型的“罐头”社会里,阻断一切来自西方世界的声音,
这种带有意识形态洁癖的声音政治在短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这种僵硬的政治自闭注定是不可
持续的,它窒息了国家的活力,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声音政治沦为禁声的政治,中国沦为“无声的中国”。

后来的改革开放,对内解除左的政治禁闭,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松绑。在这种背景下,声音政治不再僵硬,有了弹性。对内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了,僵化的主旋律出现了松动。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流行音乐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使得自身溢出了艺术表现与文艺娱乐的范畴,承载了十分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由此形成了它与中心政治话语之间或抗争,或消解,或相融的复杂关系,构成了其自身被接纳、被批判或被抵制的遭遇与处境。以至于原先单调的中国出现了多声部的合唱。开放的门既然已打开,也就再也关不回去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的声音政治不再是一元化的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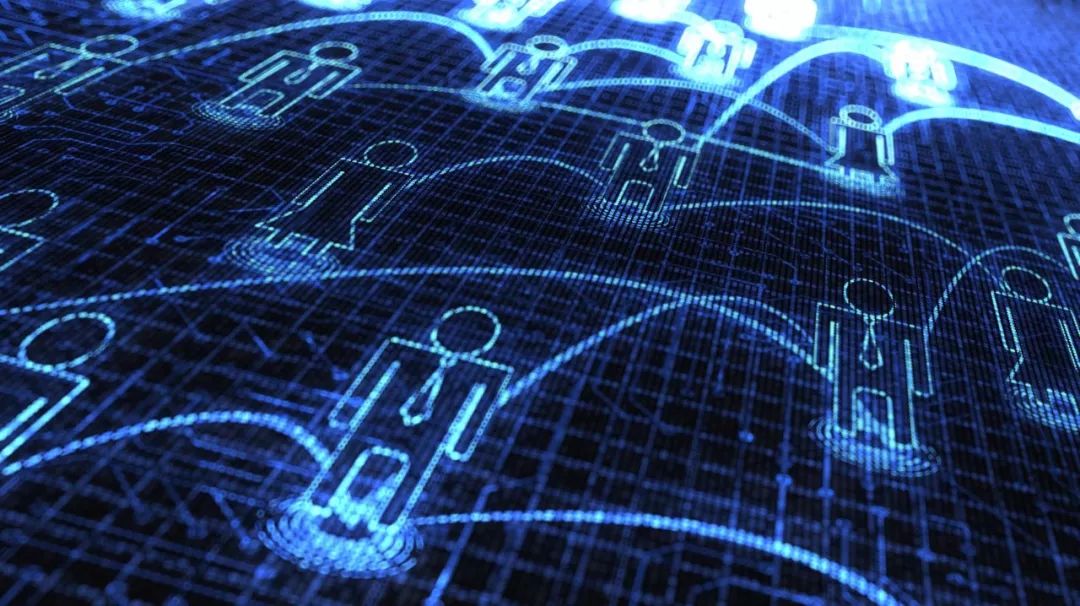
当下中国的声音政治即是在上述背景下一路过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给中国带来了极为丰富的声音景观,声音政治也变得异常生动和复杂。如何把握这四十年中国社会的声音政治,成为一件特别繁难的课题。笔者认为,把握当下中国声音政治,须要考虑以下几个维度:
1.政治民主化
声音政治受到宏观政治民主化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对内解锁禁锢和专权,强调权力的分享和表达的自由; 对外打开禁闭,注重与世界开放和对话,原先“无声的中国”旋即成为“有声的中国”。改革开放催生了公民社会的发育,推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表达意识的自觉以及表达能力的提升,释放更多的社会声音。这些声音经由有声媒介的传播成为公共表达,公共表达再通过“回声”机制进入政治过程,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合法性证明。

2.媒介专业化
有声媒介的专业化,首先表现为专业化的权利,即媒介拥有发声的权利。这是声音政治的大前提,也是有声媒介发声的前置条件; 其次,专业化还表现为发声的权力,也就是说,声音媒介拥有某种支配声音的权力,拥有这种权力,声音媒介就获得了其他组织或个人所不能及的资源和支配能力,乃至于垄断的权力; 其三,媒介专业化意味着拥有专业能力,即拥有成就专业水准的能力。

3.媒介技术升级迭代
在声音媒介中,既有传统媒介,也有新媒介。前者有广播、电视等,后者有播客、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媒介技术具有先天的政治性。 媒介技术的不断升级,可提升媒介功能的效度,与此同时,媒介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对技术成本的稀释,降低技术成本,为媒介技术的普及提供了前提条件。另外,媒介技术的社会化,需要政治力量的推动。若某种媒介技术与现实政治对冲,势必会影响这种媒介技术的社会兼容。
4.市场化程度
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在媒介市场同样适用。伴随着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媒介市场化也同步进行。媒介作为市场主体参与中国宏观市场构成,并成为宏观市场中的一个活跃板块。在市场化过程中,声音媒介作为资源要素进入媒介市场,为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讯息资源,满足目标消费者的媒介需求,并从市场获得回报。

5.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改变了权力实施的地域概念。权力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既是当地性的又是全球化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次打开禁闭的国门,渐渐融入世界。在这过程中,中国的媒介政治融入全球化进程。虽说,出于政治安全考虑,中国在对接全球化过程时,在媒介开放上是谨慎的,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媒体开放设置了保护层和防火墙。不过,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媒介政治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弹性的。此外,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考量,媒介作为一种“软力量”,必须走出去,同对手对话和辩论,主动向世界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好声音。
6.城市化推进
城市化是多种资源(包括人口资源)再生产和再分配。媒体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生产、集聚、分配,深度介入城市化过程,并成为城市化的标配。媒体的资源配置往往与城市化所形成的受众结构相匹配,与城市结构化人群的媒介消费需求结构相匹配。

当下中国的媒介现实复杂而有活力,充满不确定性,多种声音并存。
这些声音在多元化的媒介平台上发出,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有声媒介的表现比较复杂,难以用一个稳定、明确的框架予以描述。然而,从宏观面来看,一些趋势性的轮廓特征已经出现。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诸个面向:
1.主流声音从弱势到强势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推动当代中国声音政治的开放和多元。“主旋律”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主旋律”之外的社会声音多起来,且有各自表达的渠道,众声喧哗,改变了“主旋律”垄断的局面。再者,“主旋律”的无效或低效传播,稀释了“主旋律”的传播效果,致使舆论场出现“国退民进”的趋向。但是,十八大之后,这种“国退民进”的局面得到显著改变,出现“主旋律”强势回归。与此同时,媒介管理方加大了对“噪音”和“杂音”的管控,使其不能恣意扩张,致使非主流的声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抑制。

2.从单调到复调
如今的声音政治很难以单一的逻辑将其贯穿起来。不同舆论场域意味着不同声音的表达与释放。即便在同一个场域,也不是一种声音的控场,甚至在主流媒体内部,也有一元各表的景观。其次,互联网崛起,民间的声音在互联网四面八方升起,民粹主义声音甚为活跃,对冲了“主旋律”声音,即:不仅在中国非主流媒体场域,在主流媒体场域,皆不能做到异口同声、舆论一律。
3.从单一逻辑到多元逻辑
在当下中国,多种声音的背后有复杂的力量在起作用,有多种力量的博弈。其中,有技术的力量、资本的力量、政治的力量,还有专业的力量,等等,这些力量隐伏在各种声音的背后,形成了多元声音政治逻辑。比如,新媒体广播喜马拉雅,主要是由技术和资本力量推动的。喜马拉雅凭借新媒体技术,找到了声音媒介与网络时代受众偏好的最佳接口。加之有雄厚的资本支撑,喜马拉雅迅速崛起,成为平台级新媒体。资本和技术的联姻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媒体传播风口。

以上主要从有声媒介视角考量中国的声音政治。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的声音政治,既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复杂的现实语境。
当下中国声音政治的关联变量甚多,政治、资本、技术、文化等多元变量介入,多元勾连,形成了复杂的局面。
而且,每一种变量,在不同媒介空间施加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有声媒介中,其施加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互联网崛起之后,打破了中国媒介政治格局,自然也改写了声音政治的格局,主流声音一度弱势之后,管理方对互联网杂音和噪音的管理力度加大,而且多种管理方式并举,对过度活跃的互联网声音进行规训,主流声音出现强势回归的趋势。当然,
新媒体技术具有极强的活性,会不断创造新的表达机会和空间,尤其是媒介技术在资本和公民社会力量的推动之下,会释放巨大的“破窗”效应,因此,未来中国声音政治的确定性究竟如何,还难以判定。
(图片来自网络)
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执行院长、教授
本篇文章发表于《学术界》2018年第3期。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张涛甫.当下中国的声音政治[J].学术界,2018(03):65-72+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