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沈卫荣
“新清史”大概是近年来最受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议题,对它的讨论常见于各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刊物和媒体之上,十分引人瞩目。这些讨论或以精致的学术外衣来包装政治,或以直白的政治语言来批评学术,显然“新清史”和对它的讨论不像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和学术行为。所见不少对“新清史”的诠释和讨论,更像是论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不过是拿它当由头来说自己想说的事。(关于“新清史”的各种讨论不胜枚举,于此只能略举一二。前期的讨论分别结集于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远流出版社,2014年;以后的争论文章还有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 ——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12日;汪荣祖,《为新清史辩护须先懂得新清史——敬答姚大力先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17日;李治廷,《“新清史”:“新帝国主义”史学标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钟晗,《“新清史”学派的着力点在于话语构建——访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6日;此外,英文期刊《当代中国思想》也出版了“近年新清史在中国的论争”专号,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Vol. 47, No. 1, 2016。)我自己不专门研究清史,起初只把这场讨论/争论当热闹看,但看多了、听多了,常有雾里观花的感觉,反而看不明白“新清史”到底是什么,人们何以会给它如此之多的关注?于是不得不继续往下看,慢慢发现“新清史”所涉及的问题竟然有不少与我自己的专业学术领域,即西藏研究和藏传佛教研究有关,这样似乎也能看出一些门道来了。今天斗胆参与一回对“新清史”的议论,或同样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暂借“新清史”这个热门的话题,来说我自己想说的一些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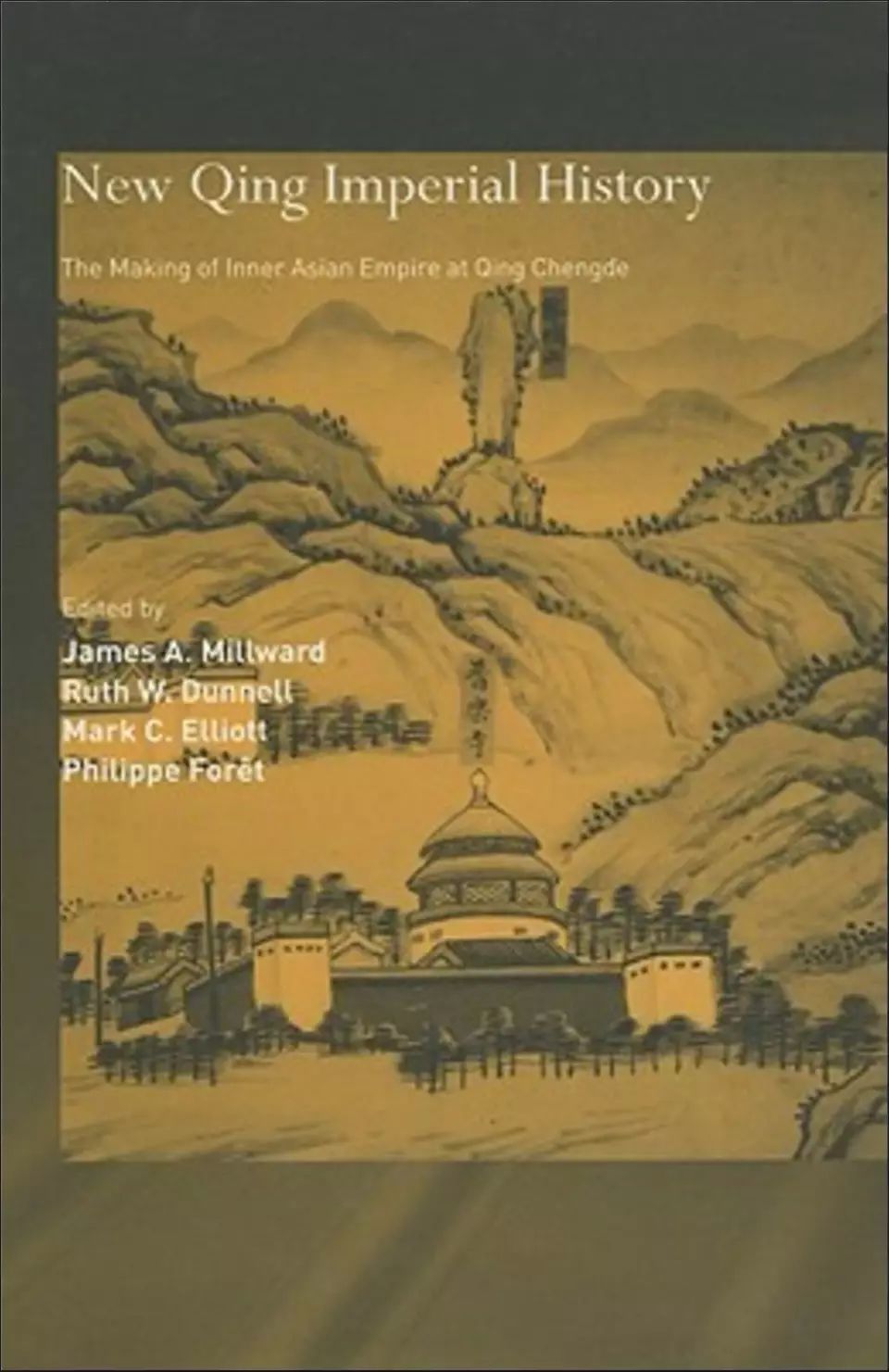
“新清史”的最初作品:《新清帝国史——内亚帝国在清承德的形成》
我最早见到的一本直接以“新清史”为标题的书是《新清帝国史——内亚帝国在清承德的形成》,其编者之一是我熟识的美国唯一的西夏学者邓茹萍(Ruth Dunnell)女士,蒙她所赐,我有幸较早拜读了这部明确标明为“新清史”的作品(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edited by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ē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这本薄薄的小书原来不过是几篇论文和资料性译文的结集,它将满清夏宫——承德避暑山庄,以及与它相关的建筑、艺术、典礼作为研究的焦点,来探讨内亚和西藏对于大清帝国(1636-1911)的重要性。论文的作者们想借助其研究来说明,清朝不能被简单地当作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王朝,因为它在军事、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很深入地与内亚相关涉。所以,这本书强调清帝国内有众多不同的族群,分析了满族与西藏高僧、蒙古头领和新疆突厥系穆斯林精英分子之间的关系,并阐述它们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作者们还特别讨论了乾隆统治时期(1736-1795)皇帝身份的性质和表现,检讨了包括曾被明显高估的朝贡制度在内的与内亚相关的礼仪[仪式]的角色意义,以此对一个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很复杂的历史阶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欣赏)。这本文集的每个篇章都以一个特殊的文本或者手工艺品为出发点,不只利用了以前在英文中还不具备的资料,而且也为读者了解承德的生活和它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大清帝国的重要意义提供了直接和详尽的知识。从这本文集来看,“新清史”最核心的内容大概就是他们特别强调和讨论内亚,特别是西藏,对于清代历史的重要性。
这部文集的导论由邓茹萍和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二位编者联合撰写,其中有一节题为“新清帝国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专门解释何谓“新清史”。它说:“最近学者们采用了‘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这个词来指称自1990年代以来,对在中国的和内亚的满清帝国史所作的一个大范围的修正。清研究牵涉了历史学家以外的艺术史家、地理学家、文学学者等其他人的参与,而在清研究中所做修正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满人和他们与中国、中国文化的关系的一种新的关心,以及对北京统治下的其他非汉人团体的关注。对那个曾经被当作是一个同质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东西的解构,或被称作‘中国研究中的族群转向(the ethnic turn in China studies)’。长期以来,人们相信中国的征服者,甚至它的邻居们,都会通过那种常常被描述为是一种自发的和单向的汉化过程,转变为中国之道。[新清史]对这种‘汉化’的假定提出了质疑,并对中国传统历史书写中的那些更为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教条,培育出了一种怀疑的眼光。采用人类学的观点,[新清史]学者对满人、蒙古人、回人、苗人和其他人等的身份认同,在历史语境中做了重新检讨。尽管这些观点还没有被普遍地接受,但许多曾将满人简单地贬为‘变成了中国人的蛮夷’的中国专家,现在也开始领会这个东北部族联盟对明中国的征服,所造成的复杂的文化、政治和族群问题。此外,越来越多的从事清史研究的学生正在学习满语。”
还有,被“新清史”重新检讨的另一个观念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奠基者费正清先生率先构建的“朝贡体系”。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清帝国的历史被叙述成与其前朝一样,都以汉文化为中心,它所实施的对外关系同样被认为是遵循了一种为西方历史学家熟知的“朝贡体系”的持久模式。这种认为中国历史贯穿始终都固守着一种单一、不变的国际外观的观念,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曾受到过质疑,但却逐渐被认可。然而,这种模式的中心形象,即中国的君王摆出一副天下共主的姿态,要求八方外夷都必须以朝贡的名义来开展外交和商业活动,长期以来不只是对历史学家,而且也对外交官、政治家,甚至对中国人自己都产生了影响。费正清当初建立“朝贡体系”的观念根据的是他对十九世纪中国海岸的外交和商业的研究,然后将它扩展成为传统中国外交关系的一般模式。然而,如果对清代和整个清帝国做更深入一点的考察的话,那么,人们就很难维持这种对清代外交关系所持的简单的文化主义模式。事实上,清朝还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与其邻居交往,其中包括政治联姻、宗教赞助、商业、外交和战争等,这些方式常常与朝贡或者汉族中心主义没有任何关联。

费正清(1907-1991)
与清是否遵循中国外交关系之传统模式的观念相连接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当关注在清的语境中所谓“中国的”和“外国的”到底确切地指的是什么?费正清认为中国[汉]文化居于清政体的核心位置,但是满族的统治精英与他们的内亚臣民(蒙古人、西藏人和突厥系穆斯林)的交往常常比他们与汉人的交往来得更加紧密。而《新清帝国史》这本书的聚焦点就是清与内亚的那些关系,以及它们的政治和文化基础。
在挑战汉化、汉族中心主义和朝贡体系模式等概念的同时,“新清史”家们重新发现了同时作为“一个内亚的”和“一个中国的”帝国的清朝。虽然,对此迄今还没有得到像对满族身份认同问题一样的持续的研究,但它对于改正我们对清代之重要性的理解十分关键。此外,有鉴于中国民[国]族愿景[理想]在延伸到西藏、新疆,甚至到内蒙古的蒙古人中间时,正面临着持久的困难,这个在内亚的新的、更大的中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大清的创造(the new, greater Chinese empire in Inner Asia is a Qing creation)这一事实于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巨大的欧亚政体,大清帝国不但可与那些“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s)相比较,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与莫斯科大公国,甚至和哈布斯堡和大英帝国相媲美,它当在世界史上占有一个新的位置。那些关于清的旧观念(今天有时依然会听到有些非中国专家如是说),即把清当作停滞的、孤立的、特殊的,以及与早期近代历史潮流相切割断的等等,早已站不住脚了。不管是“中国”,还是“东方专制主义”,或者“亚洲病夫”等等,都将无法用来描述这个扩张型的满洲国家,它不但终结了衰败中的明朝,而且还在中国内地重新建立起了秩序和繁荣,并将中国腹地的经济力量与它自己的军事实力结合起来,以抵挡俄国,粉碎准噶尔,并使蒙古、新疆和西藏加入进了帝国,使得在北京控制之下的帝国版图增大了一倍(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pp. 3-4.)。

“新清史”学派主将:米华健
这个导论的作者之一米华健先生是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主将之一,故以上引述的这些内容无疑可算是对“新清史”之主要观点的确切概括和总结。从中可以看出,“新清史”对传统清史研究的最重要的修正就是,将其视角从传统中国历史书写范式对“汉化”和“朝贡体系”的专注中转移出来,进而把它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即从“中国的”和“内亚的”帝国两个维度来研究清史,并响应“中国研究之族群转向”,更加推崇对清代之非汉人团体,特别是蒙古、西藏和突厥系[新疆]穆斯林族群之历史的研究,强调满族统治者与这些内亚民族、地区之互动的历史对于理解整个清帝国历史的重要意义。
平心而论,将清史从以王朝更替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历史传统叙事模式中解放出来,不再以汉族中心主义史观下的“汉化”和“朝贡体系”为主线来建构清帝国的历史叙事,转而更重视对满族及其统治下的非汉族族群和地区之历史的研究,“新清史”显然有其新意,它是对传统清史研究的修正和进步。毋庸置疑,清具有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由汉族建立和统治的王朝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朝贡”对于习惯于“严华夷之辩”,并以“怀柔远夷”为目标的汉民族统治下的王朝开展外交和国际关系至为重要,但对于像元、清这样的“征服王朝”来说,它确实不过是其外交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选项而已,它们在与广大西域和边疆地区的交涉中,往往显示出与汉族统治王朝不同的侵略性和扩张性。
但是,清之所以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王朝,不能说只是因为清“在军事、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很深入地与内亚相关涉”。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王朝,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非汉族政权,它们的历史都与内亚,或者西域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有着广泛和深刻的牵连。即使是像明这样的汉族政权,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它也都和西藏、蒙古等内亚地区的民族有很深的交涉(David M. Robinson, “The Ming Court and Inner Eurasia,”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351-374页;David M. Robinson ed.,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in Ming Court (1368-1644), Harvard East Asia Monograph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王朝,其统治地域、方式等都各有其特点,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王朝,它既是一个外族入主中原的征服王朝,同时它也是其前朝的继承和发展,应当首先是一个“基于中国”的帝国。
显而易见,“新清史”是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对清帝国史的一种新的书写,它与传统的汉族中心主义史观影响下的清代历史叙事,有着巨大和本质的不同。按理说,“新清史”学家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师爷、美国中国研究的开山鼻祖费正清先生,解构的是费正清最早倡导的以朝贡体系为主线的正统中国史观。他们并没有,甚至也不屑于批判中国学者在传统的汉族中心主义历史观影响下的清史书写。在“新清史”于中国引发激烈争论之前,它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似乎也没有形成为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新的学术流派,更不是每一位清史学者都认同“新清史”的这种学术转向,并自觉地与“新清史”学家站在同一队伍之中。不但有何炳棣先生这样有影响力的前辈华裔权威学者站出来捍卫“汉化”于清代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近年来还有一些专门研究清代蒙古、西藏历史的西方新锐内亚学者,从他们对满、蒙、藏、汉等民族于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朝圣与互动的历史研究中发现,满清与蒙古、西藏的交涉事实上并没有多少明显的“内亚”因素,相反却有更多的汉文化因素,进而提出了“清世界主义”(Qing Cosmopolitanism)的说法,以此与“新清史”专重内亚性质的学术主张对垒(Johan Elverskog, “Wutai Shan, Qing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Mongol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No. 6, 2011, pp. 243-274; Peter Perdue, "Ecologies of Empire: From Qing Cosmopolitanism to Modern Nationalism," Cross-Currents E-Journal, No. 8)。

何炳棣先生捍卫“汉化”于清代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那么,何以美国的“新清史”会在今天的中国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弹呢?不难看出,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或在于,“新清史”触及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理解和解释清与“中国”之关系这一问题,而这个问题自然是一个对于理解作为民族国家之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以及处理眼下中国出现的民族、边疆等种种棘手问题都十分紧要和敏感的主题。如何理解和分别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和西方视野中的China这一概念,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的关系,是十分复杂和难以处理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只是历史学家的兴趣和责任。“新清史”学家主张将“清当作一个内亚的,以及一个中国的帝国”(the Qing as an Inner Asian, as well as a Chinese empire),其中那个“中国的帝国”指的自然就是“一个汉人的帝国”,而通常他们笔下的“中国”(China)指的也就是这“一个汉人的国家”,所以,在他们看来清和“中国”或只有部分的重合。可是,一个纯粹是由汉人组成的,或者一个完全脱离了汉人的“中国”,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今人“想象的共同体”。严格说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纯粹的汉人的“中国”,而即使在一个由外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中,其主体也依然是汉人。将清朝泾渭分明地区分为“一个内亚的帝国”和“一个中国(汉人)的帝国”,并把它作为这两个帝国的统一体,这是不妥当的。当然,即使真的可以把大清如此明确地分成两个帝国的话,那么,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也依然还是“清中国”(Qing China)。
最近,米华健先生在《上海书评》所做的一次访谈中坦言:“我知道,很多人在不断暗示,甚至直接明说,‘新清史’是分裂中国的学术阴谋,想要搞垮中国。这也是不对的。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但这的确是个误会。我们之所以进行被称作‘新清史’的研究,目标其实是调整、修正包括费正清在内的那一代历史学家的学术话语(discourse),比如朝贡制度,比如汉化,又比如中国中心论。”(《米华健谈丝绸之路、中亚与新清史:发掘“被遗忘”的人群》,《上海书评》,2017年7月9日)显然,将“新清史”作为一种分裂中国的学术阴谋确实是中国史学界掀起批判“新清史”浪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实。如果主张清不等于中国,或者说清不是中国,那么今天的中国能否名正言顺地继承“大清”留下的历史遗产,它对西藏、蒙古和新疆等内亚地区的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等似乎都成了问题,这自然是爱国的中国学者无法接受的学术底线。
作为西方学者,“新清史”学者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自然不可能与中国的清史学者完全一致,而清是否是“中国”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它的探讨,中西方学者会有不同的视角、敏感度和意义,故很难做心平气和的学术讨论。尽管“新清史”的代表人物近年来再三澄清“新清史”并非是一个分裂中国的学术阴谋,但他们同时也坦承,“新清史”家中确实有人“倾向在‘清朝’与‘中国’之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或者认为“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是有不同的政治目标的不同的政治实体,即使在人口和地理上清朝与现代中国明显重叠,两者间也非密合无缝,而事实上有许多参差冲突之处”(语见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391页)。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大概比西方学者更相信西方人总结的“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既然“新清史”家们不愿意在“清”与“中国”之间划一条等号,那么,他们就难以逃脱“分裂中国的学术阴谋”的指控。
显然,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纠结,才使得“新清史”在中国学者这里成了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如前所述,西方人所说的“China”常常指的是一个纯粹的汉人国家,所以说大清是中国也好,不是中国也好,其中已经有了一个预设的基本前提,即是说,大家同时承认在唐 、宋、元、明、清这些王朝之外,还当有一个抽象的、可以明确地指称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存在。但是,这个脱离了具体的历代王朝的“中国”、这个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的一个纯粹汉族的“中国”,它无疑只是一个莫须有的存在,相信没有哪一位“新清史”家真的可以对它做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于西方的学术著作中,“Qing China”是一个我们更常见的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的表述,这表明“清”和“中国”应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合二而一的概念。从强调“中国”不是一个纯粹的“汉人的国家”这个角度来看,“新清史”反对将“汉化”和“朝贡体系”作为两条主线来描述清朝及其对外关系的历史,以破除“汉族中心主义”对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影响,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破除“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强调“这个在内亚的新的、更大的中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大清的创造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今日中国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但不应该是将中华民族的理想推及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区的困难,相反应该成为助缘。正如持“清世界主义”史观的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清代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人口、地理区划的广泛流动和变化,有力地推动了各族群之间文化、习惯和宗教传统间的深入交流,它所造成的积极影响显然不是令各族群画地为牢,强化各族群的不同特点,而是穿越和打破帝国内族群的界限,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具有世界主义性质的清文化。这种“清世界主义”对于今日中国建构一个融合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无疑具有很有启发性的借鉴意义。只有片面强调作为“内亚帝国”的清的重要性,同时弱化作为“中国帝国”的清的历史意义,并将清和“中国”分离,才会成为建构和叙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之中国”的古代历史的障碍,并进而造成今日中国建构各民族[族群]共同承许的中华民族之身份认同的巨大困难。

一个疆域变化的、历史的中国
值得充分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所讨论、所争论和所想象的这个“中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既是一个历史的、人文的概念,又是一个民族的、地域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的、法律的概念,若我们只选取其中任何一个方面来谈论一个抽象的中国,则一定是不全面和不恰当的,也无法与这个现实的中国相对应。此外,中国还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历史性的概念,“秦中国”与“清中国”绝非同样的概念,就如“清中国”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非密合无缝一样。全部中国古代历史所揭示的一个事实是,所谓“中国”的内涵和外延时刻都在变化和发展之中,今日之中国的形成无疑是以上所有这些因素长期互动和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既不能因为外族入主的征服王朝的出现,或者因为这些王朝对内亚的经略远比汉族王朝更加深入而否认它们的“中国”性质,也不能固守“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坚持要把非汉族建立的王朝一概排除在我们理想的“中国”之外,或者非要以“汉化”的方式把它们改造成为我们理想的那个“中国”,然后才把它们的历史纳入到古代中国的历史之中。
近年来,来自日本的“新元史”和来自美国的“新清史”都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细究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或许就是我们自己在按照西方政治理念对民族国家所作的定义,来理解和解释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以及它与中国古代历史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和解释在建构一个全国各民族百姓共同承认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何谓中国/何为中国”的讨论层出不穷,但这样的讨论似乎都很难脱离“汉族中心主义”的藩篱,其实际效果或与被他们激烈批判的“新清史”异曲同工。如果我们非要坚持“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来讨论“中国”这个概念及其形成的历史,那么,不管我们选择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也无论我们能够如何雄辩地证明,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哪个时候,形成了一个何等样的“中国”,或如何确凿地表明,自何时开始,“大一统”的理念已经何等地深入人心,这个“中国”依然只能是我们汉族想象中的一个理想型的中国:它不但与我们今天所关切的这个现实的中国没有必然的关联,而且也很容易把中国古代历史上包括大清在内的、由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帝国对今日之中国的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排除在外。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在这个过去了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中国”和现在的这个[多民族的、跨地域的、政治的和法律的]中国之间建立起一种严丝合缝且无可争议的历史联结。与其去虚构或者想象出一个古已有之的、纯粹汉人的或者“汉化了”的“中国”,并费力去建构它与现实中国的历史联系,倒不如像“新清史”学家们一样,彻底破除“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把“清中国”看成是连接“明中国”和中华民国的一个自然的历史阶段,而现实中国则是对“明中国”“清中国”和中华民国的自然发展和继承。显然,与将“大清”理解为由一个“内亚的”和一个“中国的”帝国所组成的“清中国”比较起来,坚持“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继续将清朝的历史,区别于中国古代史上其他以汉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王朝的历史,甚至把清朝排除在一些人理想中的文化的,或者人文的“中国”之外,对于正确理解今日中国的国家身份认同,维护当今中国的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可能造成的损害,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沈卫荣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