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陈以侃
他低头看着抓住他臂膀的那只手,就好像这是柬埔寨大屠杀以来对人权最严重的侵害。
别人怎么样不好说,但个人而言,我或许只是喜欢听自己喜欢的人事物被谈起。比如某个我欣赏的球员踢了场好球,第二天所有提到他的报纸、网页、podcast,都成了第一等的文学。罗兰·巴特是我最迷恋的文人之一,文化理论也向来是我很热衷的消遣,所以听说有Seventh Function of Language(《语言的第七功能》)这本书,就像中奖一样,更何况洛朗·比内(Laurent Binet)本身就是极好的小说家,上一本HHhH拿过龚古尔首作奖。这本新书预设1980年巴特走在马路上被车撞死实际是谋杀,然后在调查中牵扯出了当时每一个文化理论家。开场不久,侦探调查的第一个对象是福柯,课堂里见到他,还没问什么,这个穿高领的光头就一边说着“我拒绝向任何权力承认我的身份”,一边就要走,被侦探抓住手臂之后,小说家用上面引用的这句话描述福柯的神情。
我一下就起劲了,知道这书能带给我多少愉悦,因为它抓住的这根手臂真的是法国知识分子的精髓:浮夸。孟德斯鸠所谓法国人“对轻佻的事严肃,对严肃的事轻佻”。1994年诺曼底登陆前英国士兵拿到一本小册子,里面一条是提醒他们,法国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其实不是要打架,可能只是在讨论某个抽象问题。生在法国、住在法国的懂事人毛姆,就在某个短篇开头的时候说,要了解法国这个民族,你得懂他们的“panache”,本来指的是骑士头盔上的羽毛,但“它似乎也象征着尊严和狂妄,炫耀和英勇,卖弄和骄傲”,举的例子里面有丰特努瓦的法国人曾经对乔治二世的军队慷慨道,你们先开枪吧,先生们——换句话说,法国人为了帅,可以连命都不要;想起福柯还曾说过艾滋病是政府为了迫害同性恋编造出来的谎言,结果自己就死在这个病上。比内的小说里,文坛的传奇巨星,一个被狗咬死,一个被阉割,都是瞎编的,但读来并不觉得太轻佻,反而感受得到作者对这些人物和他们学说的认真。在某个采访里小说家也提到,他把故事写成侦探小说,是致敬那个法国人会觉得为了思想甚至值得杀人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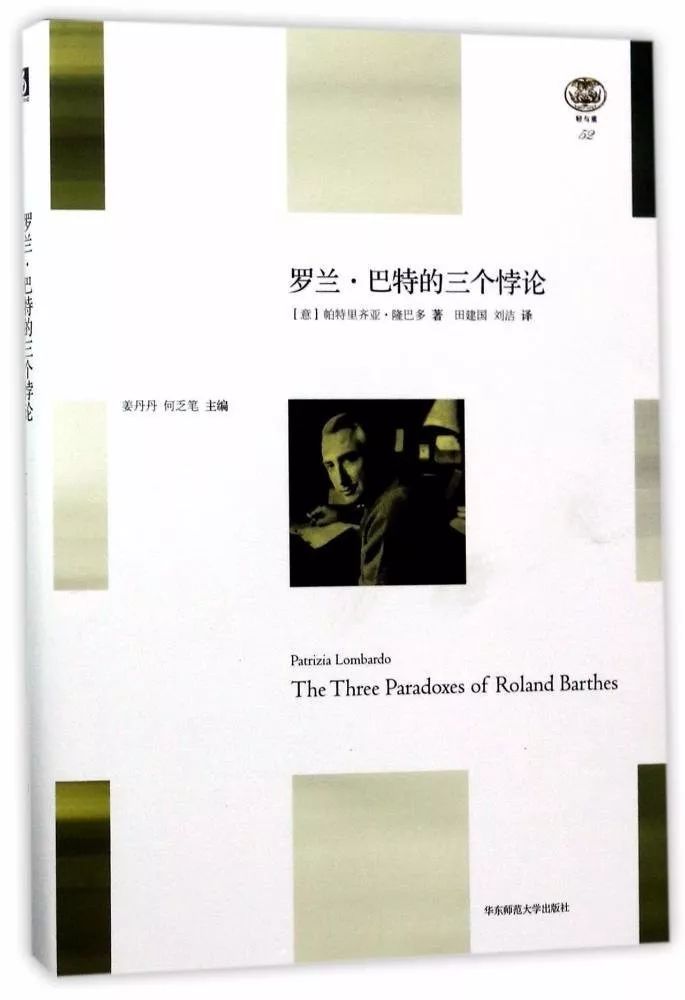
西西弗不高兴了。
凑巧,最近还看了本关于巴特的书,一个意大利人用英文写法国人,89年出的,中文版刚能买到,叫The Three Paradoxes of Roland Barthes(《罗兰·巴特的三个悖论》)。我先是逐字读了英文版——读完明白这本书是写巴特的;后来又买了中文译本,在里面奔突了一阵(用巴特的话说,“阅读是划痕:我往下阅读,跳略,抬头,复又沉浸”),结果发现我懂得更少了。我现在敢提起这本书,一方面是“作者已死”,另一方面我坚信,没有人能吃得准隆巴多女士(Patrizia Lombardo)到底讲了什么,至少不足以指证我在胡说八道。
巴特可能是理论史上最潇洒的人物,每次轻描淡写推翻自己,只见瓦砾堆已是新的丰碑。但有一件事比内就很明白:再玄奥飘渺的哲学想法,总有些痕迹让我们辨别出那个哲学家也被一种不太方便的东西纠缠着——叫做人生。《三个悖论》的作者曾经是巴特的学生,对师尊的矛盾、灰心和绝望,特别有体会。“三个悖论”大致是这样:巴特既推崇先锋写作,但又迷恋历史和古典作家;他热爱语言,但又认定语言是吞没自由的元凶;他只写过散文,但在写作生涯的末端却认定散文太实诚,太容易被意识形态招安,一心想写小说。巴特把写作看成三个部分,“语言”是某个时代给作家提供的文字,“风格”是他活到此刻所积累而成的心性,都是给定的,而只有在“写作”这部分,作家才有他的一点自由,能创造些新的东西来,但又立马会被历史、语言、意识形态所吸收、同化、消灭。巴特始终在怕自己的写作被某种体制或系统摁住,这种骨子里不落俗套的人,他的焦虑是我们很难真正感同身受的。一个几乎每篇文章都改变后人对此问题思考方式的作家,《三个悖论》写到最后还把这种工作状态描述为终于推石头推烦了的西西弗,也真是让我有点想笑。但巴特迷人的核心确实就在这样一种极其加缪式的辩证:纵然写作的挣扎一闪就灭了,但我们也只能活在那一闪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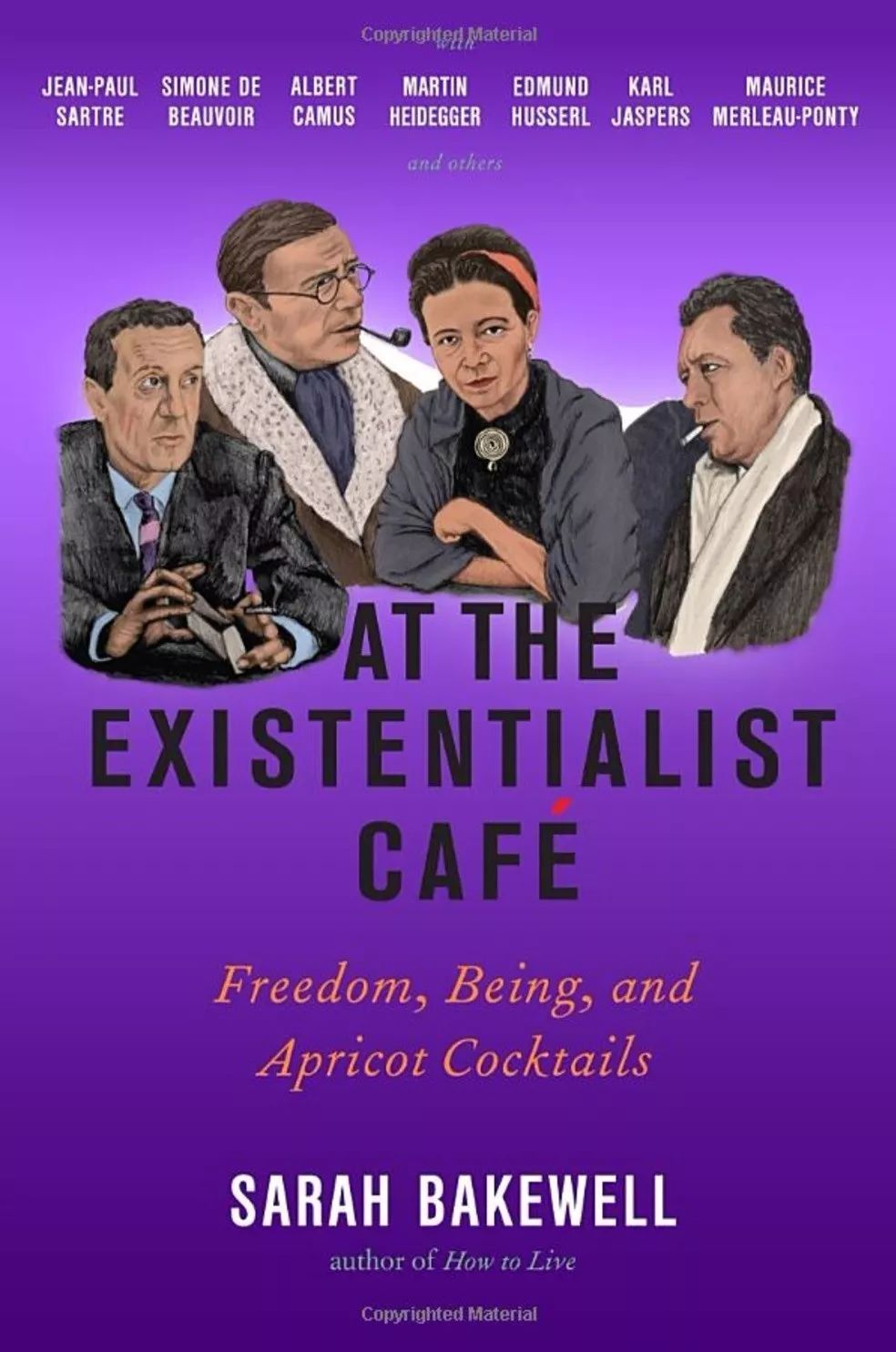
对于道德和责任我最确信的事,都是大学时在足球中学到的。
距离上次读萨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居然已经过去七年;那时候她一本How to Live: Or A Life of Montaigne(《蒙田:如何生活》)铺天盖地的好评,我读了倒只觉得中规中矩,或许因为推荐蒙田这活儿在我暗自看来总有些讨好不吃力;但绘制一幅存在主义哲学的全景图,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é(《存在主义咖啡馆》)展示了贝克韦尔是技艺何等娴熟的一位肖像画家和文普工作者:每个存在主义的核心和周边人物都在时代与个人命运的翻滚中栩栩如生。读了这本书之后,最突出的收获是重新发现萨特。作为一个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的信徒,我之前自然觉得Cultural Amnesia(《文化失忆》)里面对萨特的终审足够有说服力,大致可总结为:此人持身不正,“难怪哲学也全是胡说八道”。但经过贝克韦尔的处理(又课外补了好些萨特),我似乎跟她一样,都喜欢起萨特来了,或许只是因为他的hypergraphia(多写症),那种不知疲倦想讲解世界、改善人间的能量,从本质上是可爱的。
萨特和加缪的割裂依旧是这段哲学史中最有趣的章节之一。萨特之所以隔了几个十年之后显得格外不堪,也主要是加缪的高风亮节在衬托着旧友。他们闹翻主要吵的是,共产主义为更美好的人类未来在奋斗,我们应不应该对苏联劳改营睁一眼闭一眼。加缪说不行的;他说你可以为理念而死,但不能为理念杀人。因为加缪在某个访谈说过上面引用的话(他是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竞技大学队的守门员),我一下想到另一个法国人:温格。这是一位坚信“理念”高过输赢和拿冠军的足球教练。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有次在写萨特投靠共产主义的时候说这很像是帕斯卡赌注(Pascal’s Wager),也就是“为什么不信上帝呢,如果上帝是真的,享永世之福,如果上帝不存在,你也不少什么”,还说萨特的“原罪不是想错了事情,而是他的置身事外,即那些思考的后果从来不影响他自己的生活”。阿森纳十数年来踟蹰不前、见虐不怪此处铺展不开,但戈普尼克的那两点实在太像温格的执教之道,或许用法国知识分子和温格本人的腔调(教授曾说买哈维·阿隆索是“杀死”自己帐下不成器的德尼尔森),可以把一种为了理念而没有让球队尽可能强大的姿态——因为球员和球迷转眼就老了——称作慕尼黑惨案之后对足球生命的最大掠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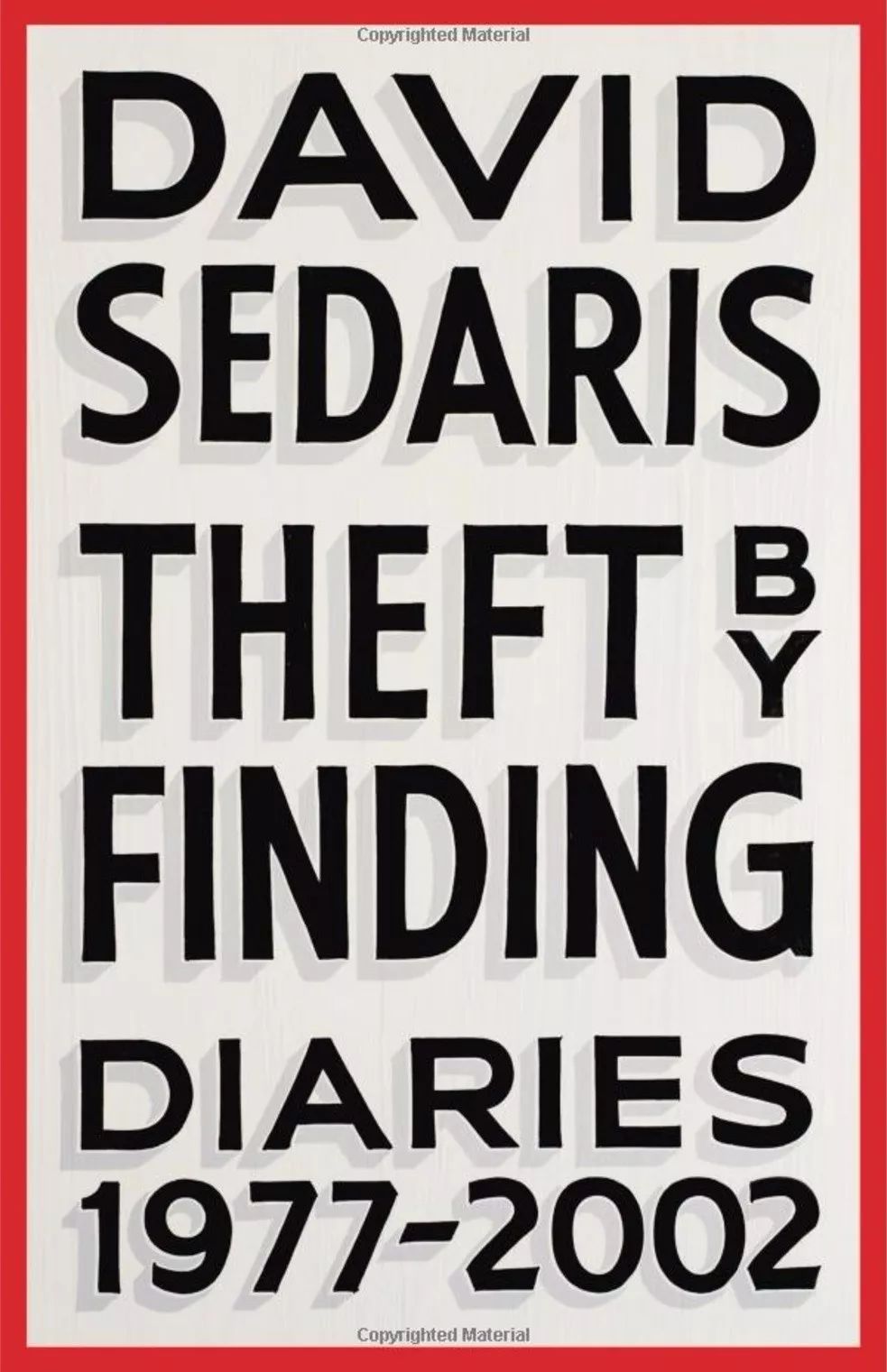
巴黎的秘密,说到底,是它呈现的快乐——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永远跟一种严肃感交织着。
因为最近读巴黎读得有些不可收拾,我决定重新捡起一个没法更纽约的作家——大卫·赛德瑞斯(David Sedaris)。号称“新千年伍迪·艾伦”。大概五年前,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编辑约我在他那本我深深向往的期刊里写一篇赛德瑞斯,但当时只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作家。我是如此郑重地对待书评这项艺术,用了五年时间思考、沉淀、成长(那位编辑已经转行,杂志也没了),终于对赛氏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看法:我的确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作家。
这次主要是发现他在巴黎住过十年,Me Talk Pretty One Day(《说得美》)里写过,然后又把他火热的新书Theft by Finding(《捡到不交公算偷》)读了,这是他1977到2002的日记精选,自然也有很多法兰西经历。赛德瑞斯是一个所有叙事都是旁观、所有旁观都带着梗、但所有梗都相似的作家。比如他写了很多学法语的窘迫经历;男朋友做菜时候切到手指,快昏厥过去了,赛德瑞斯担心的是自己待会打急救电话不会说怎么办。这些神经质大部分都拿捏得很好,但那种抽离实在太彻底,到最后连他的“抽离”读者也进不去。话说回来,五百页日记,的确有一个很打动我的地方,就是9/11发生之后,在巴黎的美国人都聚到一个教堂里。在这样哀恸的背景下,赛德瑞斯身不由己的轻佻(比如唱国歌他发现大家都不记得歌词)真切得几乎要让我落泪。戈普尼克是《纽约客》曾经的驻巴黎作者,他给“美国文库”编过一本Americans in Paris(《美国人在巴黎》),摘了五十多个作家写他们的巴黎,上面引的那句话出自他的序言。所以最后这一条留给一个在我看来并非最上乘的纽约作家很合适,因为赛德瑞斯只沉浸在自己的小脾气里,而从笛卡尔以来,法国人就替全人类思考,动不动就要死要活,当然他们会想错,会可笑,会尴尬,会失败,会闯祸,但只要写作者未必能全身而退的那种“严肃感”还在,我就不大会厌倦吧。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