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自由与强制力》
洪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吴彦的《法、自由与强制力》一书,是近年来难得的关于康德法哲学的研究。作者探讨了康德法哲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康德的法哲学,做了有益的探索。这里仅就该书的若干难点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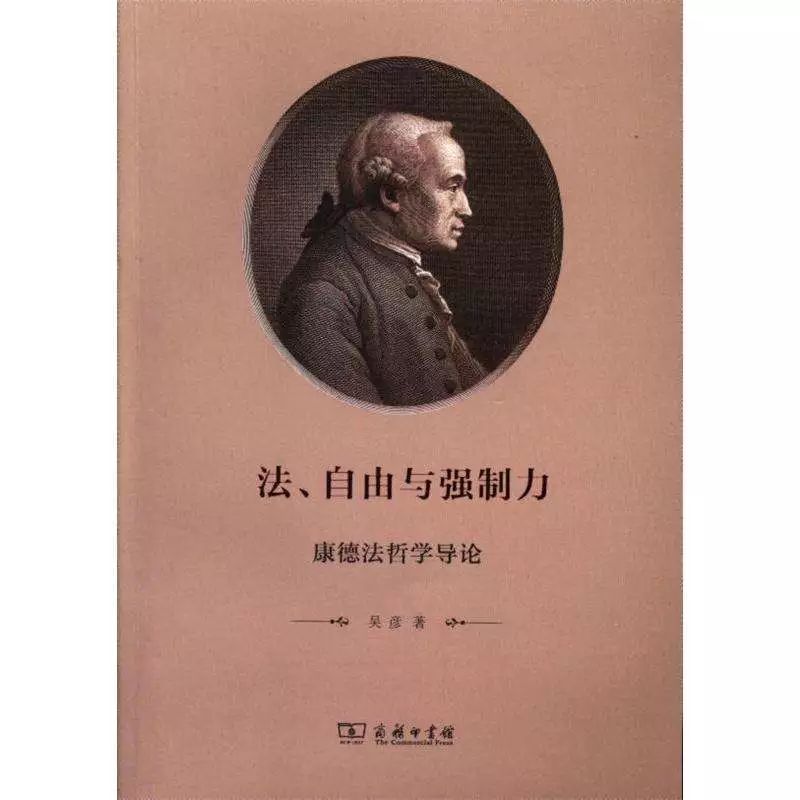
吴彦著
康德的政治哲学,我前几年曾经关注过,也写了点文章。因为这段时间里一直关注法治问题,而康德有重要的法治思想,所以读这本书时,也想从中看到对康德法治思想的论述,只是有点失望,书里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少。
伊曼努尔·康德(公元1724年—公元1804年)
《法、自由与强制力》的副标题是“康德法哲学导论”。既然是导论,康德法哲学(该书作者将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作同等看待)的基本问题应有所呈现,譬如说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该问题在康德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要,又譬如说法权国家以及法治等问题,似乎都应该有所讨论。
我个人特别关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国内很长时间里,似乎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认为搞政治的人是不必讲道德的,道德是小民百姓的事。搞政治的人有一种道德豁免权,他们可以什么都干,什么都可以干,道德和法对他们没有约束力。我想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做,除了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之外,他们拥有古各斯戒指,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可以使他们以及他们的武器遁形。与之相应地,可以发现,这些年,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研究特别热。这两个人都是主张把道德抛在一边的。直到康德,道德与政治才重新结合起来——当然,在他之前还有卢梭,康德继承并完成了卢梭的事业。所以,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康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前几年写康德,就有借康德来表达这个想法,即搞政治也应该讲一点道德。
从马基雅维里开始的近代西方政治传统的一个倾向,就是把政治仅仅当作现象来认识,把政治置于认识的领域,即科学领域,政治被看作是认知的对象或科学认识的对象。而康德认为,政治实际上更应属于实践领域。他的批判哲学实际上是对自马基雅维里以来的这个近代或现代政治科学传统的批判。有学者指出,康德试图以道德自律解决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世界中的政治自律所带来的道德与政治的分裂,回到一个被卢梭所发现的更为整全的世界,恢复作为正义的形式法则的道德律令的调节性功能,以道德给政治立法,让政治向道德屈膝,扭转被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所改变的世界图景和历史轨道。[1]因此,诚如施特劳斯所说,康德政治思想之于在他之前的现代政治传统的重要特征亦即贡献,就在于他重新“着眼于政治生活的道德尊严这一关键性的和被忽略了的问题,即被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的传统所蓄意牺牲掉的问题。”[2]
我读《法、自由与强制力》,发现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恰恰是把“法权”从“道德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认为“康德法哲学在‘法’与‘伦理’之间所做的严格区分既将‘法’从‘道德’中分离出来……”“康德的法体系是一个与伦理体系相分离的体系”等等(《法、自由与强制力》,页34,以下只注页码)。我以为该书在对康德的基本理解上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放弃了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探讨。
康德的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其实正体现于他的法权(或权利)哲学或法哲学。康德之恢复道德与政治的关联,即他的所谓道德在政治中的优先地位,不是要求国家对公民行为进行直接的道德指导,“教人以善德”。他所讲的道德,是以人的权利作为政治的基础,在政治领域,道德的定义就是尊重人的权利。在康德这里,政治之道德与承认人的权利是一致的,道德即权利、义务关系。这种完全以纯粹权利概念为基础的政治,康德称之为“道德的政治”。
康德的法权的普遍法则的表述是:
“外在地要这样去行动:你的意志的自由行使,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并存。”
[3]
亦即,法权意味给予人以自由。但是,这并非如该书所说,
“在法权的领域中,道德和不道德的行动都是被允许的,只要这些行动符合法权法则的规定”(页146),而
是说,道德并非法权所规范,但是,人虽是自由地、却依然应道德地行动。法权给人以自由,而在这个自由领域中,人应以实践理性的法则来指导其行动。
在此意义上,康德的法权国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道德国家。只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管理人的道德,或者进行道德教育,更不是把道德当作一种施政工具,而是相信当给予人以自由时,人的理性、实践理性可以指导他过一种道德的生活。权利的普遍性法则规定了人自由行动的界限:不妨碍他人的自由;而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则规定了人在这一界限之中如何自由的、合乎道德的行动。
之所以如此的基础,是承认每个人都是道德主体,其自身有在道德上臻于完善的能力,国家因此尊重并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以使其道德能力得以充分发展。康德信赖普通人的善性。他说,尽管普通人不会用哲学式语言表述善,但是,善良意志寓于每一个自然健康的理性之中。他的这一信念,体现于《实践理性批判》。在该书中康德举例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毋需老师指点就能对一个故事中的人物进行道德判断。他写道:
“倘若有人问,究竟什么是人们必须以之为试金石来检验每一种行为的纯粹德性,那么我必须承认,惟有哲学才能够使这个问题的决定发生疑问;因为在普通的人类理性那里,它早已经有如左右手的分别一样被决定了,虽然不是通过抽象的一般公式,而是通过习惯的应用决定的。”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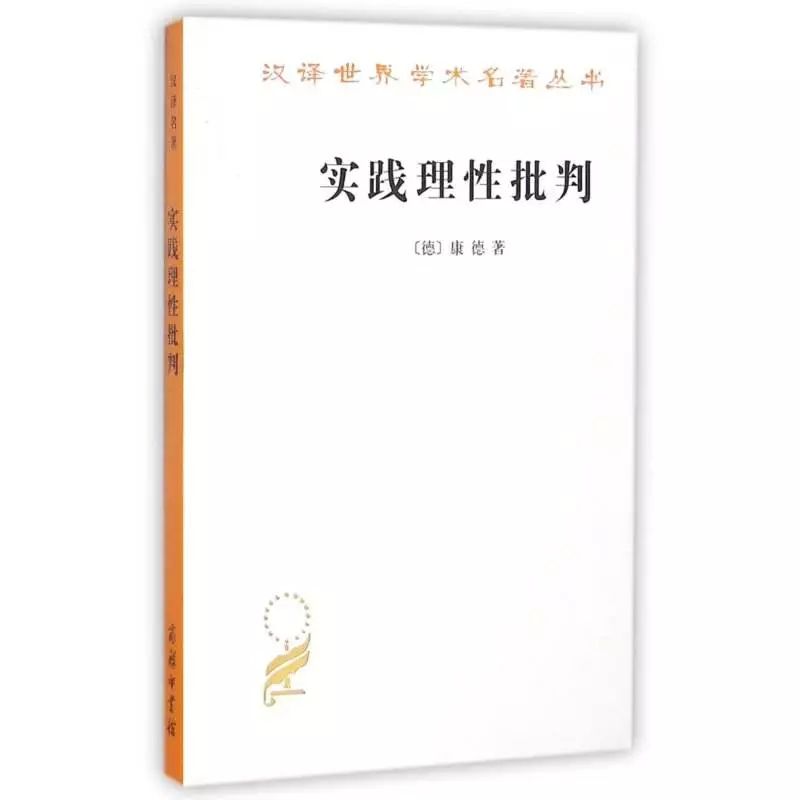
在康德看来,政治维护人的权利,恰恰是为了给予人以道德行为(行使其自由意志)的空间,道德是人对自身的规定和立法。
“法律的普遍性和先验性特点以及政治社会的法治特征,都要求政治社会坚持普遍的因而是最低限度的限制,以为人们的自由留有充分的余地,也就是说,不要去关心人们的经验的本性,不要去干涉人们对自己的自由的运用。”
[5]
因此,康德的权利-道德政治,就是给人以自我完善的自由。唯有警察思维的人,才以此为理由,对他人进行无所不在的管束。
康德以道德生活为国家的真正目的,并非意味着政府的道德管制。康德讲的
“道德”,不是具体的道德,而是说应该按照某种准则来行动。国家作为
道德共同体,是法治国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国家。后者以具体道德的方式治理人民,而在康德看来,这恰恰有悖于道德。法对于具体道德是中立的,不要求某种具体信仰,或具体幸福观或人生观,也不直接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
“如果政治制度以给人们的幸福规定道路或方式为目的,那它就会是家长式的专制或暴政,从而会损害人们的权利,尽管它的出发点可能是善意的。”国家可以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公民的外在行为,却不可以规定公民如何道德的行为,因为后者不可能来自外部,只能来自人格自身。因此,康德认为,“政府管得越多,法律就越没有力量,无情的专制主义在扼杀掉一切善的萌芽之后终将毁于无政府状态。”
[6]
一个以法权为基础的法治国家,是道德生活的政治条件;这是一个使道德行为成为可能的国家,它的目的就是保障每个人的可能的道德生活,。
第二个问题,与对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种传统看法有关。这一看法认为,霍布斯完成了国家主权的建构,洛克完成了社会主权的建构,而卢梭和康德完成了所谓个人主权——即拥有自由意志和良知的个人主权——的建构,从而形成了一条道德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现代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法、自由与强制力》对这一传统看法提出质疑,在根本上否认康德学说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页221)
对传统说法提出挑战自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是否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且为之提出充分的理由。该书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显然比较含混。有时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甚至私法观念,是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不是个人主义的,(页
219、180)有时又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不是个人主义的。(页40)如果说康德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有不同的基础,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如何来回应传统的说法?对这些重要的问题,该书似乎并未给予充分的回答。
该书又试图以自由秩序的概念,取代康德的个人自由和自主性的概念。但是,自由秩序究竟是什么意思,需要明确。它在何种意义上、在何种层面上可以取代有关康德政治哲学的传统说法,书中的讨论也比较缺乏。
第三个问题涉及书标题上的“强制力”概念。刚才李老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大陆的人,尤其我这个年纪的,对于把“强制力”理解为“暴力”,不会觉得吃惊。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国家意味着军队、监狱、法庭;而经验也告诉了我们这一本质。我觉得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对我们认识国家的本质是有好处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最终主张国家消亡。强制力和暴力的提法,前者是比较中性的,后者好像有负面意义,但实质差别不大。
关于“强制力”概念有几个小问题。
其一,“法”与“强制力”的关系。在本书中,“法”既意味着正当,又意味着法权,也意味着法律。但是,这些含义并非都与强制相关。严格地说,只有法律才与国家强制力本质相关。“法权”等概念与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概念应当做区分。
其二,本书突出了强制力的重要性。但是,强调强制力是否为康德的主张?认为“法”包含了“强制”要素,是康德法哲学的独特之处吗?在康德思想中,作为强制力的“法”是否如此重要?康德自然不会否认国家包含了强制力、“法律”以强制力为后盾,但是,这是否是康德思想的独特之处?我表示怀疑。
一种外在的自由秩序,是否一定要有外在强制(由他人施加的物理性强制)才成为必然?我觉得在这里,强制力与康德的“必然”之间不是必然的关系。事实上,哪怕有了强制力,也未见得成为必然。国家强制力无处不在,但犯罪照样有,可见强制未见得是必然。至于把人像物一样来摆布的那种“必然”强制,是否是康德所主张的,也是一个问题。强制力这个问题在全书中显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是否被过分强调了?
本书又把外在强制力的存在,追溯到这样的一个前提,即所谓人类学的事实,亦即人是一个身体性的存在。我以为这是对康德思想的一种解释。但是否符合康德的原意?讲一个人是一种二元论的存在,有灵魂、有身体,因为有身体,这个身体或肉身可能偏离他的理性的指导,所以,有可能作恶,所以,要有一种强制力迫使他服从。这一套说法其实非常古老,柏拉图似乎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好像并不特别属于康德的思想。尤其是,康德是否认为人的恶跟欲望或肉身有关,我觉得不能这样理解。人的恶,源于他的感官倾向或欲望,这样的说法是非康德式的。康德没有说一个人作恶是因为感官倾向或肉体欲望的主导,从而使他脱离了理性的管制。在康德看来,善恶取决于行为的准则,一个恶人是一个根据邪恶的准则行事的人,这一准则也可能是纯粹的且其动机并不源自感官倾向。如希特勒发动战争,这跟感官倾向、跟他的肉身欲望并无关系。所以,康德对“恶”的看法,不是像某些古典思想所主张的,欲望摆脱了理性的管制,而是说,因为行为的准则出了问题。这里是否把一套非常古老的说法和学说,来作为康德的“强制力”的基础了?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讨论、思考,它涉及前提性的问题。
如果说,“法”和“政治”的存在,与人的身体性相关,那么,什么存在与人的身体性无关呢,“伦理”的存在难道与人的身体性无关吗?书里的二分法——即把人分为内在、外在的两个部分,内在的即思想的和内心的生活,是私人的或伦理的,是自我对自我的关系,外在的即身体和身体以外的部分,是与他人的、外物的关系——是否成立?伦理尽管与人的内在动机相关,但同时也关涉人的外在行为。人的外在行为,既有以法来规范的方面,也有以伦理来规范的方面,伦理和法并不完全构成一个内在、一个外在的截然对立的两个方面。
而且,将人的思想和内心生活理解为内在的、私人的,把身体和身体以外的部分理解为外在的、公共的做法,恰恰颠倒了康德的思想。康德认为,人的合乎理性的思想和他的内心生活才是公共的,而着眼于人的身体及其利益的部分,倒是私人的。他在《答“何谓启蒙?”之问题》一文中区分了理性的公共的、自由的运用和理性的私自运用两者。康德说:“所谓‘其自己的理性之公开运用’,我是指某人
以学者底身分
面对
读者世界
底全体公众就其理性所作的运用。他在某一个委任于他的
公共的
职位或职务上可能就其理性所作的运用,我称之为其私自的运用。”[7]所谓“公共”与“私人”,显然无关乎身体之“内”与身体之“外”。
柄谷行人认为康德的《答“何谓启蒙?”之问题》一文完成了他所谓的“康德式转向”,即改变了“公共”的含义:真正的思想才是“公共的”,而从属于公职之任务的思想,反而是私人的。理性的思想者,康德所谓的“学者”(学者是“一个世界公共社会”的成员,以著作面对公众),在常人看来是私人,而在康德看来却是“公共的”。康德颠覆了一般人对公、私的看法。
在康德看来,一个人既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如一名公职人员,就他在职务活动中不是用理性独立思考,而是服从指令这一点而论,他是“私人的”;但是,只要他同时也自视为世界公民社会之成员,即以理性独立思考(因而也可以说是“学者”)时,也就是“公共的”。
在《系科之争》一文中,康德区分了
“学者”与“文士”(Literaten)。后者被认为是政府的工具,虽受过高等教育,却一般把学过的理论知识忘却,而只需记住与完成其社会公职所需的与其公职相关的政策上的(即与实践相关的)经验性知识,故
康德称之为学术的实务人士或技师(专业技术人员),如神职人员、司法人员和医生,他们作为政府工具,对公众有规约性的影响,故
“不能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公共地运用学术知识,而只能在相关系科的监督下来做”,所以“就必须被置于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下,以免他们僭越那本属于相应系科的指导权——因为他们直接地作用于无知的民众(如同牧师之于信众)……”
[8]
换言之,
“文士”是私人性的,而这恰恰是因为需要他们把政府政策传播给
民众的缘故。
(本文根据讨论发言整理。)
注释:
[1]
参见张旭:《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中的道德与政治》,见于《现代政治与道德》,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版,第163-164页。
[2]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617页
。
[3]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
——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1页
。
[4]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169页。
[5]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602页
。
[6]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第607页
。
[7]
《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李明辉译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2002年版,第29页。
[8]
康德:《论教育学》,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62页。
1、批评至上,杜绝吹捧
:我们要求评论人直击论文纰漏与不足,谨慎夸赞。
2、反复质疑,反复回应
:我们允许主讲人、评论人和提问者之间互相诘问,互相辩驳。只有时间限制,没有回合限制。(但我们保证两小时以上时间)
3、
帮你改论文,还给你发钱
:我们的目的是为主讲人的论文提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但是同时我们还给主讲人支付薄酬。
政治哲学工作坊征稿启事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哲学工作坊的目的是为全国各高校的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法哲学、伦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共同的学术交流平台。
欢迎全国各地的学术同仁(尤其是青年学者、硕博士研究生)向本工作坊提交学术论文,要求如下:
1.
论点明确:
请务必在摘要和导论中明确交代论点是什么,如何展开论证
2.
说理清晰:
请务必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展开讨论,拒绝故弄玄虚
3.
论文的字数以3万字为限
我们承诺为每篇入选论文邀请专业的评论人!
我们将支付薄酬给所有主讲人和评论人
!
政治哲学工作坊联系方式:
马华灵:[email protected]
朱佳峰:[email protected]
惠春寿:[email protected]
徐峰:[email protected]
政治哲学工作坊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政治哲学工作坊微信公众号:ecnuworkshop
政治哲学工作坊豆瓣小组:https://www.douban.com/group/604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