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
点击上方
"
行业研究报告
"订阅本号
,以便随时来访。
做投资其实是比较独的,真正在早期投资能获得成功的人其实都需要具备独立思维,提早布局、给投过的企业多一两年的空间。当然做有时候也比较反人性的,因为你投资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憋着一两年不说挺苦的。
PS: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究报告
”或者“
report88
”关注我们,点击“行业研究报告”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栏,有你想要的!
来源:徐传陞 沙丘学院
2008年,张颖、邵亦波和徐传陞成立了经纬中国。十年后,经纬中国已经成为业界赫赫有名的顶级投资机构。
在经纬中国期间,徐传陞主导投资了滴滴出行、恺英网络、博纳影业等知名公司的投资。
在加入经纬中国之前,徐传陞曾是华盈创投的联合创始合伙人,主要专注于互联网、新科技和医疗科技领域的投资,并主导了百度、分众传媒、瑞声科技、康辉骨科等投资。
以下内容根据沙丘学院导师徐传陞在沙丘学院课堂讲课笔记整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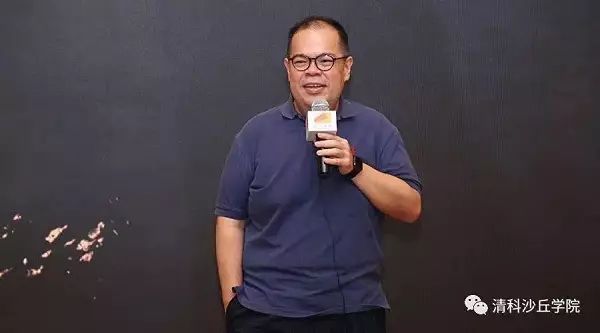
十七八年前,大家进入投资圈,其实很多人是误打误撞的。1999年第一波互联网浪潮兴起的时候,我在IBM软件部管理着200多个人。我觉得互联网好像一切以免费为主,是非常带动眼球的。那时我年轻又是学计算机的,觉得互联网浪潮非常有意思,就开始跟人交流。在2000年,我进入了早期风险投资行业。
一
误打误撞进入创投行业
在互联网泡沫时期融到第一笔资金
2000年2月,我加入了一家VC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个投资人;然后,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3月18号破了,当时感觉非常悲催的。在市场崩盘的时候去融资是你一生最痛苦的体验,我们吃了种种闭门羹。从2000年3、4月份我就跟另外两个合伙人到处融钱,用了大概十个月的时间,最终非常辛苦地融了三千三百万美金。
今天回想起来在那个时段能融到三千三百万美金真不容易,其中有一千万美金是新加坡政府的科技引导基金,因为相信我们所以就投了一点钱。然后上海市政府当时想跟新加坡政府合作,所以也投了一些人民币给我们,于是我们当时就成了上海第一个中外合资基金。我们在2000年底的时候,在市场上是非常少数的有钱人。
在2001年、2002年,我们大概投了三、四家公司,每家投了一两百万美金,在当时是挺大的一笔资金。我自己投的前三家公司,发展都是极其痛苦的。这几家公司的业务方向是针对企业的软件和服务模式,这样子的业务回头来看在中国其实是属于做得太早了。2002年底,我开始开窍了,关注了一些搜索、互联网商业模式等行业。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就参与投资了百度的B轮和阿里巴巴的C轮。
那个时候,我们跟今天在中国做到“大成”的创始人们有非常多直接的交流和对话,比如和李彦宏讨论互联网的商业模式。这对于我们最早开始做VC的这帮人来说,也有很多启发。当你对行业有一个敏锐度的时候,是可以看到一些机会的。从2003年开始,我在市场上摸索了两年多之后,开始进入一个比较顺利的阶段。我们基金陆陆续续投了百度、阿里巴巴,然后投了分众,瑞声科技的A轮。
做投资要选好自己的跑道 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一直觉得做投资并不是说投资人有多牛,而是说商业契机来临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好的眼光和运气搭上顺风车。
2005年我们投了几家好公司,包括阿里巴巴、百度、瑞声科技,还有分众传媒,四家公司全都上市了。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钝悟”的人,学东西比较慢,但比较坚持。一路走来,我觉得在投资方向的选择上很幸运,碰到了一些好的机会。这一系列公司的退出,让我感觉到自己开始明白投资的一些窍门,至少我给投资人的回报还是非常不错的。
做投资我自己一直秉承的观念,就是在每个要投的行业里面,你必须深刻地去了解机会是什么。很核心的一点就是选好自己的跑道,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所以还是要选好自己的战场。
从2000年的第一支基金现在陆陆续续做下来,如果两三年一个周期,我大概管了七八只基金了。因为我也管团队,我在内部的说法就是,作为早期的投资人,如果我们基金低于三倍净回报就是耻辱。基金投资能回三倍其实非常不容易,但我们做得不错。
那动力是什么?我认为做投资人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情。投资是个非常阳光的行业,我们每天跟创始人聊梦想,怎么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格局——这个是我做投资人非常强的内在动力。当然,每个人的内在驱动都不一样,赚钱对有些人来说也是很大的动力。
做VC的快乐感是非常强的,像我们去年投的ofo小黄车、之前投的滴滴快的,他们都在尝试以及正在改变行业的一些格局,非常有意思。跟这些创始人的交流和沟通,会让你的整个思维还有人生观一直处于非常亢奋、非常有意思的状态。
基金管理也是一门生意 提早布局给被投企业多一点空间
2000年,我进入投资行业一个月就遇到低潮期了,身边很多公司开始血淋淋的崩盘,所以我的感受可能比大部分人的认知更深刻。因为如果你在2000年的下半年进入投资跟创业真是非常痛苦,所有的公司都说没钱了,没有任何投资人愿意再加码了;纳斯达克崩盘了,市值跌了一半,国内也不可能有IPO……
在那种情况下,你完全没有公开的交易市场,包括一级市场也融不到资。今天的阿里巴巴是个2000亿美金的公司,但当年他们在2000年底的时候也遇到资金短缺,大家都是苦过来的,所以这种低谷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我一直觉得资本行业的小周期也挺明显的,过去十八年大概也经过四波的高峰低谷:1996到2000年这四年太嗨了,那2000年到2003年这三年就完全在消化这个市场的各种问题;然后2003年底开始慢慢复苏。其实整个互联网的大格局一直都是在变动中往前走,资金断裂只是中间的一些小插曲,资本行业整体的容量还是很大的。
投资基金管理也是一门生意,真正融到钱的人最终都是要投资的。一个早期投资机构想要持续发展,一定要能提前发现和抢到潜力领域、项目。行业里面确实也会有一些跟风,所以我们选择低调做事。现在经纬做投资几乎都不做任何战略战术的PR了,传递更多的都是基金层面的核心价值观。
做投资其实是比较独的,真正在早期投资能获得成功的人其实都需要具备独立思维,提早布局、给投过的企业多一两年的空间。当然要这么去做有时候也比较反人性,因为毕竟你投资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憋着一两年不说也挺苦的。
二
经纬中国的投资策略
2000年到2007年我在华盈创投,当时是联合创始人。经纬美国本身是1977年成立的,所以今年是40周年,也是非常低调的一个VC,风格非常务实。他们在2005年开始关注中国寻找合作的机会,然后张颖、邵亦波和我决定一起去做经纬中国。
2007年秋季iPhone 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不看好的,觉得移动应用是个很虚的概念。我们几个合伙人在一起商讨,觉得是不是整个所谓的PC互联网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不要专注于投移动互联网。所以随后我们在人才的格局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去找了非常多做互联网产品的年轻人来加入。从2010年到2014年,我们看了各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项目,大概投了30多家这个领域的公司。
2011年投了陌陌,2012年底我们投了饿了么,2013年我们投了快的,从2009年到2014年我们投了大部分头部优质的移动公司,这也奠定了经纬的品牌。经纬开始成立时就是要做一个不太一样的VC:第一,独立思维,不随波逐流;第二,一切以创业者为主。当你跟创始人有冲突的时候,你是不是以他为主,我觉得说起来很容易做出来非常难。
风险投资的核心是拥抱变化
其实做VC跟价值投资并不冲突,我们的核心是拥抱变化。作为早期的VC,变化一定是最核心的。互联网大概每五年有个迭代的周期,2000年可能是个工具导向, 2005年是娱乐导向,2010年是移动无线的元年,然后2015年是行业深度改造导向。
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我可以简单讲一些例子,比如单车,其实单车需求一直是存在的,麦肯锡做过调查,每天中国有三亿次的单车出行需求,可是为什么去年才开始爆火?一个核心因素就是过去单车是没有智能的。如果一个完全智能化的单车,你扫一个码能启动,能支付、又能定位、又能分发,它实际上就完成了闭环。同时,在互联网行业,永远都有竞争,这种态势也要求我们要有拥抱变化的心态。
2015年,随着行业深度改造导向,我们看到各种行业,其实刚刚过了中场休息,正在进入下半场。未来三五年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都是互联网跟移动互联网改革的下半场。现在BAT以及大的公司都在推动大量的人工智能跟智能学习,其实就是要抢占下半场的空间。所以,改造导向应该是未来五到七年一个很核心的、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变革。
创始人影响着基金风格 在“风起”之前抓住机会布局
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喜欢早于行业一两年去布局,而且我们也耐得住寂寞,很多时候都是静悄悄地在做投资。2015年是中国企业服务领域投资元年,这句话是经纬最早提出的。其实2013年初开始,经纬就开始做企业服务的系统布局,那个时候没有太多VC在关注这块创业机会;在2015年我们开始讲投资企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已经投了二十多家公司。
因为随着我们的布局和持续验证,我们发现,在一二线城市,人力成本越来越高IT成本越来越低,这与之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企业主也有动力开始用IT以及各种应用软件来提高企业效率。做早期投资必须在变革中去寻求一些创新的机会。
投资就是投人 创业者要有开放的思维
我看了这么多早期企业创始人,发现真是什么性格都有,风格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几个核心,一个是非常具有开放思维。我非常喜欢这种创始人,就是在沟通的时候他本身有很强的主见,当你跟他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会去深思熟虑,吸取各个产业的观点跟知识面,考虑之后,决定同意或者不同意你的观点。在创业这种非常多变化的环境里面,需要执着,也需要一些变通性,因时而变。
创业者、创业家其实都是最有勇气的人,妥协的勇气也是一个大局观。当年傅盛是猎豹大股东,猎豹与金山毒霸合并以后,他变成小股东,这对创始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可是它可以加速猎豹的发展。他思考了很久,最终选择了走这条路。
找到一个独角兽的创始人真的是万里挑一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
经纬中国投资案例分享
2008年的时候,海外的电影市场已经是夕阳产业了。为什么我们会投博纳电影,我也是在寻找一个潜在的机会。当时中国只有4000块大银幕,看电影是个非常贵的事情,每个人一次要一百多块钱。当时行业里像中影、大唐都是以国企公司为主,我们觉得这个机会好像挺有意思的。于冬是北影毕业的,科班出身,他觉得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六大、八大电影公司,我们相信了他的眼界跟愿景。当时我自己的推测是可能十年之后,中国能从4000块变成一万块银幕。我觉得机会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投了早期的这一轮。
其实我也没想到2016年在中国会超过四万多块银幕,比我自己预期大了四五倍的市场。所谓的发展,如果赌对人和趋势的时候,行业发展比你想象中要快得多,而且中间能带出一批公司,尤其是头部的公司。通过所谓的新经济还有技术的推动,使得整个市场的影响力更大。
我们实际上并不是第一轮投滴滴的投资方,当时我们投了快的A轮。这两个团队其实基因非常不一样,滴滴很重运营,因为他们是阿里系,有非常强的运营地推;快的本身是做产品起家的,2013、2014年他们推出这个应用的时候口碑非常好,大家觉得产品什么都做得非常好。我也参与了后来合并的谈判,两家以近乎对等的方式合在一起,合并后滴滴发展非常好。
三
如何打造极具战斗力的投
资团队
每一家基金,它本身有自己的一个文化跟底蕴,经纬在业界属于大部队的打法,整个投资团队有30多个人。我们想要在所有的行业里面都找到最优秀的公司,我们现在有七个合伙人,对特定领域有专注也有交叉,包括交易平台、企业服务、互联网金融、移动医疗、新技术、文化社区、消费升级、教育等。我们的打法有点像是组建了一个五到六人的特工队,每支队伍有一两个资深的合伙人带队。
对于搭建投资团队,清华北大的同学在我们这里是占的比例不大,我们比较倾向于找有情商以及足够智商,非常玩命努力的年轻人,然后给他们非常多的空间。我们的分析师都是第一时间出去跟创始人去交流的,有很大的自主空间。
投资一直有很多争议性,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做投资,能不能做好投资?投资是一个跟人性打交道,看局势看趋势看变革,对产品要了解,一个年轻人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去hold得住?这个争议一直是存在的,只能说从经纬过去十年的经验,我们相信年轻人是可以做投资的。他们需要引导,做早期投资是个学徒制,从完全不懂到刚刚懂些皮毛到懂得投资,这个积累需要时间也非常辛苦。
我们对团队的要求是挺严苛的,不只要投好,而且要投到最好,而且在你的领域里你一定要超前。经纬的整个文化就是追求卓越,以服务创始人为先,自身又要勤奋努力。
我们会有持续的回访机制,对一些我们没有投资的项目保持追踪。同时,我们也会不断给同事压力,为什么有些公司你没见过?这促使整个团队更有战斗力和活力。
我看到优秀的年轻投资同事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
在即使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他还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能够去推动一个正确的投资决定。
这个特性是可遇不可求的。
做早期投资,还是要多学习、多读书。不管你选择哪一个行业,你都应该尽可能地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做到多读书,多跟人家交流。不要闭门造车,也需要建立综合的学科知识体系,也要跟身边有多学科背景的人多交流。
尤其是你在接触自己不熟悉的行业时,你花三到五天时间做一些背景了解,然后能够找到行业里最优秀的人才去交流、去学习。我觉得学习对我来讲是个快乐的事情,这个对早期投资人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四
创业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对经历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人来讲,今天盛传的资本寒冬,其实只是一阵凉风吹了过来。
对当下深感凉意的创业者来说,从那个环境里跑出来的企业就非常值得借鉴。那时的百度和阿里巴巴与如今很多创业公司的处境相仿——左手握着高速扩张的钥匙,右手捧着如何盈利的问卷。而打动VC接受风险豪赌未来的关键因素是李彦宏和马云在困境中的表现。
百度那时已经融到了A轮,但李彦宏把最挣钱的技术支持服务砍掉了,坚持做一个独立的搜索网站。这就有了百度的初期商业模式——把搜索引擎卖给门户网站——带来比较充沛的现金流。
马云要做中国最大线上交易平台的时候,也还没有提出合理的商业模式,但是和李彦宏一样,他把事情给想清楚了。在第一步不挣钱的时候埋好了第二步或者第三步挣钱的线索,这能增强自己的信心,进而更容易去说服团队和资方。今天的创业者也一样,只要做到这一点,就不需要去理会外界对于「烧钱」的诟病,VC愿意把钱给这样的创业者去烧,而且烧得越多越好。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企业在启动期的时候,投资方都不会认为要很快盈利。因为创业公司一般在前面三四年都很难有造血的能力,我们更看重趋势、大方向、产品,希望创业者对自身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以前的创业公司通常是把商业模式建立起来,产生现金流,由投资方补充部分资金,企业可以慢慢打磨;但在过去两年半内,出现的问题是:
很多企业通过补贴「野蛮生长」,买单者是投资方。
在过去的两年里,天使轮和A轮的估值大致上升了50%,B轮、C轮之后的倍数甚至会高到五倍、十倍,我从业十几年来从没有看到过这种速度,这跟中国早期股市的疯狂很像,那时的上市公司拿了钱不知道怎么用就只能去地产行业买楼,今天就变成了创业公司拿着钱用补贴形式赠送出去换来一堆忠诚度要打上问号的用户。
在市场活跃的时候,投资人的热情很高,你可以快速拿钱,但你不能觉得融了一、两亿元就可以乱砸钱。现在融资会有更大挑战,我们对创业者这方面要求更高,所以创业者也不能以过去两年的资金热潮来考虑,总觉得后面有很多人追着投你,觉得商业模式可以通过依附撒钱来发展。
环境变差,好的一面是能够淘汰掉一些确实竞争力不够的公司,我们回顾泡沫碎掉的那个时期,像谷歌、亚马逊这样真正优秀的公司,一个都没死掉。同时,由于可投的选项减少,那些咬牙坚持的创业者反而更容易进入VC的视线中。
我在对创业者的观察上,不仅会和创业者聊,也会了解他的合伙人和员工的看法。
方向差一点没关系,但在人的选择上容不得丝毫掺水,一个项目的失败,十有八九是和人有关。
创业是艰难的,很多事情创业者要一开始就明白的,比如你要知道,可能有一天因为资金紧张,你必须要把跟自己最亲近的伙伴开掉,这些恶心的事情是创业过程里难逃的劫难。
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上,很多时候大家都想称王,最后做到NO.1,但是注定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做到顶峰。回到2005、2006年的视频大战,土豆优酷合并,从几十家变为五六家,至今视频领域仍然有四五家。中国这些大的平台都不太缺钱。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思考,争取大市场的目的是什么?
资本市场一定会越来越谨慎、理智,不会随便乱花钱。就算这半年你是第一,意义也并不大,企业最终还是靠长期运营。那么除了战斗到最后一刻之外,创业者有没有胸怀去放弃一些固有的坚持、以个人的退让为更好的产品和更远大的理想铺平道路,这关系到他的理念、胸怀和大局观。
另外,
互联网行业里没有那么多的天才,如果创业者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无论这个意见是来自VC的还是同事的
;以及你可以在听进去、想明白之后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只要这个迹象流露出来,至少我就会非常谨慎的评判他的项目。
在早期融资的时候,创始人是否具备清晰的用户场景思考是非常关键的,投资人会重点关注你所看到的痛点是否能够被你设计的场景有效的解决掉。
B和C轮之后,更多强调的是很强的执行跟运营能力。如何通过有效的执行和运营去获得规模化的用户是这个阶段的重点。例如运营、推广、聪明的广告营销等等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它靠的是专业团队跟外面服务团队的互相配合。
做事情很重要的是你要有对整个事情有大的前景跟格局观。在这个基础上对未来一段时间想达成的效果和所需的资源做出大致的估计。
我一般会问创业者
,你在平均18个月的时间长度里需要的资金规模大概是多少?在这种假设下,实际上你大概能估算出你用户的成长
。包括你对设备、存储等硬件的刚性的需求是什么;团队的增长,应该招什么人等事项都可以做出大致规划。
当然,实际做的过程里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你可能需要在算出来的所需资金额上乘以1.2。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投资人就很容易沟通。投资人会觉得是靠谱的,你算的越清楚,对投资人就简单一点。
最不应该做的就是经常说,我就觉得我公司值十个亿美金,自己就应该融一千万,稀释10%,然后你问他的时候,他根本就完全不了解这个钱,融资是干什么的。
个别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有一样的心理,包括内部的团队,普遍弥漫着一种融到钱,好象事情都成功了的心态,这就需要稍微敲敲警钟。创业是七八年的过程,很多时候某个阶段的融资,实际上只是代表那个时代的某个节点,钱特别多,特别热而已。
另外,我鼓励创业者向投资人提问说:你们的决策方式是怎么样的?你们的理念是什么?对于不好的VC,他们每个人回答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因为投资基金自身的文化是能够贯穿整个投资团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