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博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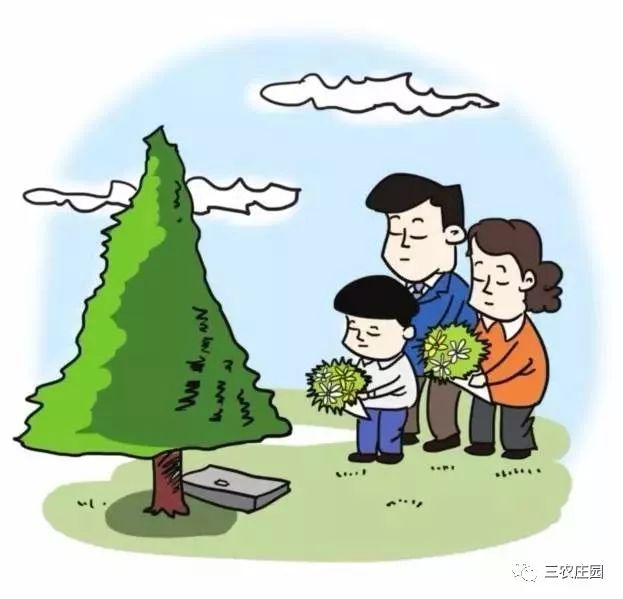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一共有20个字,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讲产业兴旺是重点,似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当然,大家也认可百姓生活富裕才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不过,生活富裕的含义,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还应该表现在精神层面,即所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正是如此,乡村振兴战略才对居住环境、乡风文明,社会治理有具体的要求。显而易见,生活富裕的精神层面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价值观决定的。所以,社会治理需要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乡村社会的有效
治理也莫不如此。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在判断究竟什么是对社会治理有效的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时,往往找不到尺度,尤其容易忽略社会存在的差异性。反映在操作层面,就是
习惯于对复杂的事情进行简单化处理,实行一刀切,从而使治理效果受到影响。
最近家乡传来消息,乡镇政府正在响应省里的号召,市里的部署和县里的安排,继前两年拆除土墙屋整治空心村,禁盖铁皮屋整治“乱搭建”之后,又轰轰烈烈地开展“禁止遗体土葬,推进殡葬改革”的所谓“零点行动”:即从2018年9月1日零点起,全面实施“遗体火化和公墓安葬”。有报道说,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在家乡所在的全市范围内,实现所有新增遗体火化率达到100%。当下正在进行的工作是,通过各种途径,让农民把家里为老人准备的“寿木(棺材)”在规定时间内主动上交,统一回收,集中处理,由地方财政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能够得到的信息看,家乡进行的这次殡葬改革,在省里并不是行动最早的,有的地方早在2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尽管这是一次大范围的统一行动,但网络舆论对“零点统一”、“强制火化”、“100%禁止土葬”还是有颇多不同的意见,因为大家对山区农村这个被称为以“推进移风易俗,实现绿色安葬”,“禁止土葬,一律火化”的全民殡葬改革
政策,起码还存在着两点疑虑:
一是疑虑土葬改火葬是否真的能够更有效保护绿水青山。
时至今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在人们心中逐步确立,人们对保护家乡“绿水青山”的认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是不可否认的。
殡葬改革的宣传显然看到了这一变化,因此在推进遗体火化的殡葬改革宣传中,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把它和节省耕地保护绿水青山联系在一起,以“土葬比火葬造成更多的土地和森林资源破坏”作为逻辑起点。如今人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显然也是对这一逻辑起点有着不同的认知。从技术上看,火葬是将遗体火化,将骨灰装入盒子,然后在公墓里选择一个穴位安葬,政府规定单个墓穴面积不超过0.6平方米;土葬是将遗体装入棺椁,安葬农家自由选择的地点。由于政府没有规定土葬的墓穴的面积,可能其面积会远超火葬公墓规定的0.6平方米。从这点来看,能否有效保护绿水青山,区别并不在于火葬还是土葬,而是在于政府是否有关于墓穴规格规定的制度供给。
那么
从逻辑上讲,
对于山区农村来说,只要像规定火葬公墓规格一样,规定合理的土葬墓穴规格,禁止占用农田耕地,因墓葬导致青山绿水受损的问题就可得到控制。因此,
火葬比土葬更能够有效保护青山绿水就似乎还没有得到合乎逻辑的说明。
以我个人的见识,火葬使用的技术方法是将遗体火化,需要消耗能源,且会排出废气,并不符合当今低碳减排的绿色理念;相反,土葬使用的木质棺椁随着遗体一起深埋,在数年之后必将回归到大自然当中,整个过程并不需要多消耗能源,多排放废气,似乎更接近绿色的理念。另外我们看到,在集中安葬的公墓里,花岗岩墓碑一个挨着一个,其间少有树木,年年月月,永远存在,公墓区类似于城市一样成为石头森林。反观分散于丘陵山坡当中的单个墓地,通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五服”观念之下,20年左右就会回到绿色森林当中。
我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上山砍柴,把一棵树的树枝清理干净后正准备砍树干,冷不丁发现这树干底下是一座坟头,吓得我魂飞魄散!现在回想起来,古往今来如此众多的逝者,留在我们视野中的墓地又有多少呢?连帝王将相的墓地都要靠偶然的考古才能发现,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土葬也能还原于青山绿水?不可否认,现在农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用不易还原生态的材料,为攀比建筑超豪华的墓地,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青山绿水的毁坏。但究其原因,并不在于土葬的方式,而在于对这种不节制的殡葬行为没有进行规制的必要的制度供给。那么我们现在将土葬改火葬与有效保护绿水青山联系起来的逻辑是什么呢?
二是疑虑土葬改火葬是否真的能够更有效防止攀比浪费。
殡葬改革的另一个理由是,如今农村丧葬出现了攀比现象,导致农民丧葬负担苦不堪言,因此需要移风易俗,实现厚养薄葬。显然,对于任何没有价值的攀比恶俗都应该摒弃,才能树文明清风,行有效治理,得生活富裕。不过,农村这样的攀比不仅在丧葬中存在,在婚嫁中也同样存在。
因此需要同样说明,土葬改火葬与制止攀比之风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从理论上说,攀比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源于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一卷,第24页),根据我长期对农村社会的观察,无论是丧葬的攀比还是婚嫁的攀比,事实上都是由这种攀比背后的物质利益关系引起的。在当下的农村,正式制度对物质利益关系的规范尚存在巨大的模糊空间,导致乡土社会中的关系资本对物质利益的获取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仪式,丧葬也好,婚嫁也好,不仅具有情感表达功能,还有社会竞争功能。因为红白喜事的规格直接影响着当事人在社会评价体系中的位置,而这种位置的高低又直接影响到其在乡土社会中的认同,进而直接影响到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最后决定的是他对社会资源获取的难以程度。所以,如果正式制度安排留给这种非正式制度获取物质利益的空间越大,攀比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一个人从农村出来进入城市,有稳定正式的工作单位,由于物质利益关系与乡土社会资本的联系被隔断,生活中所需的资源获取主要依赖正式制度安排,红白喜事攀比的事情就很少发生。由此看来,如果乡土社会里的物质利益关系依赖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制度这一状况不改变,简单将丧葬由土葬改为火葬,从逻辑上说并不能消除攀比的恶俗。因为在这里,葬礼是一种向外界展示社会位置的形式,跟有没有遗体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一盒骨灰,一件过往者穿过的服装,都可以成为葬礼表达这种关系的载体,古代不就有“衣冠冢”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将土葬改火葬与有效防止攀比浪费联系起来的逻辑又是什么呢?
我们肯定殡葬仪式应该做到有效保护绿水青山,坚决杜绝铺张浪费,因此赞成移风易俗,丧事从简。但是,火葬应该不是能够达到上述效果的唯一形式。火葬制度的出现,可能跟城市化进程相关,这是因为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里,人口密集使逝者单独求墓的需求难以满足,集中葬于公墓就成为必然;也许在平原地区,只有农田少有荒坡丘陵,分散土葬会占用农田,火化后集中公墓安葬或许能够节省耕地。我的家乡所在的地区,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二,有充足的条件实现不占用耕地的土葬。当然,如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观念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能够接受比土葬更为环保的殡葬方式,这是值得提倡的。比如,将火化后的骨灰撒入江海湖泊让其回归自然,或者植一棵树让骨灰伴随小树成长,这些生态化的殡葬模式,都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或许到那个阶段,火化替代土葬,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移风易俗,绿色殡葬。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强制推行100%的遗体火化与公墓安葬,可能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
一是可能增加乡村居民丧葬的经济成本。
这是因为,山区农民的居住十分分散,在我的家乡,距离县城最远的乡镇村落,足足有200公里之遥,尽管目前各地方政府承诺实行遗体的免费运送与火化,但丧葬不是简单的废弃物处理,传统的习俗将会出现许多与丧葬相关的服务。之前的土葬方式中,这些相关服务,比如守夜、遗容美化等等,是在农村村民之间的互助方式中完成的,现在到了县城就必须外购,而且农民面临的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垄断市场,农民没有还价能力,再加上墓穴属于稀缺资源,价格也会逐年抬高,林林总总所带来的丧葬经济成本,给山区农民带来的压力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二是可能增加乡村居民丧葬的心理成本。
千百年来山区农民把百年之后“入土为安”视为一种生命的归宿,如今突然之间要求火化,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人的认知水平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完全的改变,观念的改变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山区农村的老人,所受的文化教育十分有限,对遗体火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至可能出现以极端方式去面对。作为人的生命重要节点,这种带有高度情感功能的仪式感的突然变化,不仅会给老者带来心理负担,给家庭的晚辈也同样会带来心理压力。这种心理成本的增加,需要依靠时间去消除,因此,推行殡葬改革不可一蹴而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