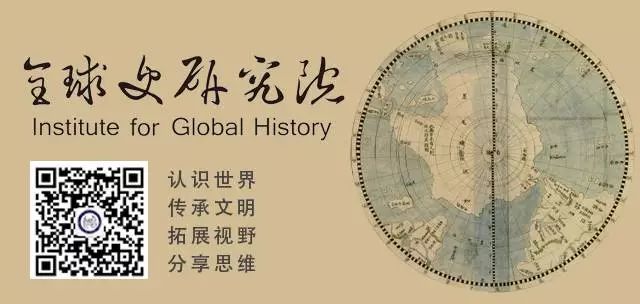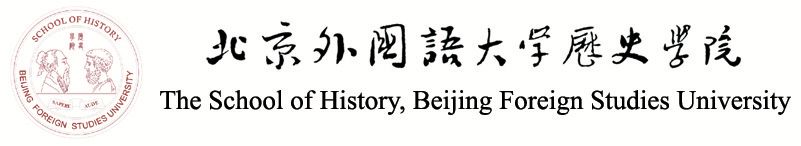
文章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
近年来,口述历史逐渐成为社会学、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尤其是对近现代的相关研究工作,各学界逐渐意识到口述史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定宜庄老师的《如何做口述历史》是一本写给从事口述史、历史、社会史方向学者的偏专业性读本,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探讨意味。口述史工作及其成果对于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来说,具备深刻意义。原因在于,口述史料(口述史工作成果)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它借助于音像手段,记录由访谈者精心设计的、与被访者间的对话,通过被访者对历史的口述,既可以弥补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又可以使大众的历史增添一抹鲜活生动的个人色彩。本期推送选取了书中第八章的第一节,以飨读者。感谢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授权转载。11月6日,文研院组织了一场围绕该书的读书活动,敬请关注。
如何将个人记忆从口述访谈稿转化成可供利用的史料, 并将其运用到学术研究之中,不致因无法有效运用而置于荒废甚至二次流失,是目前从事口述访谈的人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历史学家做口述史,如果访谈完成便到此为止,实在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以此为入口,可以“进入”很多故事,这才是做口述史最有意义、最引人兴趣的地方。其实,这也是促使我投入口述史工作的真正动因。
如何从口述史料进入历史,或者用口述史学者游鉴明的
话说,将口述置于历史的脉动里,是口述史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采集口述史料
(主要是现场访谈)
是第一阶段,对口述史料的鉴别整理是第二阶段,那么这个第三阶段,即使在口述史学界,也还没有多少人提到,更少有人尝试。而我认为,只有到这一阶段,史学的特点才得以凸显,才是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真正分道扬镳的阶段。
历史学家做口述历史,本来就不仅仅是为口述而做的。我曾经在某些公开场合说过,我希望学者不要将口述史当作一个专门的学科,而应该当作是一种研究方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看到有学者提出,不要将口述史独立于史学研究 之外,这就比我的说法更准确了。
▴
定宜庄《怎样做口述历史》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24年
历史学家做口述,从一开始的选题,就应该有自己的宗旨、主题,其后无论现场访谈还是访谈后的考证、注释和整理,都应该是沿着研究者的思路和设计走的,也应该是由研究者而不是受访者来把控全局。当然,好的研究者在这条预先设计的道路上,会不断有意外的发现。他会在路边看到太多事前未曾预料的风景,或鲜艳美丽、宏伟壮观,或荆棘丛
生、暗礁遍地,这一切复杂而丰富,既会让他惊喜,也会让他恐惧。然后,也许他会在这条道路上披荆斩棘,走入一片新天地;也许他会发现路边有一条岔路,路那边的风景更有吸引力,也便于他更好地发挥,于是改弦易辙;当然,也许他会发现此路不通,只能原路返回。但可以肯定的是,踏上这条路之后,他的遭际无论如何,在学术研究中都属正常,都是他的重大收获。这与做其他任何史学研究的过程、感受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好的口述史学者都需要有学科训练,也就是“门槛”。没有专业的基础,也提不出专业的问题,当然也不可能踏上这样一条道路,这不在本书讨 论的范围之内。
做口述史最吸引我的,就是可以通过一个人,发现他身后的一群人。这群人可能被文献记载过,更有可能没有。当
你拿着文献记载去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可能不在你预先知道的某个人群之中。我为佘幼芝做的访谈就是如此。
佘幼芝女士“守墓十七代”的故事,是我用史学考据的方式来分析一个口述访谈实录的最初尝试。
首先必须把这件事的背景简单交代一下。
袁崇焕
(1584—1630)
,广西藤县籍,东莞人。明朝万历己未年进士,曾坚守危在旦夕的宁远孤城
(今辽宁兴城)
,一战击退身经百战、战无不胜的后金可汗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既死,太宗皇太极继位,袁崇焕采取以和为守、以守为攻、乘机出战、以和谈为配合的方针,遭明廷指摘为“欺君”“诱敌胁和”等罪名。1629年
(崇祯二年)
皇太极率后金兵入关,直逼北京,袁崇焕率兵千里赴援,崇祯帝却听信谗言,以谋叛罪将其下狱磔死,家人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
佘女士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佘:我的先祖是袁大将军的一个谋士。我小时候老听我大伯说“谋士”“谋士”,我以为是磨刀的石头,我想我先祖怎么是石头呢(笑)。后来我妈给我写出来,我
才知道是“谋士”,所以对这事印象特别的深……袁大将军是广东东莞人,我们既是同乡又是上下级的关系。
(崇祯皇帝将袁崇焕杀害之后)我先祖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趁天黑的时候,把袁大将军的头从菜市口的旗杆子上盗下来,就偷偷地埋在我们的后院里。
自从我先祖把头盗了以后,就隐姓埋名,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当老百姓了。临终时把我们家人都叫到一起,就跟我们家里人说,我死以后把我埋在袁大将军的旁边,我们家辈辈守墓,我们一辈传一辈,不许回去南方,从此以后再也不许做官,所以我们遵守先祖的遗志和遗愿,一直守在这儿。到我这代已经是第十七代了。从 1630年8 月 16号是袁崇焕的忌日,到现在是371年。
听老家儿(北京话,指父母)传,因为我们是广东人,凡是住在北京的广东人死了以后就埋在我们这儿来,就把我们后院辟成广东义园。那时没有碑,都是坟头,你也不知道哪个是袁崇焕的。那时墙高着呢,人家就知道我们是看坟的,看广东义园的。
……那就一直到乾隆皇帝当政以后……
这个“守墓十七代”的故事,在北京城里一度家喻户晓。 而随着佘女士的声名鹊起,各种质疑、反对的声浪也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高,这些质疑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守墓十七代”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第二句话:如果是假的,这个口述还有任何意义吗?
我深知在佘女士对守墓经过的讲述中,的确存在大量漏洞。而我为佘女士做第一次访谈时,是把历史上的袁崇焕、 为他守墓的佘义士等,都作为一个大背景。我当时的关注点,其实是佘女士本人,是她作为北京人,尤其是北京南城的汉人,她和她家人的生活状态。其余我只将它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
本来,作为口述史的口述访谈,而不是讲求时效的新闻报道,很少是一次可以做好的,所以才有深入访谈之说。但由于我怀疑守墓一事的真伪,因此一度曾想放弃。这是我在第一次访谈之后,将此事搁置了一年半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决定再访,是因为其间又看到诸多相关资料,心中产生诸多疑问,决定对于相关问题,无论真假,最好还是一探究竟。
第二次访谈,我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佘家既然号称从此
一不考功名,二不做官,那他们守坟的生活来源是什么。
首先,袁崇焕祠与墓,都位于旧广东义园,旧日被称为“佘家营”。而佘女士家族几百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此地。所以我做的第一步,是观察当时的地图
(我选择了两张地图, 时间分别是 1928年(民国十七年)《京都市内外城详细地图》 和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北京市地图》)
,得知这20年间,在这一带分布最多的,主要是庙宇、义园、义地,还有所谓的育婴堂和牺流所。而这些庙宇,主要的用处是停灵。
义园,指的是旧时埋葬无名人士的义冢,广东义园就是埋葬在京的广东人的坟场。佘女士并没避讳这点,她说坟场就在他们家的后院:
那时没有碑,都是坟头……人家就知道我们是看坟的,看广东义园的。
我们是广东人,凡是住在北京的广东人死了以后就埋在我们这儿来,就把我们后院辟成广东义园。你也不知道哪个是袁崇焕的。那时墙高着呢。
也就是说,广东义园就是这众多义园中的一个。
如此之多的形形色色的“义园”,都是以被收葬者的原乡为单位并且命名的。或者说,虽然客死京城,也要埋葬在自己家乡建立的“义园”中,这是从清末到民国的北京
(北平)
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人死之后要实行土葬,所以北京城市周遭,就出现了成片的坟地。有关坟地与坟户,我在《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一书的诸多口述中都有涉及,但都是以北京城的居民为主,对于那些流寓京城最终未能返乡,而将遗骨葬在京师的,包括为他们提供安葬之所的义园以及守护义园的人们,却是被我忽略的众多题目之一。
义园与会馆主要都在城南,是当年外乡人来京后主要的集中地,是他们生活中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如今对北京城南会馆的研究连篇累牍,但对义园的研究却屈指可数。唯李二苓有《明清北京义地分布的变迁》一篇,是不可多得的填补空白之作。该文从明代义园的分布说起,提到1720年
(康熙五十九年)
曾禁城内丛葬,再到乾隆后这一禁令的逐渐宽松,然后详细讲述了光绪年间及以后,私立的义地几乎填满外城低洼易涝荒地的情况,而佘女士祖上守护的广东义园,便恰在她所述的这种外城低洼易涝荒地之上。从有清一代到新中国成立之间,南城
(亦即外城)
适宜居住、商业繁华之地是会馆集中处,而易涝的沙地和城墙根,尤其是广渠门内,也被称为“沙窝门”,就是因为遍布“沙窝子”所致, 广布义地和义园。
所谓广东义园,其实是两个。位于今东城区东花市斜街 50、52号的佘家馆,也就是我初次探访佘女士之处,称为旧义园,也是袁督师墓之所在。在旧义园之南,亦即今龙潭湖公园内的,则称新义园。佘女士对此是这样说的:
那时候我们这儿是老义园,龙潭湖那儿是新义园。 都是埋广东人。我们旧园都埋满了嘛,就再请个姓刘的 看着那个园。
广东义园在这一带占据的地方似乎不小,据当年我在这一带访问过的居民称:
这不是护城河嘛,这是外潘家窑,就是现在北京肿瘤医院那儿。里潘家窑就是现在的龙潭湖,你知道吗? 龙潭湖叫里潘家窑。这外潘家窑呢,不是一个苇坑,是仨。是这么一形儿,这儿有一块儿,这儿有一块儿,这 么三块儿,三块儿养鸭子。养鸭子北京5 家。
……
都是最大的(养鸭子的)。然后第四,里潘家窑, 里潘家窑到今儿是谁,我不知道,打听不着了。我估计啊,原来袁崇焕的墓在那儿,袁督师庙,龙潭湖那儿原来是广东义地,所以我觉得啊,原来这块儿的产业,应该是归他们广东人。原来是义地嘛,他们广东人不能回乡的都埋在这儿。是广东人,不会是咱北京的,等于说(跟我们)也不是朋友,也不是亲戚,没关系。
从这段话透露出两点:第一点,广东义园在这一片占地相当大;第二点,他们与当地的北京人并无来往。至于他们是否也曾养过鸭子,详情不得而知。
这成片的水涝沙地和上面破落的荒冢圮屋,在 1949年以后便成为北京城市改建中不可忽略的部分。这当然也波及广东义园。
义园的管理员,就是当时的守坟人——佘女士的伯父。 佘女士与她伯父一家虽然看起来关系不是太好,但访谈每到重要节点,还是必定要提起的。
一是有关为袁崇焕守墓的故事,佘女士也是从他口中得知的。
一是每次为袁崇焕举行祭典,也是由这位伯父带。 “那时候我伯父还在呢,到清明那天带全家祭祀去。”“由伯父烧上香,由他主祭,伙计点上香,大爷接过来插到香炉里,然后就磕头……”
尤其是关于迁坟事宜:“1952年毛主席说要把坟都迁到城外去,我伯父那时还在呢,他就特别着急,就立马儿呀找他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广东人哪,我伯父跟他们都是老世交似的。”
1955年要在这里建学校,也是由教育局和人民政府跟他谈,最后也是经由他的同意。
这个人物尽管隐而不宣,实际上家里的事情都是由他做主,在诸多问题上起到的作用都很关键。他与在京广东人,尤其是上层人士都存在广泛联系。尤为有趣的是,佘女士还不经意地提起,她父亲和伯父都过继给了旗人。这意味着, 这位伯父是作为旗人与广东人的双重身份活跃于在京广东人中间的。
这里要插一句的是,佘女士这段访谈充分表现了口述史的意义,它能够把想象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差异,在看似无意的闲谈之中呈现出来。
在我与苏柏玉一起去广渠门一带踏勘的时候,她提醒我阅读一部小说——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在这部张恨水写于 1924年的长达90万字的章回体小说中,对北京南城那些 外乡人的习俗和守坟人,有充实和生动的表现,其中写主角杨杏园道:
进得屋子来,长班跟着进来泡茶,顺手递了一封信给他。他拆开来一看,是同乡会的知单,上写着“明日
为清明佳节,凡我旅京乡人,例应往永定门外皖中义地,祭扫同乡前辈,事关义举,即恳台驾于上午八时前,驾临会馆,以便齐集前往为盼!皖中旅京同乡会启。”杨杏园想道:“同是天涯沦落人,一生一死,也值得祭扫一番,我明天就抽出一天的工夫,往城外走一回罢。”
……
杨杏园见草地上摆着一副冷三牲,三杯酒,三杯 茶,前面摆着一大堆纸钱。还有许多纸剪的招魂标,分插在各坟顶上。杨杏园对黄别山道:“这完全是我们南方的规矩。看见这些东西,好教人想起故园风景……”
说的是“皖中”,其实可以类推,理解为广东等地也未尝不可。
在描述这些人前往义园扫墓的同时,对“管理员”也就是守坟人做了一番描写,这里就不引述了,但可以联想到守坟人的样子,也能想象得到,他们与会馆里那些士人必有广泛的交情。
袁崇焕的故事,就是从广东义园的守坟人引申出来的,
篇幅有限,就不一一细说了。举这个例子,只是通过佘幼芝
口述,发现北京城,主要是南城,还有这样一个守坟人的群
体,虽然人数不会很多,却与南城的外乡人生活紧密相关,
这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旧日京城,尤其是研究者很少
注意到的广渠门一带的认识。
这样的例子,在口述中比比皆是。譬如前面多次提到的
常人春、常寿春兄弟,他们谈到祖父在清亡之后身处的社会
圈子和崇信的理教,让我们发现了原来未曾关注甚至也没认
识到的一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人既不属于皇室贵族,也
并非下层的穷苦旗丁,他们曾在政局的大改组、大变迁中,
得到了施展身手、飞黄腾达的机会,然后又在时代大潮落下
之后急剧衰退,他们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和社会交往圈乃至
日常的生活起居,都是我以往茫然不知的。由于在庞大的存
世文献中很难找到如此细致入微地描写这一层次的旗人群体
生活的资料,通过口述而获得的这一案例就显得殊为可贵,
对于丰富当时那段社会和历史的理解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