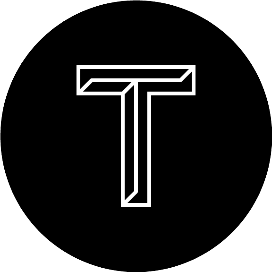今年的春节档尚未开战,就被冠以「史上最强」的称号。结果不负众望,票房达到 95.1 亿元,观影人次超过 1.87 亿次
(数据出自 2 月 5 日国家电影局的公告)
,双双刷新了历史纪录。《哪吒之魔童闹海》一骑绝尘,把竞争对手通通甩下,并最终超越《长津湖》,成为影史最卖座国片。
这是 2025 年中国电影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不可谓不亮眼。可振奋之余,不免令人担忧,毕竟去年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去年,同样是春节档盛世,随后的几大档期却相继遇冷。到年末清算,最终全年票房倒退回 10 年前,定格在 425.02 亿,其中春节档就占了近五分之一。
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年所谓的「神仙打架」。其实说白了,不过是其他档期通通失灵,使得中国的头部影视公司只敢寄希望于春节档。这并非不计后果的一意孤行,而已经是权衡了风险后的最优选择。
再考虑到中国有近 60% 的观众
(数据来自灯塔专业版)
一年只进一次影院,且这仅有的一次大概率会贡献给春节档,事实就更加触目惊心。大公司铆足了劲,杀红了眼,不过是为了争取这些来去匆匆的「过客」。换言之,中国电影产业历经 20 年还是没能培养出稳定的观影群体,使得电影只能沦作节日的祭品或短视频的周边。这才是这份成绩单背后,危机四伏的现实。

倒不是我想唱衰,或唱反调。实在是现实忧困,令人不敢乐观。
只要看看 2 月片单,就没法真的欢欣鼓舞。那里正静静躺着可怜的 7 部新片 ——《花样年华》《美国队长 4》《我们的命中注定》《多幸运遇见你》《边海》《诡才之道》《猫猫的奇幻漂流》,预示着烟花散去后的冷清,不日将至。

这个春节档的电影,确如烈火烹油。类型丰富、场面宏大,信息密度极高,狂轰滥炸不止。但剥开这些表面喧嚣,我们会发现,它们都在拍同一个母题,叫做「身份政治」。概括起来就是:「我是魔,不是仙」
(《哪吒之魔童闹海》)
;「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
(《唐探 1900》)
;「我是中原人,不是蒙古人」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我是西岐少主,不是殷商质子」
(《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
;以及「我是中国潜艇兵」
(《蛟龙行动》里面还唱了一首军歌,副歌第一句就是这句)
。弄清楚「我是谁,我是哪个阵营的,持什么立场,和谁是同温层」,在这个春天变得无比重要。

2021 年是「伤逝」。那正是疫情期间,即便在过大年,悲情也止不住地从银幕内溢出。于是《你好,李焕英》里,贾玲送别了母亲;《刺杀小说家》里,雷佳音失去了女儿;就连《唐探 3》这种搞笑片,也把「战火离乱」拿来,让自己在这个愁肠百转的节骨眼儿不至于太过没心没肺。
2023 年是「厉害国」。疫情刚刚过去,人们需要振奋,于是影院成了加油站、氧气罐、鸡血库。《满江红》的诗篇,要一起念诵出来,把激越千年的热血荡进当下时空;《流浪地球 2》里宏伟的逃跑计划要执行起来,而这次,是中国人在救世界于危难。
至于去年春节档,则是满屏「窝囊废」。《热辣滚烫》里的乐莹
(贾玲饰演)
、《飞驰人生 2》里的张弛
(沈腾饰演)
、《第二十条》里的韩明
(雷佳音饰演)
,全都是生活或事业的失意者。他们原本打算缩回自己的舒适区里认命苟活,最后发现不能这样,因为退无可退,避无可避,人必须还得做点什么,证明自己还在活着。这无疑也命中了经济下行,生活普遍困顿之下,人们在鸡血无效、振作无能,却又没办法退出游戏的情况下,只能坚持不退场的内心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春节档确实正在替代「春晚」,成为辞旧迎新之时,国人的一场仪式。这场仪式有宏观调控的成果,也有自我投射的成分,不管怎样,最终都会凝成一种教化,缝合在过去与未来的断裂处。
于是到今年,「身份」被有意无意地择选出来,成了首要问题,自然也是时代症候之体现。
为何身份变得如此重要?它是一种最小化的「成功」。
特别是当「做什么」不再能赋予一个人尊严和意义之时,强调「我是谁」,并为此感到自豪,便是每个人唯一能握紧的「微小叙事」。
然而,这个叙事同样是岌岌可危的。它不过是一套说辞,一种建构,之所以能成立,恰恰也因为它只需自洽,无需证明。正因如此,「他者」才成了极度危险的存在。只要有他者在,就会提醒「我」,「我」的这套叙事,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说,它不过是「我」的编造而已。于是这个世界呈现出一种极端的分裂,每个人都在严防他者的侵扰和动摇,而只和那些「看似是他者、其实是自我」的、如同无限复制体的同质化他人紧紧相拥。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春节档的电影都在贴身份标签。那不过是一种共同体幻觉的给予,是分清敌友、消灭他者的「新型叙事满足」。而在这个过程里,不同导演,又选择了不同路线。
林超贤和徐克这对「长津湖兄弟」属于乐此不疲。前者用行动两部曲,不断建构全球危机下的中国主体身份;而后者早在 2014 年,就曾主导过样板戏的翻新工作,如今又改编金庸,把侠之大者提炼为爱国英豪。
乌尔善的《封神》属于自担使命。这部神话大片的追求绝不止于奇观,或是做什么「中国版《指环王》」,而是要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借由商周之变背后的价值观更替,建立人伦道统。
向来精于算计的陈思诚,把《唐探 1900》书写为华工血泪史,使 「唐人街」不再是推理的架空舞台,而成了有所指的「半殖民」隐喻。整个案件最后得出的结论,实则直指美国建国之本 —— 记载着「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 的虚伪。撕碎绿卡、登上归国的航船,则是对「润」的拒绝,以及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遥远回应。
至于饺子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则对于「小爷是魔」的身份进行了二度确认。差别在于,前作还只是破除偏见的自我认可,而新作直接指向一种制度性不公:
「仙」建立了一套招安游戏,把听话的妖收编,去消灭在野的妖,好维持自己的绝对统治。
哪吒此时的身份觉醒就具有了一种阶层革命的意味。但吊诡之处在于,影片明明打开了丰富的隐喻空间,却又在美元符号、白宫、五角大楼等难辨真伪的解读中,迅速坍缩为简单的阵营对立,让人不禁感到迟疑,进而错愕。
总之,无论是官方授意、主动配合,还是夹带私货,这个春节档几乎百分百完成了「仪式」使命、上峰要求。
而且从票房看,或许这份要求,也是实打实的需求。

在 2018 年,今年春节档的对手林超贤和陈思诚早已有过对决,前者用《红海行动》以微弱优势打败了后者的《唐人街探案 2》。也正是那年,春节档在这两部大片的加持下,一跃突破 50 亿大关,并把观影人次提升至史无前例的 1.45 亿次
(此前还从未突破过 1 亿次)
。自此,春节档迅速膨胀,晋升为第一大档期。
也是那一年,电影局突然换了招牌,中美贸易战宣布打响。大环境的骤变,如暴风雨一般袭来,令人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