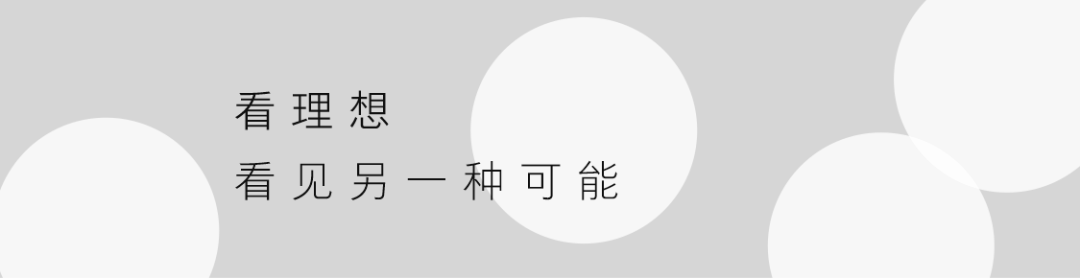
这几年,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而且可以预见,未来它会变得越来越显眼。老龄化带来的诸多困境里,“照护”问题首当其冲。
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96亿,其中失能老人超4600万;65岁以上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超1000万,每年约4000万人罹患焦虑障碍;有超过7000万人和伴侣动物共同生活——这些庞大、又稍许抽象的数字背后,是非常具体、日复一日的照料现实:情感陪伴、做饭量食、喂水喂药、翻身擦拭、换洗衣物、陪同就医……
它们正持续发生在不少人的现实生活里,而更多人在不远的未来也将成为同样的照护者。
音频节目《良善照护如何可能?我有一个问题05》已在看理想App上线。

在这档节目里,我们和几位新一代知识人与行动者一起,试图呼唤一些真切的提问:比如照护为何有时与暴力相伴?照护为什么总是女性的、家庭的?怎么不让照护成为奢侈的商品而是共享的福利?被照护者的福祉,一定要以照护者的牺牲为代价吗?养老机构能否成为可靠的照护选择?
当下,照护无疑是许多人正在或亟待面对的真实问题,我们希望透过这道充满困顿的窗口,将思辨与行动化成细密的针脚,在「共同在场」和「彼此承托」的信念中,一起探寻,良善照护如何可能?
为此,我们将
从节目上线起至2月14日(正月十七)
,向每一位看理想App登录用户发放1张本节目专属的优惠券
,希望我们都看顾好身心与彼此。
讲述|安孟竹
来源|节选自《良善照护如何可能?我有一个问题05》
01.
照护难题是社会现实的映射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江苏的一位中学老师用铁锤杀害了罹患自闭症、又因烧伤而瘫痪的19岁大女儿。据报道,这个女孩生前经常夜里叫嚷着要吃东西,生理期时会把床上弄得血迹斑斑,发脾气时咬碎过好几部手机,父母勉力维持着她每天的生存,却无法让她活得更好。
记者后来找到一封这位父亲留给妻子的信,信中写到,唯有他带大女儿走,妻子才能和小女儿好好生活下去。这则新闻开启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一个“慈父”陷入了“因关怀而杀害”的伦理困局?在与病痛和障碍纠缠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还能去想象一种值得过的生活?
田野调查期间,我遇到了很多像这个家庭一样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面对自闭症谱系孩子不同生命阶段挑战的家长们。他们时常焦虑孩子在照护机构里能否得到善待,在药物副作用和孩子频繁的情绪爆发之间他们左右为难……
《入殓师》
我也看见了一些心智障碍青年虽然已经成年、但依旧生活在父母庇护之下的困境;看见了他们的手足打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未来要照顾哥哥姐姐的人生使命……
这些他人的故事也时常把我带回自己的生命记忆中,让我意识到,照护中的困境其实不止是个人或家庭的难题,也是我们身处的某种社会现实的反映:在家长们的警惕和焦虑背后,是监管机制的匮乏与道德转型引发的信任危机;在他们过度保护、有时甚至变成了某种管控的做法背后,是一个对障碍者充满了歧视和排斥的社会环境。
这一切也迫使我继续思考,如果我们不愿意让照护者陷入这些两难的窘境,让照护变成个体和家庭独自面对的抉择与取舍,那么在公共服务建设、支持体系打造,以及社会行动等层面,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人类学的训练教会我,
做照护研究,不止是诉诸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脉络去理解他人的照护逻辑,理解别人如何想象生老病死,同时也是要将“照护”当成一面观察世界的透镜,并且通过他人的故事来反思自己。
同样,做这档节目对于我来说,也不只是在向公众传播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知识领域,它更是我和大家一起,在聆听他人的过程中,重新修习自己生命功课的契机。
02.
“反照护”时代的多重危机
套用研究日本高龄者照护的学者 Jason Danely 的一个比喻,照护之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就像城市里下水管道、电缆这样的基础设施,它们常常被埋在地下、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一如照护的工作总是被塞进厨房、厕所、床边这些不起眼的角落,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理所当然地存在,唯有出故障、出问题的时刻,它的重要性才被察觉。
在今天,正是由于种种照护危机的浮现,这个过去长久受到忽视的问题才开始得到重视和讨论。
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认为,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anti-care(或者说“反照护”)的时代,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猛进,效率和利益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
凯博文的这一结论源于他对美国医疗领域的观察批判。他发现,今天的生物医学教育倾向于把病患所承受的苦痛简化为病理切片和生化数据,而电子化的医疗责任管理系统将医生绑在写病历的任务上,使他们不得不压缩与病患沟通的时间。
相比于投入精力去理解病人的生命史,医生们更加依赖药物和手术刀的力量。这一切都使得“照护”的内涵正在从“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剥离。
《入殓师》
对另一位人类学家安玛莉·摩尔(Annemarie Mol)来说,医疗体系的照护危机体现在,治病这件事正在被一种“选择的逻辑”所主导。她发现医护工作者越来越像商场里的导购,他们的责任只是事不关己地给病患和家属提供不同的治疗选项,陈述每种方案的风险。
究竟要手术、化疗还是服药,要激进干预还是缓和治疗,最终要病患和家属自己来决定。一旦“做出明智的选择”变成了最重要的事,那么当治疗方案遭遇失败、或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时,我们似乎就只能把责任归咎于做出选择的自己。
医疗照护的危机只是广阔社会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左翼学者经常批评说,新自由主义社会从设计原则上就是缺乏照护精神的。新自由主义提倡公民自食其力,为自己负责,在有限的资源供给之下,将人们推入无止境的相互竞争中;鼓励大家关心自己的利益,漠视他人的苦痛和脆弱。
在这样的社会里,当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遭遇病痛、失能,照护往往变成了对于个人和家庭资源能力的考验。消费不起高质量照护服务的家庭只能依赖亲人的长期投入。
对照护的亲属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天长日久的陪伴与看顾,或许也意味着生涯轨迹的改变、逐渐收窄的活动空间和不断被挤压的自我。当它有一天终于变成一种难以继续承受的压力,似乎唯有用死亡才能结束一切、让彼此解脱。
从2021到2023年期间,仅香港一座城市就发生了8起家庭照顾者杀人事件。这些残酷的伦理悲剧也提醒我们,缺乏支持的照护只能导致对照护者个体的过度消耗、和被照护者难以维系的生活质量与体面。
照护出现危机,也并不总是源于照护的匮乏,有时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于“照护”这件事有着一系列的偏见和预设。
比方说,我们常常会把对孩子、残障者、老人的照护责任理所当然地归于家庭,然而正是这样的想象,成为了许多国家削减对于弱势人群提供福利支持的借口,而填补这种福利空白的往往是家中的女性。
再比如,每个国家、社会都会发展出一套关于照护的价值排序,认定什么样的人更值得去照护、什么样的问题更值得去关切,而这种价值排序也影响着公共资源分配的方式。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时期,一些国家依然选择投入大量的财力去购买军事装备,相比之下,那些承受着疫情威胁的医护人员、老人、穷困者、失业者得到的支持和保障则微乎其微。另一些国家则在防疫过程中,选择把照护的范围局限于“自己人”,以保护本国公民的名义把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移民阻挡在国境之外。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照护的不同尺度与视角之间常常发生对立。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对有权势者的照护往往意味着对低阶层、少数族裔和女性的剥削。而这种矛盾也体现在人类与其它物种的关系上。
需要承认,现代医学照护人类健康的能力不断增进,是以牺牲其它物种的生命为代价的。为了积极研发治疗疑难杂症的药物,我们长期默许制药行业进行残酷的动物实验,而很少人注意到,在这项以治愈为名的“高尚”事业背后,是肆虐全球的灵长类动物捕猎与走私贸易。
这种剥削一些生命、换取另一些人福祉和利益的照护真的可以持久吗?在照护这件事上,我们真的可以只在意眼前和附近,不看远方吗?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人类曾以关心地方发展的名义放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采,而今天,在对气候变化日益明显的感知中,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咽下的每一口食物中,我们都在承受着短视的代价。
在一个更加广阔和长远的尺度上,照顾好其它族群、物种,以及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星球,或许和照顾好我们自己与身边的人同样重要。
03.
关于良善照护的想象
在今天的中国,80-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正在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面对医疗成本的水涨船高、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照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都要回应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