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
·
显克微支(
1846 -1916
),波兰作家。代表作有通讯集《旅美书简》,历史小说三部曲
《火与剑》《
洪流
》《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历史小说《
十字军骑士
》。
显克微支出身于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
华沙
高等学校语文系学习,后因不满沙俄政府对学校的钳制愤然离校。1872年起任《波兰报》记者。大学时期即开始写作,是具有
民主主义
和
爱国主义
思想的现实主义作家,素有“波兰语言大师”之称。1896年,显克微支又完成了反映古罗马暴君尼禄的覆灭和早期基督教兴起的长篇历史小说《
你往何处去
》,1905年他因这部作品荣获
诺贝尔文学奖
。100多年来,显克微支的作品再版次数和印数均居波兰作家之首,并且被译成40余种外国文字,译本达2000多种。英
法等国曾掀起过
“
显克微支热
”
。

阅读前文:
亨利克
·
显克微支作
施蛰存译
然而,这时候,这两个孩子倒了霉,那个耍鞭子的艺术家走进马戏场里,而且正当他脾气最坏的时候,因为他刚才训练狮子完全失败了。那头猛兽己经老得脱了毛,顶高兴人们让它静静地休息,即使一刻儿也好。它怎么也不肯冲到这位艺术家跟前来,在棍子的打击之下,它尽在笼子里往里边躲。那班主很绝望地打算,如果在夜晚以前这头狮子还没有丢掉这忠诚脾气,那耍鞭子的一场表演就要失败了,因为鞭打一头尽在退避的狮子,正如吃龙虾先从尾巴吃起,不算本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使那班主的脾气变得更坏,那就是给他发卖站票的那个黑人来报告,说这些卡越拉人显然已经把他们采葡萄赚来的工钱全部喝光了;不错,他们来买票的人数倒真不少,可是他们付出来买票的不是现钱,而是印着
U.S
.字样的毯子,或是他们的妻子,特别是年老的妻子。
赚不到卡越拉人的钱,对于这位艺术家,这个损失倒不算小,因为他计算着要卖个“客满”,要是站票都卖不光,那就不可能“客满”了。因此那班主此时心里正在恨不得所有的印第安人只有一个背脊,让他可以当着所有的安那海谟人的面在这个背脊上表演一番(这是鞭打之意)。他在这样的心境中,走进到马戏场里,在木栅边看见了那匹马闲站着,神气很疲乏似的,他就气得想豁虎跳。奥尔索和琴妮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把手遮着眼睛,让篷布里透进来的阳光不致耀眼,他望到里边才看见了奥尔索,接着又看见了琴妮,跪伏在他跟前,把两个肘子搁在他膝盖上。看见了这情景,他就把鞭子尖儿撂在地上。
“奥尔索!”
一个霹雳打在这两个孩子身上也未必会使他们心里发生更大的恐慌。奥尔索马上跳起,从长板座位中间的过道里走出去,他那种匆急的行动宛如一头畜生听见了主人的声音而赶过去一样,小琴妮跟在他背后,吃惊得眼睛睁得挺大,一路冲撞在那些板凳上。
奥尔索走到场地里,就在栏杆旁边站住,阴沉沉地不做一声。从上面降下来的灰暗的阳光,很清楚地照出了他的生在两条短腿上的赫拉克勒斯似的身体。
“走近些!”那班主用粗哑的声音喊。
同时他的鞭子尖儿却在沙上蠕动,好像一头隐伏着的猛虎的尾巴,在不怀好意地摆动。
奥尔索往前走了几步,他们俩彼此瞪着眼看了一会儿。
大体说来,这时候班主的脸色很像一个驯兽师,走进笼子去鞭打一头危险的野兽,但同时也在注视它。
怒火占了谨慎的上风。他的两条穿在鹿皮短裤和高统靴里的细瘦的腿,气得跳动起来了。也许,引起他这么大的怒气来的,不单是这两个孩子的懒惰。
琴妮在上面板凳中间看着他们,正如一头牝鹿在看着两头雄鹿。
“小流氓!捉狗的,贱货!”那班主咬牙切齿地骂着。
他的鞭子以闪电似的速度画了一个圆圈;嘘,呼,随即啪地打了下来。奥尔索轻轻的哼了一声,就向前窜进一步;但立刻就被另外一鞭子止住了,于是接着第三鞭、第四鞭……第十鞭。表演开始了,虽然还没有看客。这位大艺术家的擎起的手臂动都不动一动;只是把他的手转着,好像这是装在一个尖轴上的一架机器上的一部分,每一转就使奥尔索的皮肉上吃着一鞭。这个鞭子,或者还不如说这个恶毒的鞭尖儿,仿佛竟塞满了这个大力士和班主之间的一切空隙。那班主,渐渐地打得兴奋起来,浸沉在一种真正的艺术家的热忱里面了。这位大名家不过是在偶尔即兴罢了。可是那条在空中闪亮的鞭子已经在大力士的项颈上画出了两圈血痕,这是到晚上就得用粉敷掩起来的。
在鞭子的跳舞中,奥尔索始终不做声,但每打一鞭之后,他就向前跨进一步,那班主就退后一步。他们就这样的在满个场地上绕圈子;后来那班主闪出了场地,完全像一个驯兽师似的闪出笼子,终于在马厩门口消失了,也跟一个驯兽师一般无二。
但是,在走出去的时候,他的眼光落在琴妮身上。
“上马去!”他喊着,“以后再跟你算帐!”
他的声音还没有响完,白裙子已经在空中闪动,琴妮一眨眼就跳上马背,像一只猴子。
班主走进了幕后,看不见了;马就在场地里跑圈子,有时把它的蹄踢着木栅。
“嗨!嗨!”琴妮以一个细弱的声音喊,“嗨!嗨!”但是这几声“嗨!嗨!”同时也就是一种呜咽。那匹马愈跑愈快,马蹄乱踢着,碰到了木栅便更猛力地仰身避过。小姑娘站在马鞍上,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看样子好像她的脚尖儿竟没有碰着鞍子;她两条赤裸的、红红的臂膀,做着很快的动作,以维持身子的平衡;她的鬈发和轻纱的裙子,被气流推送着,就飘在她那像一只在空中盘旋的鸟似的纤瘦的身子背后了。
“嗨!嗨!”她又叫着。她眼眶里充满了眼泪,因此她就不得不抬起头来看东西了,马的快跑使她头昏眼花;一层层高起来的看台、墙壁和演技的场地,都开始在她四周旋转起来。她晃了一晃,接着又晃了一下,终于跌落在奥尔索的怀里。
“啊,奥尔索!可怜的奥尔索!”小姑娘呜咽着说。
“怎么回事,琪?”那青年轻声地问,“你为什么哭?不要哭,琪!没有打痛我多少,根本没有什么痛。”
琴妮把两条手膀勾上他的项颈,就吻着他的脸儿。她浑身都兴奋得震颤了,她的哭泣差不多变成了痉挛。
“奥尔索!啊,奥尔索!”她再三再四地喊着,说不出别的话来,她的手膀紧紧地勾着他的脖子。如果她自己挨了鞭打,她也未必会哭得更厉害些,所以,到后来反而是他来安慰她了。他忘记了自己的创痛,把她抱在怀里,拥在心头;他的被鞭打得胀起的神经,使他开始感觉到他在爱她,还不仅像一头獒犬爱它的情侣呢。他的呼吸很急促,他嘴里就跟着间歇的呼吸而断续地说:
“什么东西都打不痛我,你在我身边,我很高兴啊——琴妮,琴妮!”
其时那班主怒气冲冲地大踏步穿过马厩,妒忌钻进了他心底。他看见了那小姑娘跪伏在奥尔索面前,这个美丽的孩子有时曾经在他心里唤起了一种仿佛是还没有十分发展的下流感情。可是他怀疑她和奥尔索有了暖昧,因此就蓄意要报复了。他一定可以在鞭打她的时候获得极度的喜悦——在狠狠地打她一顿的时候;他抵抗不了这种欲念。过了一会儿,他就叫她了。
她挣脱了那大力士的手膀,一眨眼就在黑暗的马厩门里消失了。奥尔索好像呆木了似的,他并不跟着她走进去,而是蹒跚地走到一条板凳边,坐下了,急剧地喘息起来。
那小姑娘跑进马厩里,最初竟看不见人,因为那儿比场地里更为黑暗。但是,惟恐她会因为不立刻服从命令而挨骂,所以就用一个低低的、担惊害怕的声音叫道:
“我来了,老爷,我来了!”
就在这一刻儿,班主的手已经抓住了她的小手,一个粗鲁的声音喝道:
“过来!”
他一声不响地拖着她向化妆室里走去,如果他对她发作一阵,或者吆喝一顿,也就不至于使她惊惶到这样了。她一路往后挣扎,用尽她的力量来抗拒他,尽快地再三说:
“亲爱的,好心的赫尔希先生!我以后决不……”
但是他到底威逼着把她拖进了那个贮藏许多服装的、狭长的、开着的房间里,反身锁上了门。
琴妮连忙跪下来,抬着眼,交叉着手,像一张树叶似的颤抖着,满眶的眼泪,她想以祈求来使他心软,但他的回答是从墙上拿下一条鞭子,说道:
“躺下来!”
于是她绝望地抓住了他的脚,因为她几乎已经吓得半死了。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颤抖得像乐器上的一根绷紧的弦子。但是尽管她祈求似的把苍白的嘴唇贴在他那光亮的长统靴上,也还是白费。甚至她的恐惧和乞求反而更鼓励了他。他扭住她的裙带,把她放在一堆乱摊在桌上的衣服上,可是还费了一点时间,才止住了她两腿的乱抖乱踢,终于挥鞭打下去。
“奥尔索!奥尔索!”那姑娘大叫起来。
在同一个时候,房门一直震动到铰链上,从顶到底裂开了,整整的半扇门,被一股大力气所冲破,砰的一声倒在地上。
在那破口里立着的是奥尔索。
鞭子从班主手里掉下了,他脸上罩着一重死尸的灰白色,因为奥尔索这时的脸色确是非常可怕。他的一双眼睛在翻着白眼,他那个大嘴巴边满是泡沫;他的头向前低着,宛如一颗牡牛的头,他全身聚精会神地紧张着,好像准备投身于一个危险。
“滚出去!”那班主吆喝着,企图以这一声喊叫掩饰他的恐惧。
但是这一回,他们的联系可断绝了;平时一举一动都顺从得像一条狗的奥尔索,现在却更低倒了头,恶兆似的慢慢地走向这位神鞭艺术家,好像有一股卓越的力量在胀起他的钢铁般的筋肉。
“救命!救命!”这艺术家叫喊了。
人们听到了他的叫喊。
四个魁梧的黑人飞快地从马厩里穿进那扇破门直向奥尔索扑过去。于是开始了一场可怕的搏斗,那班主牙齿打着颤在旁边看着。好久好久,只见一堆互相扭结的黑身体在乱七八糟地回转着、动着、互相追绕着、猛烈地摔击着;在他们周围的寂静中,只听见时而有一声呻吟,时而有一声鼻子里出来的哼响或喘息。但过了一会儿,有一个黑人,好像被一种超人的神力从乱轰轰的一堆中抛掷出来,平平直直的打半空里跌落在班主的身边,砰的一头撞在地板上;随后就是第二个黑人给摔了出来;最后,在这一堆打架的人中间,只站起来一个奥尔索,他的脸色比刚才更加可怕,满身血迹,头发都根根倒竖了。他的膝头底下还压住了两个晕厥过去的黑人。他跳起身来奔向那班主。
那班主闭了眼睛。
就在这一霎时,他觉得他两脚已经不碰着地板,他觉得好像在腾空飞去,此后他就什么都不觉得了,因为他全身撞上了留着未倒的半扇房门,就毫无知觉地跌落在地上。

奥尔索抹一抹脸,走到琴妮身边。
“来吧
!
”他温和地说。
他拉了她的手,就一起走了出去。这时满城的人都在跟随着大车的游行队伍和那架唱“美国佬杜特尔”的机器,所以马戏场四周冷清清地没有一个人。只有那些鹦鹉在架子上摇荡着,叫得怪聒噪的。
两个孩子手牵手地一直往前走,向着街路尽处可以望得见的一大片仙人掌地里走去。他们一声不响地走过了许多给攸加利树遮荫着的屋子,以后又走过了屠宰作坊,那里有成千累百红翅膀的黑椋鸟在绕着那作坊飞翔。他们又跳过了那条大灌溉渠,走进一个桔树林,从这个桔树林再走出去,他们就在许多仙人掌丛里了。
现在他们已经到了荒野里。
一眼看去,这种多刺的植物愈长愈高;错乱不清的仙人掌从另外一片掌上生出来,拦阻了路,以它们的芒刺勾住了琴妮的衣服。有时那些仙人掌长得非常高,使这两个孩子好像置身于森林里,但是即使在这森林里,也没有人会找到他们的。他们一路前行,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只求愈走愈远。有些地方,仙人掌的尖堆较少些,他们就可以看到远在天边的那些青翠的桑达—安娜山峰。他们就对着这些山峰走去。灰色的刈麦蝉在仙人掌丛中鸣唱着,阳光泛滥地晒着大地;干燥的土地坼裂成一片龟纹网;坚硬的仙人掌好像热得反而软了些,花都挂了下来,枯萎了一半。
他们俩静静地、沉思地一路走去。周围的一切都是很新奇的,他们不久就完全移神于眼前所见的印象,连苦楚都忘记了。琴妮的两眼看着一堆一堆的仙人掌;此刻她把疑问的眼光停在仙人掌堆里。不时轻轻地问道:
“这里就是荒野了吗,奥尔索?”
但是这荒野里好像并不是空无生物的。从远处仙人掌堆里响出了松鸡的叫声,附近四周也响着各种奇怪的唧唧吱吱、嘀嘀答答和喃喃的声音,总而言之,是生活在这些仙人掌丛里的小动物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声音。一会儿,一大群松鸡飞了起来,一会儿,又是许多头上生着肉冠的秧鸡迈着长脚跑掉了,黑色的栗鼠在听见两个孩子走近时纷纷跳进地洞里去;到处都有兔子在乱奔乱窜;花金鼠蹲在它们的小腿上,呆在洞口,很像胖胖的德国农民站在自家的门口。
这两个孩子又往前走了一阵子,不久,琴妮觉得口渴了。奥尔索心里显然觉醒了印第安人的聪明,就帮助她采撷霸王梨吃。这种果实在每一块开花的仙人掌上都生得不少。在撷取的时候,他们手上都刺着了许多细如毫发的芒刺,但是他们都觉得这果实又甜又酸,味道很好。既能止渴,又可解饥。这荒野就像母亲似的把这两个孩子喂了一饱。等到力气健足,他们才更向前走。一路过去,仙人掌愈堆愈高;简直可以说是一树一树接叠着长起来的。

他们脚底下的地在慢慢地一路高起来。从这些小丘上回头再看一眼,他们看到了在远处半隐半现的安那海谟城,像一大丛树木生在一块低地上。马戏场一点也看不见了。因为他们始终坚持不变地对准着那些山峰走了整整几小时,所以现在这些山峰的轮廓已愈来愈清楚了。这个地区已经换了一种模样。在仙人掌丛里,出现了各种灌木,甚至还有了树。桑达—安娜山脉的有树木的一部分山麓就从此开始了。奥尔索折断了一株小树,修掉了枝叶,做成一根棍子,这东西在他手里,可能就成为一件可怕的武器。这个印第安人的本能在告诉他,在山里头,有一根细杖总比空手好些,尤其是因为太阳已经在渐渐地西沉了。它的巨大的火焰的盾牌已经远在安那海谟之外,正在向海洋里沉下去。过了一会儿,太阳就看不见了,但是在西边,红的、金黄的、橙色的晚霞,象一条条长带子似的,满天铺展。山峰屹然耸立在这些光彩里;仙人掌显出了各种奇异的形状,有的像人,有的像兽。琴妮觉得又疲倦又想睡,但是两个人都用出全力急忙向山里走去,虽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目的何在。果然他们不久就看到了山崖,走到山崖底下,发现丁一道溪水,喝过了水,他们就沿溪走去。那些山崖起先是破碎剥落的,这时却变成为整块石壁,愈走过去,这些石壁也愈加高峻,于是他们就走进了一个峡谷。
晚霞在消隐下去,逐渐加深的黑暗笼罩了大地。有好几处地方,藤蔓从峡谷的这一边爬到了那一边,好像在溪上结成一个穹顶,这里就完全黑暗而且很阴森可怕了。头顶上可以听到有树木的声音,但在底下却看不见它们。奥尔索猜想这一定就是荒野了,因此也就一定是充满了野兽的地方。他们不时听到各种可疑的声音从那边传来,到了夜里,他们很清楚地听到了粗哑的鹿鸣、美洲狮子的咆哮和凄厉的山犬嗥叫声。
“你害怕吗,琪?”奥尔索问。
“不!”小姑娘回答。
可是她已经非常疲乏,一步都不能走了。奥尔索就把她抱着走。他继续向前去,希望走到一个垦荒的人家,或者墨西哥人的帐篷。有一两次他好像远远地看见了一只野兽的闪亮的眼睛。他把一只膀子紧紧地将熟睡的琴妮抱在胸前,另外一只手里紧紧地捏着他的棍子。他自己也很疲倦了。尽管他有很大力气,琴妮已经使他觉得沉重了,尤其是他把一条左臂抱着她,而想空出一只右手来作防卫用,那就更觉得不支了。他不时停下来换一口气,于是再往前走。忽然他站住了,仔细地听着。他觉得仿佛有一个铃铛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就象那些垦荒的人在夜晚挂在牛羊项颈上的铃铛。他赶紧再向前走去,不久就到了溪流转弯的地方。铃声格外清楚了,最后又加上了一阵狗吠声。奥尔索断定他现在已经走近了有人住的地方。这正是他的紧要关头,他在白天里已经筋疲力尽,现在他的气力正支持不住了。他又转了一个弯,才看见一点亮光;再走上前去,他的敏锐的眼睛就看出了是一堆火。一只狗,显然是拴在一株树上的,正在挣扎着狂吠。最后他看见一个人坐在火边。
“但愿这个人是那本好书里的人。”他心里想。
于是他决定叫醒琴妮。
“琪!”他喊道,“快醒来,我们就有吃的了!”
“什么事?”这姑娘问,“我们在哪儿啦?”
“在荒野里。”
她醒来了。
“可是那亮光是什么?”
“有人住在那儿。我们就有吃的了。”
可怜的奥尔索实在饿极了。
此时他们已经走近了那堆火。狗吠得更厉害了。坐在火旁的那个老头儿把手罩着眼往黑暗里瞧。过了一会儿他才问:
“谁在那儿?”
“是我们,”琴妮用她细小的声音回答,“我们饿极了。”
“走近一些!”那老头儿说。
从一块隐藏着他们的大石头背后走出来,他们站在柴火跟前,彼此牵着手。老头儿很吃惊地看着他们,不知不觉地叫出来:
“怎么回事?”
因为他看见的景象,在这荒僻无人的桑达—安娜山中,会使任何人都大吃一惊的。奥尔索和琴妮都穿着他们演出的服装。这美丽的小姑娘,穿了粉红紧身裤和一条短裙,忽然出现在柴火光中,看来就好似一个幻异的气仙。她背后站着一个异常壮健的少年,穿了肉色的紧身裤,筋肉鼓起着,宛如橡树上的瘿结,隔着紧身裤也看得清。
这垦荒的老头儿瞪着眼看他们。
“你们是干什么的?”他问。
那个小女人,显然认为她自己的口才比她的同伴好些,所以就抢着像鸟鸣似的回答:
“我们是马戏班里的,好大爷。赫尔希先生把奥尔索打得很凶,后来他又要打我;可是奥尔索不让他打我,他就打了赫尔希先生和四个黑人;因此我们就逃到荒野里来,我们在仙人掌里走了好久,后来奥尔索抱了我走;于是我们走到这里来了,我们很想吃点东西呢。”
这个老隐士的脸慢慢地光亮起来,他的眼睛以一副仁慈的、父亲般的表情看着这个急着想一口气把什么都说完的美丽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他问。
“琴妮。”
“哦,那么,琴妮,欢迎你,还有你,奥尔索!我很少碰见人。走过来,琴妮。”
这小姑娘毫不踌躇地把她的两只赤裸的手臂挽上了老头儿的项颈,热烈地吻着他。她以为他就是那本“好书”里的人。
“可是赫尔希先生会不会找到我们在这里呀?”她的红红的嘴唇离开了这个垦荒老人的枯干的脸,就这样问。
“他只会找到一颗子弹!”老头儿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是不是你们刚才说要吃呀?”
“啊,很想呢!”
那垦荒老人在柴火灰堆里扒了一阵子,取出了一只挺好的鹿后腿,香味四下里散发开来。于是他们坐下来吃。
夜景真是美极了;在峡谷上面的高高的天空中,流转着一轮明月;夜莺在林莽中美妙地唱起歌来,柴火也喜悦地爆响着,奥尔索高兴得又在自言自语了。他和那小姑娘吃得好像付了钱似的;但是那老隐士却吃不下,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看了小琴妮,眼睛里就满是泪水。也许他在好久以前做过父亲,也许因为他在山里难得见到人。
从此以后,这三个人就在一起过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载于《译文》1954年第1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相关阅读:
小说欣赏|罗稻香【朝鲜】:哑巴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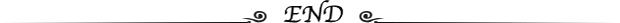
《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010-59366555
订阅微信:
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
[email protected]
投稿及联系邮箱: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