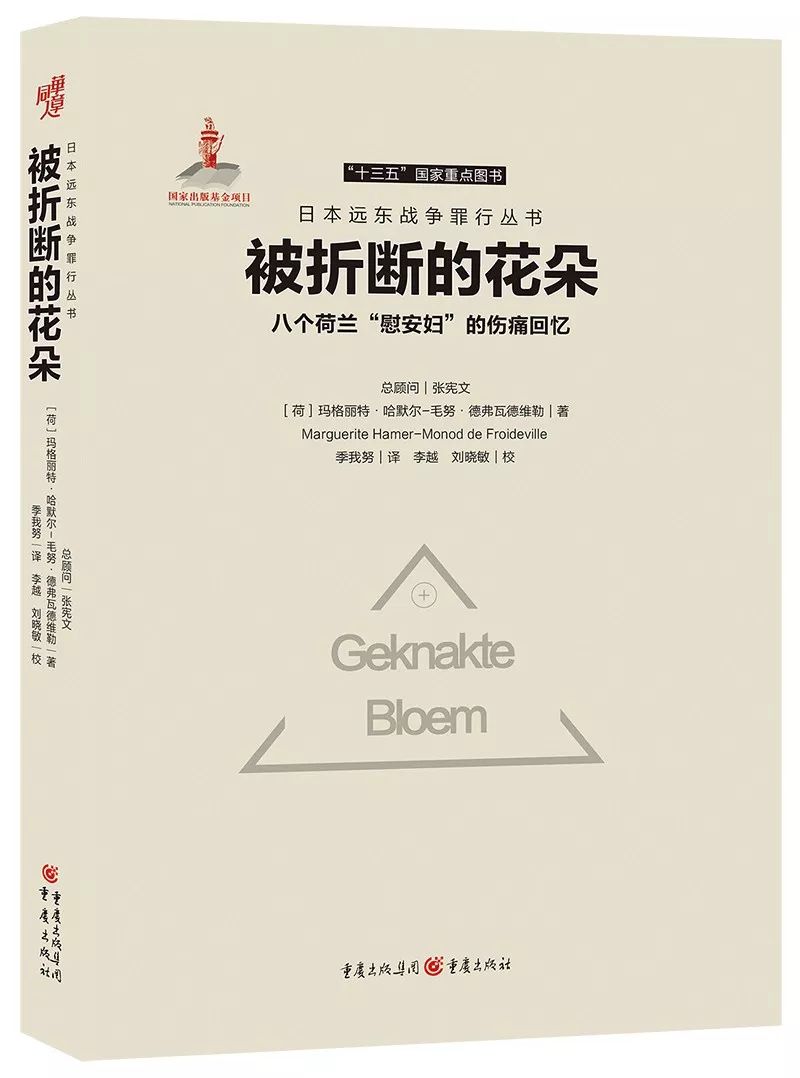
众所周知,日本在二战期间在日本、朝鲜、中国,以及广大的东南亚占领区强征“慰安妇”。鲜为人知的是,大量处于日军占领区的白人妇女也被强征为“慰安妇”。由季我努学社策划并翻译,于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被折断的花朵:八个荷兰“慰安妇”的伤痛回忆》一书,还原了这段历史。
一、血色太阳摧残鲜艳花蕾
本书之所以取名为“被折断的花朵”,源于84岁去世的荷兰“慰安妇”埃卢娜写下的一首诗:
写下这首诗的几个月后,埃卢娜就与世长辞了。
这首诗带给本书作者玛格丽特·哈默尔-毛努·德弗瓦德维勒极大的震撼,她觉得陷入日军魔爪的荷兰“慰安妇”就像被折断的鲜艳花朵。荷兰少女们被来自“东方日出之国”的禽兽们摧残,受到非人的折磨,临终前都满怀难以忘却的伤痛。
德弗瓦德维勒女士是欧洲著名社会活动家,是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在荷兰启动的“荷兰项目实施委员会”主席,也是荷兰“慰安妇”受害者保密顾问。1943年,年仅2岁的玛格丽特和母亲就被日军关押到了印尼的苏腊巴亚和安巴拉瓦集中营,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荷兰。她毕业于荷兰最著名的莱顿大学,攻读法律。1993年,玛格丽特加入了“日本赔款基金会”,致力于法律诉讼迫使日本政府承认罪责,并向荷兰受害者道歉、赔偿。
玛格丽特对于荷兰“慰安妇”历史的追寻和关怀,使得她在欧洲和日本享有崇高的声望,日本天皇夫妇、荷兰女王与公主多次接见她。日本政府多次邀请她访问日本。在她的不懈努力之下,很多荷兰“慰安妇”拿到了日本“亚洲妇女基金”的“补偿”。玛格丽特作为荷兰“慰安妇”的保密顾问,了解到了大量第一手的日军征发荷兰女性充当“慰安妇”的证据,因此成就了这一本揭露日本征发白人妇女充当“慰安妇”暴行的力作。
作者对于她所接触的荷兰“慰安妇”充满了同情,她的同情心和使命感,使她成为了很多“慰安妇”最真挚的朋友。她深刻同情荷兰“慰安妇”在战时以及战后的遭遇,并给予了最深切的理解和关怀。作者发现,绝大多数“慰安妇”都有着深刻的精神创伤。日军依仗暴力强加在“慰安妇”身上的邪恶暴行,让她们充满羞耻感和内疚感。而“慰安妇”自己是无法在内心深处排解对于遭受性暴力的羞耻感和内疚感的。她们害怕她们的可怕遭遇被别人知道,所以选择沉默。她们在心理上将自己关进充满绝望和恐惧的小黑屋,心理压力和彻骨仇恨让她们痛苦不已,甚至痛恨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可怜的女性。这些消极情绪经常会引起身体不适,甚至会让她们病魔缠身。头痛、梦魇、神经衰弱,这些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会伴随她们终生。
玛格丽特采访的荷兰“慰安妇”有很多位,但是最终同意她将自己的遭遇写进书中的只有八位,并且她们只同意玛格丽特采用化名。她们分别是玛露塔、诺露切、埃卢娜、埃伦、贝齐、提奈卡、莉娅、叶妮。
二、从“地狱里走来”的玛露塔
玛露塔,1925年出生于苏腊卡尔塔(梭罗),她在那里度过了少女时代。她是荷兰人与当地土著混血的后代。她6岁的时候,生父去世了。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位荷兰人。二战爆发后,继父被征召进荷兰军队,战争中被日军俘虏,先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后来又被日本人送到福冈煤矿中强制劳动。由于玛露塔的祖上是荷兰与当地土著的混血,所以日军没有强制她和母亲住到关押荷兰人的集中营里去。
继父被荷兰军队征召后,玛露塔家的日子非常艰难。日军占领梭罗后,玛露塔一家搬到农村的一所小房子里居住。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她不得不帮助母亲制作动物玩具,以补贴家用。由于玛露塔长得漂亮,卖玩具的工作就交给她了。
1944年4月的一天,18岁的玛露塔带着玩具在路上售卖,突然碰到两个日本宪兵。日本宪兵从汽车上下来,问玛露塔干什么的。她回答是卖东西的。日本兵一把抓住她,把她塞进了车里。她被带到一所房子里,到傍晚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百名左右的小女孩和青年女子。很多女孩和玛露塔一样,都是被日本宪兵抓来的。日本宪兵闯到老百姓家里,带走年轻姑娘,母亲们请求用自己代替,日本宪兵置之不理。还有一部分女孩和少女,是梭罗当地投靠日本人的败类带来的。
玛露塔和30名同伴,被送到了一所旅馆,这里已经被日军改建成“慰安所”。经过几个日本兵从头到脚的检查,10个长得不够漂亮的女孩被放走了,包括玛露塔在内的20个比较漂亮的女孩被留了下来。随后医生对她们进行了体检,他们被日本兵牢牢地按在检查台上,日本医生用一支金属器具插进她们的身体,除去了她们的处女膜。姑娘们拼命大喊,使劲挣脱,无济于事。被日本医生“检查”完身体后,姑娘们又被送回原来的房间。日本人送来吃的,没有人吃得下。
姑娘们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被押上火车,被送到了苏门答腊。玛露塔和7个姑娘又被挑出来,押上卡车,送到港口。随后上了货船。日本兵在甲板上铺了垫子,她们就睡在垫子上。5天后,船靠岸了,姑娘们到达了目的地,弗洛勒斯岛日本海军“慰安所”——一座建在海岸边的楼房。
到了岛上,她们才知道,日本兵把她们弄来,是为了“给岛上的日本兵享乐的”。姑娘们都十分害怕,因为她们没有过性经验。第二天中午,第一批“客人”进入了“慰安所”。可怕的一幕就此拉开。有姑娘哭着想逃跑,被卫兵抓住,扔回了房间。日本兵们对这些姑娘肆意凌辱施暴。从那天开始,她们就像是被放在传送带上一样,每次都要被数十个日本兵连续强奸。虽然有规定日本士兵要使用避孕套,可没人理睬那些规定。一年后,玛露塔的地狱般的生活终结了,因为她被查出患有性病。对日军而言,她已经没有用了。玛露塔得以解脱,她和两位怀孕的同伴,搭乘当地渔民的渔船,逃回苏门答腊,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了自己家。
回到自己家后,她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母亲。母亲根本不相信她说的话,相反母亲认为她卖掉了家里赖以生活的那些玩具,带着钱自己跑掉了。因为失去了本钱,玛露塔的小弟弟在她回家前的几个月死掉了。在家里待不下去,她出门投奔了一个女朋友。之后,她移居荷兰。日军在弗洛勒斯岛日军“慰安所”对她的野蛮强暴,让她染上了终身都没有治愈的性病,她再也不相信男人,终身未婚,也不与任何男性打交道。她与家人断绝联系,因为母亲和继父的女儿,认为她是“给日本人当娼妇的女人”。但是她并不记恨家人。她与玛格丽特成为了好朋友,她自称“从地狱里走过来的人”。
三、害怕横着面向床铺的日本军官佩刀的诺露切
诺露切在玛格丽特采访的“慰安妇”中,也是最悲惨的一位。诺露切和玛格丽特采访的很多“慰安妇”太不相同。其他的荷兰“慰安妇”要么是终身不婚,要么是结婚后很快离婚,要么是找到了一个包容她们的丈夫,婚姻生活还比较美满。被日军强迫为“慰安妇”,已经够悲惨。她被解救后,回归家庭,承受了丈夫和公婆的长期指责,仍然整天生活在噩梦中。“慰安妇”的经历,不仅影响她,也影响着她的孩子们,她的丈夫和公婆,导致所有人都生活在痛苦当中。
诺露切是混血儿,二战爆发前,她已经结婚,嫁给了自己的丈夫亨库,住在爪哇岛的苏腊巴亚市。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亨库沦为战俘,后来被送去修缅泰死亡铁路。诺露切带着幼子回到了娘家。她母亲住在苏腊巴亚甘邦部落。与母亲同住的还有诺露切的未婚妹妹伊娜。一家人艰难地维持着生计。
1943年的一天,一辆日军的卡车来到了部落。一名日本佐官带着几个日本兵下了车,大声命令,全部落的所有女性集合。诺露切和伊娜猜到日本人是来抓年轻女孩的,就跑回家躲在箱子里。有一个不怀好意的邻居告密,指着诺露切的母亲说,她家有两个年轻女孩。日本军官威胁道,叫她们出来,不然惩罚你们全家人。诺露切和伊娜听到声音,就出来了。诺露切牵着幼子的小手。母亲指着伊娜对日本军官说,这个女儿你们可以带走,请把她留下,她刚当上妈妈,需要照顾孩子。日本军官打量了伊娜和诺露切说道,“不行,这个太瘦了”。他用军刀指着诺露切说,“你上车,不上车,就没命。”诺露切松开儿子的小手,伤心欲绝地上了车。日本兵命令诺露切的母亲给她收拾几件换洗衣服,不一会儿,一个装着她衣服的行李上被母亲拎上卡车。
诺露切被日本兵送到苏腊巴亚日本军官住的旅馆。日本人告诉她们,主要工作是做杂工,在食堂打打饭,在酒吧打打杂。但是后来她们才知道,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给日本军官提供性服务。旅馆四周都是日本兵,她们根本逃不出去。这里实际上就是日军的高级“慰安所”,只是没有挂牌子而已。
白天的生活还算安稳,她被安排在食堂干活,吃得不算差,因为日本客人的剩下的残羹冷炙,她可以吃到。不过到了晚上,就是天壤之别了。晚上她被安排在酒吧干活,需要给日本军官没完没了的斟酒,日本军官对她和同伴动手动脚,肆意抚摸她们是家常便饭。她们还不敢反抗,惹日本军官不高兴了,就会遭到殴打。日本军官喝醉了,就跟野兽没分别。他们会粗暴地把姑娘们拖到房间里施暴。诺露切因为反抗了一名军官,惨遭这个军官的非人虐待。经历了几次这样的事情后,所有姑娘们都学乖了,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接受日本军官的调戏和蹂躏。诺露切对付日本军官的手段是,尽量使他们快点结束对她的暴行。
诺露切说,有些日本军官还是很温和的。有几位日本军官对诺露切很温柔,他们与她发生性关系时,不会粗暴地殴打她。他们会慢慢地脱掉衣服,然后去洗澡。但是她还是很害怕,因为日本军官发起疯来,根本没有人性。她尤其害怕日本军官横放在椅子上的佩刀,她认为这是日本军官对她的威慑,刀口指向她是一种威慑的仪式。所以即使是这些比较温和的军官,也让她感到提心吊胆。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旅馆里来了很多年轻的飞行员。这些都是神风特攻队的队员。他们给姑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飞行员一踏进房间,就坐在床边嚎啕大哭起来。他们把自己身上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一股脑地塞给了姑娘们。诺露切问自己接待的那个日本飞行员,为什么哭。飞行员说,“我们明天要去那里!去了那里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是去死。”后来姑娘们和诺露切交流说,这些大多数未满十八岁的飞行员基本上一夜都在哭泣,没有几个碰姑娘们的。他们哭完了,就睡着了,只有少数几个和姑娘发生了关系。
诺露切一直在“慰安所”里待到战争结束,她被英军解救出来。她出来后,就往母亲家里跑去。找到母亲家,儿子和母亲都在,妹妹已经不在了。母亲告诉她,后来日本兵又来抓姑娘,妹妹被抓走了。1946年诺露切带着儿子回到荷兰,找到了婆家,并幸运地和自己的丈夫重逢。丈夫被日本兵抓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活着回到荷兰。他一回到荷兰,就返回印度尼西亚,找寻妻儿。没找到又回到荷兰,没想到妻儿找来了。当年11月,夫妻团圆,但是诺露切由于羞耻,并没有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告诉丈夫。
1947年1月,亨库又返回苏腊巴亚,寻找诺露切的母亲和妹妹。从伊娜处得知了诺露切的遭遇,伊娜对姐姐很是鄙视,称之为“日本人的娼妇”。从此诺露切的生活又重新回到地狱。亨库受不了打击,人生观崩塌了,开始沉迷于酒色,经常几天不回家。公婆对诺露切的态度也变差了。亨库开始轻视她,经常用“日本人的娼妇”来辱骂她。不过,他们依旧生活在一起,因为孩子,诺露切委曲求全地保全这个家。从1947年到1953年,她又生下了五个孩子。她外出,一些荷兰男人也想占她的便宜,因为她名声坏了。
无穷无尽的羞辱,让她快要崩溃了,最后是天主教的乌尔苏拉修女收留了她和孩子们。不过,后来情况得到改观,1953年,亨库被派到新几内亚岛工作了一年。他在当地听到了日军强迫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事情,他相信了诺露切的话。他回到荷兰后,把她和孩子接回家,从此再也不提“日本人的娼妇”这样的话。即使两个人吵架,他也绝口不提。发生在诺露切身上的事情给孩子们留下了疮疤,虽然母亲从未对他们讲过自己的悲惨遭遇,但是从小目睹父亲和祖父母对自己母亲的恶劣态度的孩子们,心灵已经受到了伤害。直到2003年诺露切离开人世前的三个星期,她的一个儿子才鼓起勇气,询问妈妈的遭遇。诺露切最终还是选择闭口不谈。诺露切带着一生的伤痛离开了人世。
四、被强奸到怀孕的埃卢娜
1944年2月被关押在巴达维亚集中营的埃卢娜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当时埃卢娜21岁。日军在集中营中挑选了10多个长相俊秀的荷兰女孩,诱骗她们,说是要将她们送到烟草厂去工作。随即用步枪逼着这些女孩登上卡车,送到三宝垄的日军“慰安所”。埃卢娜到时,发现“慰安所”里已经站着很多姑娘。刚到“慰安所”日军就强迫姑娘们签订了全部是用日文写成的文件。姑娘们根本看不懂,在被日军逼迫签字后,她们就成了“自愿”为日军服务的“慰安妇”。签完字后,姑娘们被分送到三宝垄的各处“慰安所”。
埃卢娜和8个同伴被送到“慰安所”的第二天早上,就被安排去被日本医生“检查身体”。2个日本兵把她死死地按在桌子上,日本医生从她的下体开始检查。在屈辱的检查结束后,日本“妈妈桑”对姑娘们训话,你们要温柔地接待兵大爷,要让兵大爷们“开心、舒服”。“妈妈桑”要求姑娘们尽量要求“兵大爷们使用避孕套”,因为日本军队非常害怕士兵被传染上性病。“妈妈桑”特别交代,在“兵大爷们完事后”,姑娘们要用注射器往阴道内注射一种“清洗剂”,以保持身体清洁。
当天晚上,一个日本军官来到埃卢娜的房间,粗暴地夺取了她的贞操。埃卢娜对军官大吼,拼命甩开那双想要抚摸自己身体的大手,不准他碰触自己的身体。她拼尽全力地踢、推搡、撕咬、抓挠对方。日本军官抽出寒光闪闪的军刀威胁她,并使劲抽打她的嘴巴。埃卢娜力气用尽,无法反抗,军官强行压住她,剥光了她的衣服,强奸了她。随后,她又受到日本医生和“慰安所”老板的强奸。第二天,埃卢娜从别的同伴那里知道,她们也受到了同样的摧残。日本军官享有强暴处女的特权。
第二天,埃卢娜和同伴们开始了“接客”的生涯。日本士兵一个挨一个地来到她的房间强奸她,不顾她的哭泣和哀求,继续侵犯她,一个完了以后,下一个接着来,似乎没有尽头。埃卢娜和同伴们被带到的是为下级军官和士兵服务的低级慰安所,这些日本禽兽从来不使用避孕套。埃卢娜说,有同伴发疯似地数次扑向日本兵的刀尖,拼命抵抗,但是仍然无济于事。“慰安所”老板恐吓她们,如果再反抗,就杀掉她们在集中营的家人。
几天后,姑娘们像没有意识的木偶,习惯了日军连续不断的强奸。埃卢娜每天要遭到20个左右的日本兵的强奸。她像行尸走肉一样,任凭日本士兵欺负,从来不按照老板要求地那样——“热情地迎接兵大爷”。她在遭受强奸时,尽量去回想小时候一些美好的事情,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减轻自己的痛苦。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突然有一天,这家“慰安所”被突然关闭了。埃卢娜被送到了茂物附近的戈塔帕利集中营。可怕的是,埃卢娜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是一个基督徒,是不能容许自己堕胎的。不安、悲伤、绝望、愤怒,一波一波向她袭来。不过对于凌辱自己的日本兵的憎恨,最终让她下定决心,选择堕胎。她知道自己绝不会去爱这个有着深深伤害她的日本人的血统的孩子,甚至她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集中营条件简陋,没有任何麻醉药,老天爷怜悯她,手术一开始,她就失去了知觉,胎儿被集中营的荷兰女医生取了出来。埃卢娜还是幸运的,后来还可以生儿育女。她的父亲死在了日军强迫修建的缅泰死亡铁路工地。
五、被强奸时总是想美好事情的埃伦
荷兰女孩埃伦,一直生活在荷属东印度东爪哇省任抹县的一个小镇上,升入高中时,父母把她送到三宝垄读书。1942年2月27日,由于日军即将登陆,高中被迫关闭,她回到家中。3月1日,日军登陆爪哇岛,埃伦的父亲被日军俘虏。她和母亲、哥哥、妹妹被日军关进任抹县的集中营,随后日军把她们集中到中爪哇的哈马黑拉岛集中营。哈马黑拉岛集中营生活条件非常恶劣,饮用水短缺,食物配给很少,且相当低劣,拥挤不堪,病人很多。
1944年2月20日,几名日本军官来到集中营,经过三轮筛选,从集中营中15-30岁的女子中,选出了15名女子。日本军官哄骗埃伦和其他被选出来的同伴,是要送他们去烟草厂工作,或者送去当护士。
26日,埃伦和同伴们被装上卡车,被日本兵带到三宝垄的一座祠堂。埃伦进来时发现,这里关着更多的年轻女孩。通过简单交流,她得知这些女孩都是被日本兵从各个集中营抓来的。日本兵使用暴力,强迫她们在全是日语的文件上签字,没有一个姑娘能够逃脱。后来埃伦才知道,签了这个文件,等于同意“自愿去卖淫”。签完字后,日本兵就把姑娘们分成四拨,送往不同的“慰安所”。埃伦被送到一座大楼,这里已经被改成“慰安所”。埃伦分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衣橱、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床,还有一个洗手池。
3月1日,“慰安所”开张了。这个“慰安所”不仅接待日本军人,还接待日本普通人。这个“慰安所”属于相对高级的“慰安所”,只在晚上开门迎客。嫖客们通常一待就是通宵,只要姑娘们不顺从,嫖客们就狠狠地殴打她们。刚开始埃伦和同伴们也是拼命反抗,但是丝毫不起作用。埃伦最终放弃了反抗,但是她从不配合。
接客的时候,她总是穿着一条凤尾草叶纹的黄色连衣裙,像个木头人一样躺在床上,任由嫖客撩起她的连衣裙,满足自己的欲望。她从来不会去看对方一眼,所以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使用避孕套。她只是紧闭着双唇,竭力去想别的事,默默地承受着日本男人的凌辱。在整个过程中,她的思想都试图离开自己的躯体。那些男人在她身上根本不可能享受到丝毫快感。
周日是她们的噩梦,因为周日她们会被送到专门接待日本兵的“慰安所”去。整天都要接受几十个日本兵的强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个月后,埃伦突然被日本人放了。她登上汽车时,把那条象征着屈辱的黄色连衣裙扔出了窗外。她在茂物市近郊的戈塔帕利集中营见到了母亲、哥哥和妹妹,得知了父亲战死的消息。日本投降后,埃伦随家人返回荷兰。她当上了秘书,并结了婚,因为在日本“慰安所”经历,使她对男性怀有深深的厌恶感,并且她还被查出患有性病,所以她很快又离了婚。从此永不再婚。
六、“富士子”贝齐
贝齐与埃伦在同一个“慰安所”中被日本人蹂躏,是一同落难的同伴。她与父母和两个弟弟生活在万隆市,随后搬到了日惹市。战争爆发的时候,她正在苏门答腊上寄宿制高中。1942年6月,她父亲被日本兵抓进集中营。不久,其他的家人也被日本兵抓进了集中营。1944年初,贝齐和母亲被日军转移到蒙蒂兰集中营,两个弟弟被关到别的集中营。蒙蒂兰集中营人满为患,物资匮乏。她和母亲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每个人只有60厘米宽、2米长的空间。白天还要出去干重活。
和埃伦一样,同一天,1944年2月20日,贝齐也被日本军官挑选为“慰安妇”,随后被带到了三宝垄的“慰安所”。她也同样经历了被强迫签字的过程。她和埃伦被分到了同一个“慰安所”。她的房间布局和埃伦差不多,也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衣橱、一个洗脸台。“慰安所”老板给了贝齐一个日本名字“富士子”,意思是富士山的女儿。不过贝齐一直认为这个名字是“神圣的母亲”的意思。因为,她保护了一个年幼的女孩。日本人想要强奸这个女孩,她勇敢地站出来,与日本人大吵。不过她的斗争失败了,日本人还是当着她的面强奸了那个小女孩。
3月1日,“慰安所”开始接客了。一名日本军官来到贝齐的房间,她拼命抵抗,害怕得惨叫,但是日本军官还是强奸了她。不配合的女孩们都被送去了接待普通士兵的“慰安所”。日本兵威胁她们,如果再不配合,就杀掉她们的家人。于是剩下的女孩们都不敢反抗了。周日,“慰安所”的女孩们会被送去普通士兵的“慰安所”。贝齐感觉自己就是传送带上的商品,粗鲁的日本士兵在她身上川流不息,肮脏而野蛮。
贝齐在“慰安所”的日常生活是周一到周六晚上接待日本嫖客。一般日本军官如果傍晚到来,大都在她们房间里待上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如果嫖客来得晚,就会通宵蹂躏她们,甚至玩弄她们到第二天黎明。她们要定期接受身体检查,特别是性病检查。每当日本医生告她们,没有感染性病的时候,她们心中都有一个疑问,是这样吗?“慰安所”规定使用安全套,在房门上张贴着的用日语写的嫖客守则也明确规定这一点。但是贝齐始终不明白安全套是何物,因为她从来没有勇气看对方是不是使用了“那东西”。
两个月后,“慰安所”突然被查封了,贝齐也被转移到戈塔帕利集中营。她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母亲,母亲对她表示理解,并安慰她。随后她们又被转移到巴达维亚近郊的克拉马特集中营,贝齐在这里得了痢疾,差点死掉。好在战争结束得早,她得到及时治疗。父亲和一个弟弟在战争中丧生。战后,她们一家回到荷兰,定居在阿姆斯特丹。贝齐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丈夫,她向他吐露了一切,丈夫总是安慰她,关怀她。两个人组建了美满的家庭。
七、善良的“大姐”提奈卡
血色太阳之下充满罪恶,但是在作为罪恶渊薮的“慰安所”里又有温暖的阳光。荷兰“慰安妇”提奈卡就是马吉冷日军“慰安所”当中的一缕阳光,落难小姐妹们的好大姐。提奈卡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时,已经30多岁了。
她在战争爆发之前,住在苏门答腊。她嫁给了一位荷兰飞行员。很可惜,丈夫在一次飞行事故中去世了。为了谋生,她在当地的夜总会里工作。战争爆发后,她被关到了中爪哇的蒙蒂兰集中营,后被日军强征到马吉冷的日军“慰安所”。由于有过婚姻,由于工作关系,所以她对男女之事,比那些涉世未深的少女们更有经验。
她天性善良,力所能及地给予年轻的姐妹们一些帮助。在姐妹们遇到一些难伺候的日本军官和士兵时,她总是把这些日本军官和士兵领导自己的房间,由自己来应付,尽量让年轻的同伴减轻伤害。时间长了,一位日本军官爱上了她,并且跟她说过“我爱你”。这位日本军官是单相思。但是提奈卡说,幸好身边有这么一位珍惜她的人,她在“慰安所”的日子,才过得稍微轻松一些。“慰安所”里充满罪恶,一位荷兰女孩试图割腕自杀,幸好发现及时,捡回一条命。另外一个荷兰“慰安妇”,经不住日本兵的长期蹂躏,子宫感染而死。
后来,“慰安所”被查封了,她又被带回了蒙蒂兰集中营。有一天,日本兵让提奈卡等“慰安妇”去挖一个大洞,把她吓坏了。她以为日军因为战局恶化,要毁灭人证,准备将她们活埋。她尽量放慢挖掘的速度。最后好在活埋事件没有发生。
战后,她回到了荷兰,并在此结婚,但是“慰安所”的非人折磨,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经检查,她的子宫严重受损,无法怀孕。第二任丈夫没过多久也英年早逝了。她总是随身放着两任丈夫的照片。提奈卡生性开朗、坚强,充满爱心。她和玛格丽特成为了好朋友。她80多岁的时候,还在照顾住处附近的小猫,并给小鸟喂食。她喜欢钩织桌布,还送了一张给玛格丽特。但是玛格丽特知道,她只是将伤痛埋在自己心底。因为在接受采访谈及自己过去的悲惨经历时,玛格丽特能看出她心中的哀伤,一个开朗的老太太也变得表情严肃,满面哀伤。2006年,提奈卡在孤独和贫困中离开人世。
八、生下混血儿的莉娅
莉娅的故事在本书中是最凄惨的,她刚满13岁时被日军强迫充当“慰安妇”,白天要给日军南方航空队(原文如此,笔者注)的官兵做家务,晚上要遭受无休止的强奸。她被一位日本军官看上,成为这位日本军官的专享“慰安妇”,并生下了两个孩子。日本投降后,她获得解放,但是两个孩子却被日本军官偷偷带往日本,从此天各一方,终生未能相见,饱受骨肉分离之痛。玛格丽特动用日本皇室和荷兰王室的关系,帮她寻找,经过很长时间也未找到。莉娅带着遗憾离世。
莉娅1942年刚满13岁,原先一直在巴达维亚天主教会寄宿学校学习。日本占领印尼后,学校被迫关闭,莉娅的母亲被关押到纪地的集中营。而她和40多个女孩子被日军送到了托萨里日本南方航空队的营地。孩子们8人一组,被分到了航空队的各个营房,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熨烫衣服等家务活。很快,女孩们发现,“照顾日本官兵生活”不是日军把她们带来的主要目的。有一天,莉娅正在打扫走廊的时候,来了几名士兵。她突然被两个士兵抓住,拖进房间,扒光衣服。日本兵不顾她的哀求与反抗,轮奸了她。从那天起,她每天都会被强奸数次。其他女孩的命运也同样如此。
有一天,莉娅发现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月经了,而且乳房肿胀。日本军医检查后,她知道怀孕了。医生说必须堕胎。莉娅是天主教徒,认为堕胎是罪恶,但是日本军医还是强行给她堕胎。堕胎手术后,没几天,她又被派去打扫卫生,又开始了一天被数十名日本士兵强奸的悲惨生活。又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又再次怀孕——每天遭受几十个日本士兵的强奸,他们又不使用避孕套,怎么能不怀孕呢?莉娅哀求军医,不可思议地是,军医竟然同意她保留胎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日本兵不顾她有孕在身,依旧每天强奸她。1943年10月的某一天莉娅分娩了,两个日本兵给军医当助手。孩子刚生下来,这两个日本兵就把孩子杀害了,随随便便地把孩子的遗体抛在了屋子外面。莉娅悲痛欲绝,整日以泪洗面。
随后,莉娅被带到了位于谷侗咕萨里街的一所房子里,那里住了吉田和其他几位军官。吉田一开始对她挺好的,照顾她的饮食,让她好好休养。可是等到她身体恢复后,吉田每天都要在她身上发泄兽欲。如果她拒绝,吉田就要狠狠地打她。吉田除了让莉娅满足他的性欲外,还命令她洗衣服、打扫卫生。莉娅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的,在吉田这里,总比在原来的地方每天遭受几十次强奸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