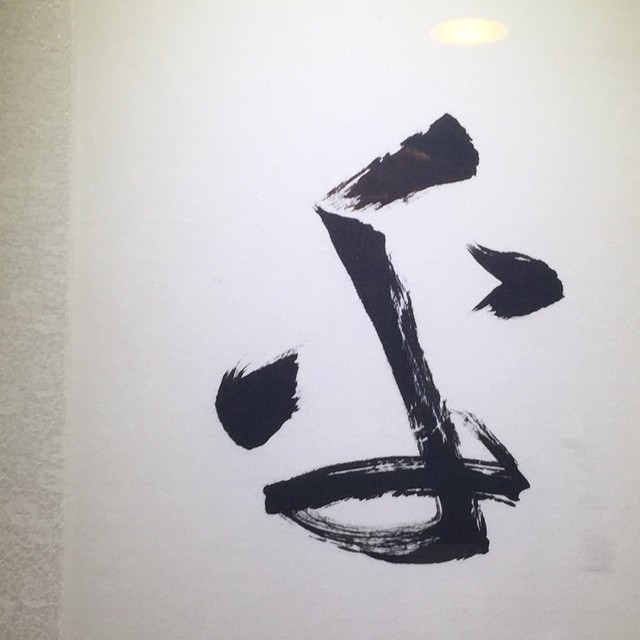![]()
“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美国选举选谁都差不多
刘瑜|文
引自《民主的细节》一书
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比如眼下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马萨诸塞州的州长选举。
今年11月7日是美国的选举日。没有总统选举,但有许多州要选州长,我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就是其中一个。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任助理司法部长。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副州长。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对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收入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高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美国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候选人的“本质”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不要削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坚决主张削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追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动力。”
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一共就那么点收入,还老是被挖去一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后来上网一查,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5.3%减到5%。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0.3%,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听到。
而帕崔克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再看另一个分歧。帕崔克主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州内学费”,赫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一个机会。”而赫利则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奖励非法行为”。
帕崔克主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出于“安全考虑”。赫利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其他一些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异”都显得鸡毛蒜皮。0.3%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去投票?
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民主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
但是我不这么看。“选谁都差不多”这个现象的发生,其实恰恰是两党激烈竞争的结果。正是因为两个政党在竞争中都要争取大量的“中间选民”,所以它们的政见日渐“趋中”,最后往往稳定在最大多数选民比较赞同的位置上。而一个上台的政党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恰恰是民主的含义。
![]()
早在1957年,政治学家Anthony Downs就总结出了两党制下“政党趋中化”的规律。许多后来的经验研究都证明了这个简洁然而意义重大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来说,“选谁都差不多”又是好事,因为它说明不同的政党都在使劲谄媚“多数老百姓”——这不正是“代表最广大人民之利益”吗?好比我喜欢吃面条,不喜欢吃三明治,那么一个党请我吃拉面,一个党请我吃刀削面,我当然“选谁都差不多”了。
投票率低,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恰恰说明他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既然就算不投票,也要么能吃到拉面,要么吃到刀削面,那投不投票也无所谓了。5%和5.3%的收入税差别,说实话,怎么看也就是个拉面和刀削面的区别而已。
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的表现。这个社会已经完成了对工人能不能组织工会、如何控制大公司垄断、公立中小学如何运营、妇女该不该投票、黑人能不能坐公车前排、言论自由是不是好事、人权是不是一个褒义词等等这些个“重大”问题的辩论。剩下的,至少就国内事务来说,基本都是小修小补的“鸡毛蒜皮”了。
如果一个国家这些最基本的共识都还没有形成,而我是那个国家的公民,我当然会举着选票跑到投票箱前了。毕竟,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选谁会非常不一样,我可不想被人按着脖子,吃下自己不爱吃的三明治。
如何看待美国大选中的川普现象
很多人认为,当今欧美政治已被民粹主义裹挟。
在美国,茶党的兴起、川普在共和党的胜出以及桑德斯旋风,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表现。在欧洲,无论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决定、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崛起、北欧诸国右翼政党的抬头,等等,都被视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征兆。
问题来了,如何区分“民粹政治”与“民主政治”?如果说民主的要旨是“人民意志至上”,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与“以民意为精粹”的民粹政治有何不同?
进一步而言,为什么“人民意志至上”是道德可欲的,而“以民意为精粹”就是有害的?难道“我同意的民意”就是民主政治,“我不同意的民意”就是民粹政治?一个趋势是:没有政治家自称是“民粹主义”者,但是几乎人人都在给异己者贴上民粹主义标签。因此,如果不对民粹政治和民主政治进行概念上的厘清,那么任何针对“民粹主义”的分析都可能成为语义含糊的风车之战。
本文试图在美国的背景下思考民粹主义。具体而言,第一,试图从概念上区分民主政治以及民粹政治,论述二者的相关性及差异性;第二,试图从长线历史的角度理解美国的民粹主义,以及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第三,从前面提及的分析框架及历史视野出发,理解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类型、程度、由来及后果。
民主政治与民粹政治
民主和民粹,具有高度重合性。它们都以“民意的合法性”为其话语核心,并以此反对缺乏民意基础的专制政治。问题在于,尽管高度重合,“民主”与“民粹”是否存在相异性?如果存在,如何界定?
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简单来说,就民主的理论传统而言,存在着两种对民主的理解,一种是多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自由式民主;而另一种是一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
![]()
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后者,那么,本质上“民主”必然走向“民粹”;而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前者,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区分民主与民粹的钥匙。
“多元式民主”相对“一元式民主”,这个分野从何说起?简言之,分野在于对“民意”的认识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是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整体性“人民意志”或“人民利益”,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民意”?选举,作为一种民主技术,是用以发现“那个”人民意志并为其道德合法性进行论证,还仅仅是一种决策的效率装置、“多数民意”无论技术上或道德上都不应取代“多元民意”?
“多元式民主”秉承汉密尔顿—熊彼特—哈耶克的传统,认为“民意”是多元的,因而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意见)都应有表达渠道。他们恐惧“多数暴政”,认为应以自由制度安排(财产权、市场自由、言论自由、少数权利等)约束稀释多数偏好——事实上根据Riker这样的社会选择理论家,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并能通过选举发现的“多数意志”都大可质疑,遑论以其为决策的依据。
而“一元式民主”则以卢梭—新左派为主线,倾向于将民意本身视为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源泉,解除对这一意志的束缚。尽管卢梭的概念是“公意”而非“众意”,但是假定民意是一个单数形式(general will,而非general wills)并进而假定这个意志客观存在,本身就蕴含了极权政治的种子。
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多元式民主注重权力制衡与分散——多数与少数、精英与大众、中央与地方、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相互制衡并共享权力。这种理念下,其民主制度设计必然为“多数意志”(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意志的话)设定了“半径”——半径之外,通过选举发现的“多数意志”不能随意占领。权力分立、间接选举、非民选权力机构的存留、联邦制、游说组织、智库、市场的政治力量、财产保护等制度安排,便成为抵消“多数统治”的一些缓冲机制。
相对而言,一元式民主倾向于一种可被称为“选举霸权”式的制度安排,选举产生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收编”立法和司法部门,被“拧成一股绳”的权力又进一步吸纳公民社会、媒体、企业与市场,最终“多数民意”通过选举的胜利得以统领整个社会。
很大程度上,当代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普京的俄罗斯或者埃尔多安的土耳其,都是这种“一元式民主”的代表。与威权统治不同,这些国家存在着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但是又与自由式民主不同,其当选政治家往往大幅剪除整个社会的多元性,试图将所有权力机构乃至公民社会“统一”到一种意志之下,而其胜选的事实亦使其“赢者通吃”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的道义合法性。
对两种民主做出区分之后,民主和民粹之间的区分就相对清晰。简言之,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一元式”的,是“选举界定民意,民意统领一切”,那么民主和民粹就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只有当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自由式的、多元式的,我们才能找到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民主的多元性程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民主和民粹的区分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讨论自由式民主与民粹主义的界限。
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天然导向社会分层。因此,区分(自由式)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一个标志是对精英主义的容纳程度。自由式民主容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精英主义,而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在此,精英主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智识的。
▍
第一,经济上而言
,(自由式)民主容纳相当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并认为财产所有权的安全是政治权利的基本保障;而在民粹政治中,经济自由常常屈从于其他政治价值
——对于左翼民粹主义,“其他”价值往往与“平等”相联系,而对右翼民粹主义,“其他”价值则与“身份认同”相联系。
▍
第二,政治上而言
,民主政治也比民粹政治更能包容政治精英主义。尽管自由式民主作为民主,必然要求
政治权利的平等
,但它并不保障、亦不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