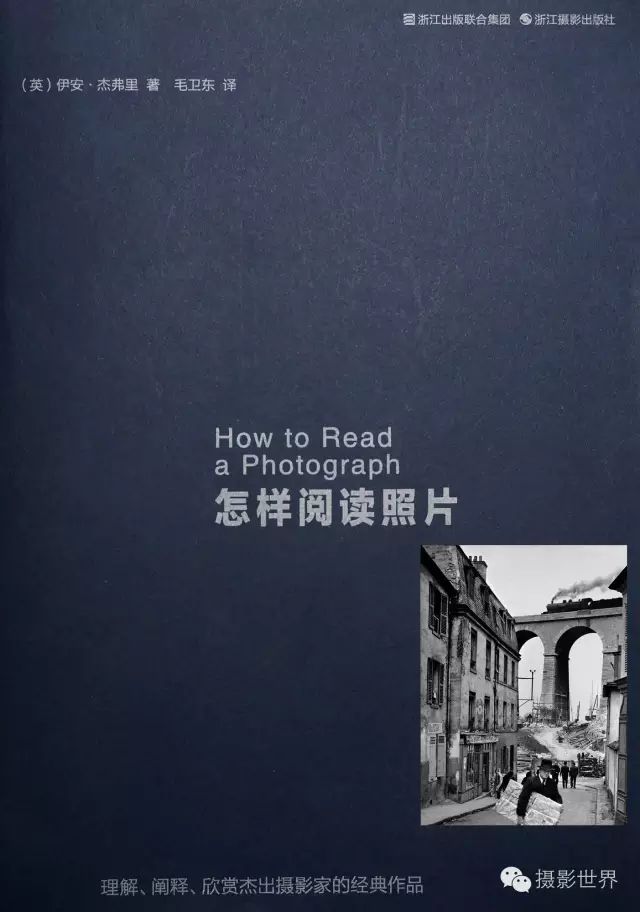点击上图查看《当代》2025年1期目录
林檎小说二题《徙木史》《夜巡》发表于《当代》2025年1期
相关阅读:
王增宝《树与人:生存于明暗之间——读林檎的〈夜巡〉与〈徙木史〉》丨特约评论
——林檎小说印象
文|董晓可
如果必须用一个词语来概述我对林檎小说的阅读感受,那便是“少年感”。读他的小说,你会不由生发出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王二的自豪,“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抑或巴别尔《我的第一笔稿费》里的忧郁,“住在梯弗里斯而又遇上春天,出娘胎已二十年却又没有情人”。是的,这就是少年意气,不论是目空一切还是孤独痛苦,都带着让人羡慕的青年人才会有的激流与纯粹。他身上有一种久违的冲撞力量,这种力量不见得能带来所谓成熟作家深潭照物的震撼,却必然带来长河激浪的自信与颠覆意志。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作家林檎自有其“吴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便是他“从菜市场、公交站、小区保安亭里发掘出的‘伟大传奇’”。依此出发,我冒昧揣测,林檎所钟情的理想作品,应该是来自狄更斯、欧亨利、奈保尔、卡佛等作家所开创的书写日常琐隙间社会危机与人性光亮的现代世俗文本。而在此之外,他那干脆利落的运笔手法,又让人感到一种来自90后的打破原有秩序与捍卫道德律令的“整顿职场”的强劲力量。
林檎来自巴蜀地区,巴蜀多才俊,是不争的事实。阅读林檎,会让我直接想到1980年代中期巴蜀地区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们,想到莽汉主义的粗粝豪放,想到“四川五君”(欧阳江河、柏桦、翟永明、钟鸣、张枣)的各怀奇技。而这其中,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是他接近同乡(二人皆来自川渝)欧阳江河的干脆利落。阅读过程中,我甚至无数次想到欧阳江河的代表诗歌《手枪》来:“手枪可以拆开/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一件是手,一件是枪/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手涂黑可以成为另一个党……”在我看来,林檎便具备这种艺术领域中自由“拆卸”及“组装”手枪的禀赋。
这种禀赋,首先来自于他的艺术敏感性。当然,这种敏感性一方面源于缪斯女生的天然赠与,另一方面或许更多来自日复一日浮躁乏味却急需耐心的艺术锻造。在文学的跋涉征途上,林檎是有故事的人。正是出于真诚的热爱,那些默默无闻的日子里,承载了他搭建自我艺术格式塔的最美时光。
在林檎经历了近百个小说的不断调适后,展现出了较好的艺术禀赋。在我看来,这至少表现在三个互为犄角的维度上。其一,极强的短篇意识。在小说创作上,有这样一句行话:“给我三个好的故事,给你一个好的中篇。”这句话,意在强调小说中故事点的重要性,这有些类似于接受美学家姚斯所倡导的或隐或显的期待视野。可以说,在林檎的几乎所有近作中,你很难找到“和稀泥”式的艺术构筑。在每一个不足万字的小短篇中,他都会明确地植入两到三个故事点,并通过逐渐强化的方式,层层递进地生成自己的“重拳”,带给你痛爱交织的艺术冲击力。其二,他还有着独属于自己的“看世界”方法。在此层面,批评家李蔚超独具慧眼,并将其概括为“城市微观史”。而林檎的“城市微观史”其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在我看来,突出之处在于对凡俗大地上未被社会秩序“格式化”的一个个铮铮灵魂的书写。事实上,林檎作品中的人物太有个性了,这种个性渗透于言语与行动体系的方方面面。比如从言语来看,在《菜鲟》中,当莫晓贝收到了爷爷送来的菜鲟(公蟹),不由疑惑地问道:“小螃蟹班上没有女同学吗?”在《尺蠖》中,面对晕倒的母亲,乔家姐妹有了如是对话:“赶紧回去看看你妈,乔安说。你妈,乔麦反问,难道不是你妈?”而在《萌牙》中,面对生出的智齿,30岁的老师和自己的学生一起掩埋,并祈祷牙仙子让其发芽。在这些鲜活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人物构筑。这些少年的天真与智性,会给我们带来别一种来自新生代际的、感同身受的泯然一笑抑或情感认同。
除此之外,林檎更厉害的“城市微观史”的“伟大传奇”书写的第三特点,集中表现在他那爆发野性的解构能力。关于这点,我将重点聚焦于《当代》第一期的两部作品:《徙木史》和《夜巡》。
二、《徙木史》PLUS《夜巡》:如何对现实正面强攻
当然,这里的PLUS,不惟表征“我和你”式的根脉相连,还征兆着一种《大佛普拉斯》一样副文本式的无奈与解构。因为早在19世纪,天才诗人兰波就用青春敏感的心灵吟唱出了“生活在别处”的真谛。在经历了大工业浪潮后的今天,我们无疑处在席勒美学视域中“感伤的诗”的现代景观社会。在此社会,你已经很难触及生活的本质,甚至会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仪式化。你更不可能触及历史的本质,而只能在娱乐喧嚣中感受到一场场草台班子的演绎。对此世界,林檎显然有清醒认知。如果说在刚刚出道时,他的部分作品更多体现在戏谑与反诘兼具的迂回式个体“黑色幽默”。那么,在《徙木史》与《夜巡》两部作品中,他显然怀有试图处理宏大主题与社会隐疾的抱负。
在《徙木史》中,那棵银杏树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变迁,从美国飞机坠落被唤醒,到历经土改、拆迁等一系列事件,其命运与莫家以及江城紧密交织。它本是自然的一部分,却因人类社会的发展,被迫不断迁徙。在面对莫识途的强拆时,老莫奋起反抗,像一头捍卫领地的野兽,与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拆迁队展开搏斗。曾经亲密的父子关系,因利益冲突变得剑拔弩张,现代社会中金钱与权力的强大力量,让人们逐渐迷失自我,背离了最基本的情感和道德准则。而最后那棵被移植城市的老树的逃离,更表明了一种反抗规训的决绝。
而在《夜巡》中,保安队长莫识途看似风光,实则深陷生活的泥沼。他利用职务之便,出租闲置车位谋取私利,还拉着“我”一起进行所谓的“夜巡”,发现“违规行为”进而获取利益。在此过程中,无数偷情与背叛,直指失落了道德的世道人心。而当他与儿子的矛盾爆发,被儿子的行为伤透心后,变得像个落魄的叫花子,在车库里被人羞辱。他的遭遇,反映出底层众生在面对复杂社会面前的迷惘与无奈。
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小说中作为“楔子”的独特性。无论是违背自然的树木迁徙,还是夜晚巡逻的选取,均在暗示一种“反常理”的悖谬。这种树的反抗与人的扭曲,本质而言均以一种边缘化的话语,直抵林檎这一90后所理解的现代江城世界的疯狂与荒谬。在此,江城已然失去了莫言、苏童、阎连科等老一辈作家那或多或少富有故乡情节的缅怀,而映射出丧失了安全感的少年们的内心惊悸,更像是卡夫卡笔下那让人捉摸不透的现代城堡。如果说,林檎这种富有野性的现代爆破,意在营造一种被遮蔽、压制声音的狂欢,那么此种狂欢的关键性在于其提供了一种可供狂欢的场域空间,以及主角们以何种姿态登场,并在对话与碰撞、融合与分离之间寄予其话语表达。
这,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有效对话现实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在诸多前辈作家那里有着个体性的实践。而就林檎目前所发表的有限作品来看,他尚未跃出社会问题小说的界限,这也体现了他的志趣所在。那便是,在“江城”世界中,实现自己“闪烁出些许契诃夫般的悲悯和隐忍”(“伏笔计划”颁奖词)的小人物书写。在此层面,在其富有野性的江城艺术构筑中,主要还是依托于富有辨识度的人物上。这些人物,通过个性化的执拗动作,来表达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或者“是”。
首先是“不”。在当下文本中,我们见惯了太多“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凝滞含混修辞策略。而在林檎的叙事中,有着可贵的棱角分明的个人主体。林檎在人物塑造上,有着对于“老莫”这一形象近乎疯狂的痴迷。在诸多文本中,其主人公皆为老莫。这一看似取巧的偷懒,实则别具匠心。一方面,“老莫”之统一称谓打破了具体名性的有限性,进而通向了卡夫卡“K先生”一样的符号化,直指能治系统里芸芸众生的每个具体所指,进而实现了为当下时代画像的功能性。更重要的是,“老莫”之“莫”,本身便自带强烈说“不”的功能,这个“莫”有些类似于鲁迅笔下的“未庄”,抑或格非笔下的“乌有先生”,体现着林檎向一切社会隐疾说“不”的勇气与智慧。在《徙木史》与《夜巡》中,林檎便是以类似于《三枪拍案惊奇》一般的现实扭曲、疯狂演绎,解构了一切虚假圣神与正义侵害。
其次是“是”。林檎的作品中老莫往往有一个搭档,那便是“我”。此处的“我”并非诸多我们习以为常小说中的叙述功能承载体,而是有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这种感情隐含着秩序化社会下,无数个被忽略个体的笑与眼泪,疼痛与幸福的世俗尊严与价值肯定。在此,“我”与“老莫”互为依托,往往由“我”来完成“老莫”未完成的话语夙愿,尽管此种话语中亦往往只能呈现为一种心灵仪式。如果不局限于《徙木史》与《夜巡》两个文本,我们会发现在林檎近乎所有的作品中,均隐含着这样一个并非“老莫之他者”的、作为情感共同体的不同样式的“我”。这些“我”,有时是我们已然提到的作为老莫伙伴的男孩子,有时是作为温暖、恬静姊妹的乔麦与乔安(如《尺蠖》《药师变》《安宁》等),有时是富有童心、童趣的孩童群体(如《萌牙》《鲸鱼马戏团》)。而所有的这些“我”与“老莫”相伴而生,以重拳出击的凌厉与力度,表达了一个90后作者,对于现代城市文明与秩序之于鲜活灵肉的桎梏,以及“船在海上,马在山中”自然属性的决绝返归姿态。
余论:从“分成两半的子爵”到“树上的男爵”:天空与地面之辩
综上,以《徙木史》与《夜巡》为出发点,我们能感受到林檎这一理工男聚焦现代城市及其受困群体的能力。但我想,他是否还有高于地面的发展空间呢?我愿意以卡尔维诺的两部小说为例,来予以浅谈。在我看来,林檎当前“江城世界”众生相的构筑,更像是其笔下“分成两半的子爵”的聚焦。在他的小说中,似乎永远在言说,他分成了两半,为什么分成了两半?有没有可能再合为一体成为健全的子爵呢?但似乎“树上的男爵”是缺失抑或部分缺失的。事实上,树上的男爵尽管在树上,却无时无刻不在盯着地面发生的一切。而另一方面来看,男爵之所以具备盯着地面的超凡能力,是因其深处高高的树上。这,本质而言涉及到一个天空与地面之辩。如果你永远仅仅盯着地面,你会看到无数的子爵,却不见得看得到男爵。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永远是飞鸟掠过塔尖却凝视大地的存在。这就好似《饥饿艺术家》煞尾处的描述:“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在此看似世俗化的描述中,蕴含了高于地面的神祇的艺术力量。当下的林檎似乎正处于疯狂迷恋“分成两半的子爵”而尚未真正仰望“树上的男爵”的时段,期待着有一天,他将现在的富矿用尽而不得不转型时,会探索走向更为阔大的艺术境界。
最后,我想以一种马尔克斯式的表达来结束我的言说:多年以后,但愿读者还能记得,2025年开春,有一个叫林檎的少年横空出世,从此走向了文学的远方风景。
这,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祝福!
本刊特约评论

董晓可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在《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评论作品50余万字,荣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有评论集《盖茨比的鞋子》、学术专著《80年代文学的话语重建与转型研究》。
稿件初审:周倩羽(实习)
稿件复审:徐晨亮
稿件终审:赵萍

点击上图查看新刊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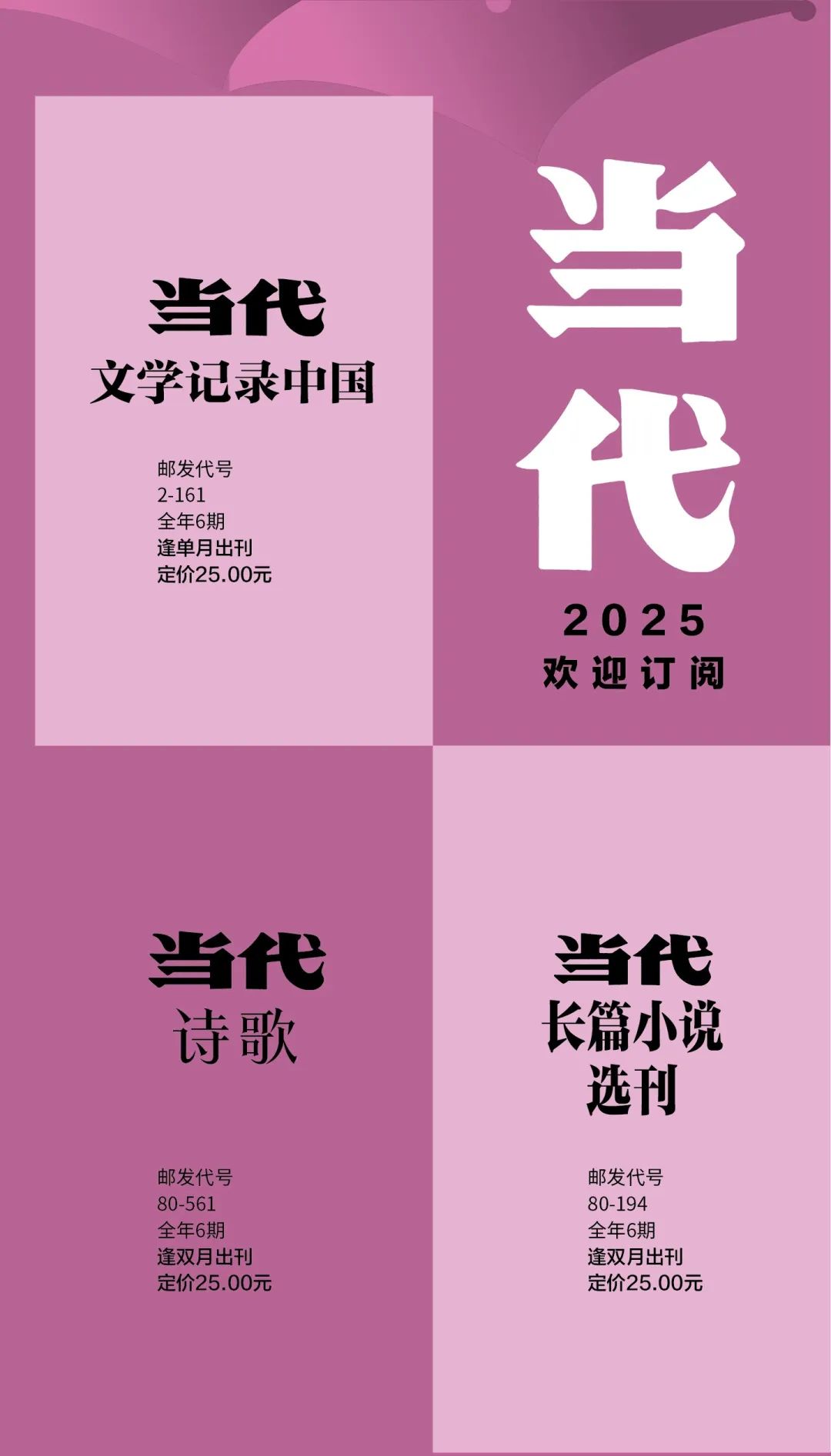
订阅《当代》:
2.《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邮发代号/8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