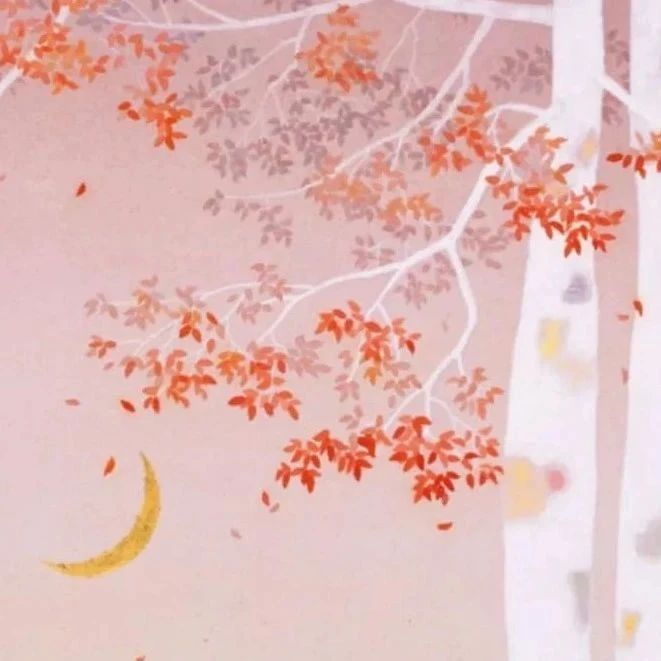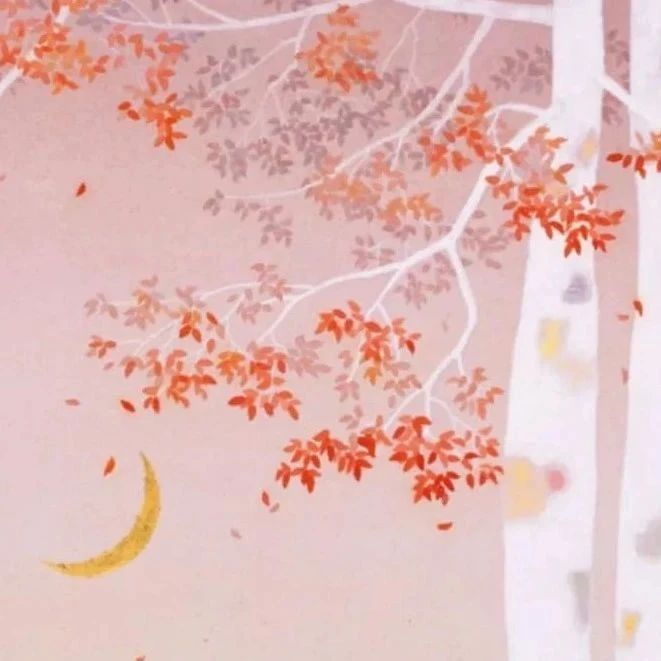卡夫卡与《变形记》
这段开头选自于一个短篇故事—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看起来卡夫卡似乎并不太关心我们是否读到这句或者其他任何他笔下的文字。卡夫卡还嘱咐他的朋友麦柯斯·布洛德在他死后烧掉自己的手稿,他宁愿这些文字不被人阅读。卡夫卡在40岁时就因肺结核而英年早逝。所幸的是布洛德违背了他好友的遗愿。于是这些得以保存下来的文字代替卡夫卡本人向我们诉说着卡夫卡的故事。
对卡夫卡来说,人类的处境远非悲痛和沮丧二词可以形容。
他认为人类处于一种荒谬的窘境,而全人类都是上帝在“糟糕的一天”中的产物。于是,试图寻找生命的意义本身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可正是这样自相矛盾的无意义状态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阅读卡夫卡的小说,诸如《审判》(The Trial,一种法律程序,可是整个过程却毫无结果)和《变形记》。生活本身的毫无意义让我们可以任意地赋予这些作品意义。
例如,评论家们将格里高·萨姆莎“变形”为蟑螂的行为看作一种反犹太主义的隐喻,也是对消灭“这一害虫似的民族”的罪行的冷酷预测。(卡夫卡便是犹太人,且比阿道夫·希特勒稍年长。)作家常常比一般人更具前瞻性。
此外,评论家们同样将1915年出版的《变形记》看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奥匈帝国瓦解的预测。卡夫卡和他的同胞们身处的位于布拉格中心的波西米亚正是这一辽阔帝国的组成部分。人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国民身份土崩瓦解,不复存在。而那些有弗洛伊德倾向的人们则将《变形记》看作卡夫卡与其粗鲁的商人父亲之间病态关系的体现。无论何时卡夫卡紧张地将自己的作品递给父亲,他的父亲总会看也不看就退回。这是位鄙夷自己儿子的父亲。
不过,任何读者测度的所谓“意义”都会崩塌,因为在卡夫卡的宇宙中,没有潜在的意义以作支撑。然而,荒谬主义文学尚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坚持文学也可以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毫无意义。在完成这一任务上,卡夫卡的主要追随者塞缪尔·贝克特表现甚佳。他充分体现了“作者表达无径,表达无源,表达无欲,而仅有表达之责”。
秉持着这样的观点,让我来欣赏一下卡夫卡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小说《城堡》(The Castle)的开篇:
K在深夜抵达。整个村庄被厚厚的积雪覆盖。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丝毫看不见城堡山的影子。即便是城堡所发出的最微弱的灯光也看不见。K在这座连接主路和村庄的木桥上伫立良久,仰望着这场表面的空洞。
所有的事情都战栗着谜一样的色彩。“K”是一个代号,但不是一个名字(指的是卡夫卡吗?)。这是个薄暮,介于白昼与黑夜间的空寂时光。此时,K站在一座桥上,仿若悬浮在村庄与外界世界之间。城堡被浓雾、黑暗和积雪所笼罩。位于K面前的仅仅是“空洞”吗?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K来自何方又缘何而来。而他永远也不会抵达城堡,因为他甚至不能确定那里有一座城堡。但是,他就是要去往那里。
卡夫卡以德语写作,且终生都文风晦涩。在其孱弱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卡夫卡在其家乡布拉格的一间政府保险办公室工作。(据说,卡夫卡在这一工作中表现优异。)他研读的是法律,可是由于职业关系,成了一名官僚。他与女性和家人之间的关系,让他在精神上遭受了极度的痛苦。他在才华尚未完全展现之时便英年早逝。痛失英才后的数十年间,仅有寥寥数人在德语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在卡夫卡去世多年后,直至20世纪30年代,其作品的英语译本(首部被翻译的作品是《城堡》)才开始出现。这些作品激励了一些作家,同时也困惑了一批读者。卡夫卡的影响力被再次复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股主要文学力量。而这一切发生的地点不是在布拉格,亦不是在伦敦或者纽约,而是在巴黎。
在20世纪40年代法国存在主义者的无神宇宙中,卡夫卡被塑造成了一种父权和统治者的形象。正是他们的这种哲学理念触发了20世纪60年代的“卡夫卡革命”。这一时期,人们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奥威尔式具有严苛政治控制的,就是卡夫卡式高度压抑的,要么就是兼有这两种社会的特点。卡夫卡说,他不再令人迷惑,因为他的时代俨然已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