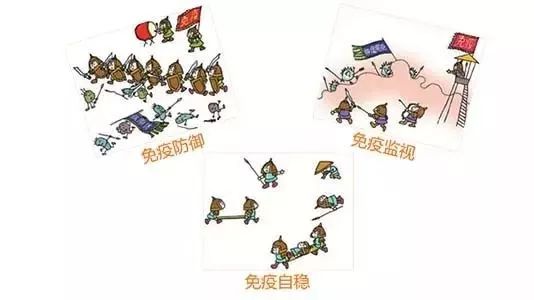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有关东风
-41
洲际弹道导弹又传来了新消息。一方面是一些东风
-41
洲际导弹所特有的
8
轴大型
TEL
车在中国北方进行寒带地区试车的新照片的公开,另一方面则是有消息称,中国在今年一月刚刚进行了一次东风
-41
的分导多弹头系统的测试。加上外媒对于中国即将部署东风
-41
导弹的猜测,这种人们关注了许久的武器似乎马上到了呼之欲出的时候。

如果不深究具体的技术细节而纯粹只是按照编号来看的话,东风-41其实是中国研制的第一款固体燃料弹道导弹。当然此东风
-41
非彼东风
-41
。
上世纪
50
年代末,我国在几乎没有苏联方面的援助指导的情况下,开始自行研制固体火箭燃料和固体火箭发动机相关技术,并在不久后初步研制成了小直径的固体火箭发动机,随后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专门研制固体火箭燃料和固体火箭发动机的部门开始研制一系列可用于弹道导弹和远程火箭用的大直径固体火箭发动机,并计划以此为基础研制一款射程几十公里的战术火箭装备炮兵部队。这一型战术火箭最初的名称,便计划定为“东风
-41
”。
当然当时的所谓
“
41
”并不像后来研制的弹道导弹一样有着诸如标识导弹级数等其他内涵,而仅仅是和同时期的比如“红旗
-41
”一样代表一系列新型号的开始。
不过这型
“东风
-41
”并没有被实际制造出来,该型导弹后来被更名为“东风
-61
”,然而没等导弹的原型被制造出来,相关的技术力量就被转移到研制潜射弹道导弹,也就是后来的“巨浪
1
型”上来,而最初的“东风
-41
”则悄然下马,成为中国早期弹道导弹研制中一段短暂的记忆。
“东风
-41
”第二次上马则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当时我国基本完成了第一代的东风
3
、
4
、
5
型液体战略弹道导弹和巨浪
1
型潜射弹道导弹的研制,开始下一代弹道导弹的研制,这一时期虽然不像”文 革“初期那样还有诸如东风
6
号环球导弹这样不切实际的冒进项目,但实际研制的项目依然不少,除了技术难度相对不大,由巨浪
1
型导弹上陆改进而来的“东风
-21
”导弹外,还包括液体远程弹道导弹“东风
-22
”、固体中远程弹道导弹“东风
-23
”、潜射固体远程弹道导弹“巨浪
2
”以及洲际固体弹道导弹“东风
-41
”。
这些项目中,有些项目比如东风
-22
和巨浪
2
型在性能指标上相似,但一个是液体弹一个是固体弹;有些项目比如东风
-23
和东风
-41
则还处在预研阶段。为了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取得技术突破,在
80
年代中期的调整中,东风
-22
这样反应速度不佳的液体导弹和东风
-23
这样进展较少的导弹宣告下马,巨浪
-2
这样符合弹道导弹发展方向的导弹则拓展为东风
-31
和巨浪
-2
两种,分别满足陆基发射和潜射两种不同的使用环境。
而当时的东风
-41
也处于预研阶段,并未投入全面研制。从我国后来研制东风
-31
时遇到的困难看,似乎这样做还比较明智,不过随着时间到了新世纪,东风
-41
的必要性却是越来越凸显了。

在
2016
年,五个常任理事国全都进行了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试射,中美还进行了反导实验,连印度都不甘寂寞试射了烈火
5
,核武器的升级改进计划几乎家家都有。
长期以来,我国的战略核威慑主要依靠的是不断改进的东风
-5
系列洲际弹道导弹,借助各种长征
2
号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该型导弹在本世纪初先后完成了增程型东风
-5A
和多弹头分导型的东风
-5B
,在射程和威力上满足了对北美大陆实施战略核打击的基本需求。
之所以说是
“基本需求”,是因为这种打击能力虽然存在,但是一来东风
-5
不具备机动发射能力,主要依靠地下发射井进行战备值班,但这类发射井因为数量有限且防护水平无法无限度加强,因此在战争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堪忧;二来东风
-5
作为一款上世纪
70
年代研制的导弹,其性能潜力早已发掘殆尽,面对新一代的导弹防御系统,其突防水平也面临挑战,而东风
-31
及其改进型东风
-31A
,甚至传闻中具备多弹头分导的东风
-31B
,受限于射程,投掷量和发射车机动能力,都无法达到理想的水平(俄罗斯的白杨
-M
战略导弹也有类似的不足,不过俄罗斯的地理位置以及其较为先进的发射车相对掩盖了这一不足)。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要强调这几个特点,尤其是
TEL
车的装备,是提高弹道导弹生存能力的关键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除了东风
-41
的
TEL
车,我军还同时推进多款
7
轴
TEL
车的研制,用于东风
-41
以下级别的战略导弹的搭配。
对于现代精确制导武器而言,单纯的
“硬”的防御思路已经不够用了,“跑起来”的战略导弹才有更好的威慑效果
至于所谓发射车测试与部署地点的关系,笔者倒以为并非是八竿子打不着。毕竟这种洲际导弹发射车的主要任务模式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在荒原上驰骋,而是在接到指令后,从防御良好的掩蔽阵地里驶出,全速
“冲刺”到预设的发射阵地后尽快发射弹道导弹,因此发射车测试地区的交通条件和地貌特征往往与实际部署地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其中的联系,不是仅仅从射程上计算就能说明的。
当然,从充分利用既有弹道导弹发射与后勤设施的角度考虑,在研制和部署东风
-41
固体弹道导弹的同时,利用这些年我国在液体运载火箭技术上的成功,从现有运载火箭型号基础上发展一型运载能力比东风
-41
更大的洲际弹道导弹,部署于现有的发射井内,也不失为增强战略核威慑力量,实现我国战略弹道导弹部队更新换代的合适策略。
冷战时期,在美苏冷战核武器军备竞赛的
“恐怖平衡”之下,中国得以凭借“最低限度核威慑”以较少的核武器维持本国的战略地位。而随着苏东剧变之后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的不断凋零,特别是
SS-18
“撒旦”战略导弹面临老化退役而接替的导弹还未开始装备,即将带来俄罗斯战略核武库不可避免的萎缩,冷战结束初年俄罗斯凭着核武库这一最后防线与西方对抗的景象也将难以继续;面对我国战略机遇期最后的时间窗口,尽快加强和扩充我国的战略核武器力量,才能让包括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