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律师行业要建政委了,不妄议现实,只说说历史

罗伯特•巴特莱特:《中世纪审判》,徐昕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女巫审判与
神判的复发
因其如此难以证明,故在此种指控中,承认冷水神判作为一种证明方式。
巫术犯罪是难以证明的。不仅由于很多女巫活动发生在夜间,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种观念认为这种犯罪无法看见。患病的邻居、变质的牛奶或秘密聚会不过是真正犯罪
(
作为一个女巫
)
的蛛丝马迹。所争议的正是这种神秘状况的证明。我们业已了解到神明裁判尤其被视为适用于此类令人费解或晦涩模糊的案件,因此,发现相对较早地提到神判运用于巫术和魔法的指控并不令人惊异。与诸如夜间谋杀或性纯洁之类难以查明的案件一道,巫术和魔法的难题被诉诸上帝的裁决,而非交由人类审判。
加洛林王朝和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立法皆规定神明裁判适用于巫术
[
案件
]
。
12
世纪挪威的《博尔加廷法》
(
Borgarthing Law
)
规定:
倘若在任何人的床上或枕头中发现巫术道具,人的毛发、剪下的指甲、青蛙腿或其他用于妖术之物品,则主教的官员可起诉三位被疑使用巫术的女子,她们须对指控进行答辩。她们须以热铁洗刷嫌疑。若其在火审后是洁净的,则可从指控中解脱出来;若其在神判后伤口不洁,则被视作负有责任。
与此同时,在欧洲其他地域,西班牙的《昆卡法典》也规定了热铁神判适用于巫术和魔法的指控。
13
世纪神判的消亡对巫术审判具有直接影响。既然神判在教会法院中不再是一种法定证明形式,则与在其他疑难案件中一样,诉诸刑讯成为在这些疑难案件中寻求确定性的自然手段。在
15
、
16
和
17
世纪大规模的猎巫运动中,刑讯的中心作用显而易见。权威人士常常感到,巫术是这样一种甚至连刑讯适用的通常限制皆可取消的特殊类型犯罪。
“
法官可以反复刑讯
”
,
17
世纪早期一个法国法院宣称,
“
因为这种巫术犯罪是如此不同寻常、如此隐蔽和如此秘密
”
。
班贝格的市长约翰内斯·朱尼厄斯
(Johannes Junius)
于
1628
年写下的著名信函,显示了刑讯在巫士的制造中是何等必不可少。朱尼厄斯被控施行巫术,他受到刑讯,最终招供。由于痛楚,他以颤抖之手写完此信,并偷偷从监狱送给女儿,信的开头是:
“
无数个美好的夜晚,献给心爱的女儿维朗妮卡
(Veronica)
。无辜的我蒙冤入狱,无辜的我遭受拷打,无辜的我必会死去。因为凡进到巫士狱之人必定会成为巫士,否则会被刑讯至神志不清而胡编乱造
……”
。
有人已实话实说,
“
无刑讯之处,几无巫术
”
。

不过,故事也有另一面。尽管认为神判已被刑讯替代的说法是真实的,但也残存着一种将巫术与神判联系起来的趋向,一波宛如回头浪式的观点,即将神判视作适用于此类特殊犯罪的正当的证明形式。一个特殊的说明性例证出现于猎巫者的经典指南《锄恶利器》中。该书作者多明我会修士克赖默尔
(Krämer)
和斯潘格
(Sprenger)
讨论了热铁神判的正当性:
“
……女巫能在魔鬼的帮助下无伤害地承受这种神明裁判,这并非不可思议……因此,较之其他罪犯,甚至应更少允许女巫适用这种神明裁判,因为她们与魔鬼异常亲密;而正是由于她们诉诸此种审判之事实,她们应认定为女巫嫌疑人。
”
在这一不同寻常而别出心裁的主张之后,他们引述了康斯坦茨
(Constance)
主教区内最近的一宗案件作为例证——法官菲斯腾堡
(Fürstenberg)
伯爵
“
年少且缺乏经验
”
,允许一位女巫嫌疑人诉诸热铁神判:
“
而她随后手持炽热的烙铁不仅跨出规定的三步,而且跨了六步,还提出手持热铁走出更远。其后,尽管他们应将此视作她是女巫的明显证据……但她还是被释放了
”
。
他们提到的这宗案件,
1485
年发生在黑森林
*
的罗滕巴赫
(Rothenbach)
,文献资料亦可证实这点。
有关巫术与神判的持久联系,此处就有明显的证据:炽热的烙铁在
15
世纪后期的德国,正如在
10
世纪的英格兰和
12
世纪的挪威与西班牙一样,至少对于某些人而言,似乎是揭露女巫身份的任务之恰当工具。但另一方面,有经验的宗教裁判所法官明确拒绝将神判作为一种证明形式,因为它无法充分地加以控制。当然,神判以不受控制为目的,将问题从人类手中卸除,并交于上帝之手。克赖默尔和斯潘格担心魔鬼而非上帝将更可能在此刻施加控制,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宁可自行保留支配权。他们拥有自己的应对工具
——
纠问和刑讯,并因而乐于在猎巫运动中拒绝神判的使用。
然而,尽管《锄恶利器》中提出了异议,神明裁判最显著的残存仍然是在巫术案件中,因为在近代早期如此普遍的
“
水验
”
女巫之习惯,无疑是冷水神判一种晚近的复发。女巫在中世纪被施以水验
(1090
年代的巴伐利亚记载了一个例证
)
,并且这种证明形式在
16
和
17
世纪的运用本质上不足为奇。不过,至于近代早期水验的泛滥是否最好视作一种残余抑或一种复兴,仍然存有疑问,因为中世纪晚期适用于女巫的常规神判形式为热铁,而非冷水。另一方面,
16
世纪水验女巫恰好出现在神明裁判存续时间最长的那些地区。但无论它是残余还是复兴,这便是神明裁判继续濒于世人记忆中的形式。
1560
年代似乎是水验女巫变得普遍到足以引人关注的十年。克莱沃
-
尤利希
(Cleves-Jülich)
公爵的医生约翰·魏尔,在其
1563
年的《论妖术》中写道,
“
当被指控的女巫们手脚被捆、投入水中时,她们从不下沉,而是漂浮于水面,许多辖区内的治安法官和警察并不将此事实视为不可靠的证据,而是当作确凿的证据
”
。
这似乎是
16
世纪最早提到该习惯。另一位作者在
1584
年的著作中认为水验女巫是
“
一种新习惯
”(
newen gebrauch
)
,并特别将它与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
联系起来。
这样的联系相当到位。该习惯从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向外传播。至
1580
年代中期,女巫在法国被施以水验,
法国的案件在整个
17
世纪一再出现,且总是发生在诸如勃艮第、香巴尼和皮卡第等东北地区,即“边境”
(
vers la frontière
)
地区。在英格兰,记载的第一起水验案件发生于
1590
年,
而
1590
年代中期西属尼德兰和联合省对该习惯的谴责则显示了它在这些地域内使用。
意大利、西班牙及法国南部和西部地区似乎未受影响。
至
1600
年,女巫们因此在欧洲许多地区受制于这种神明裁判形式。该习惯贯穿于整个
17
世纪,在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
18
世纪。例如,在殖民地弗吉尼亚,这种神判晚至
1706
年还在审判中使用,
而在此一代人以后,匈牙利还存在着官方的水验。
然而,尽管许多女巫在这一时期被施以水验,该习惯始终沉浸于上级权威人士的学术非难和反对的氛围中。
尽管有少数博学者的拥护,就像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他写道,
“
上帝安排了女巫极不虔敬的超自然征兆,即水会拒绝将其拥入怀抱
”
,
但学者们的共识还是反对水验女巫。极为不同的思想家们在该问题上有着惊人的一致。耶稣会修士和清教徒牧师,持怀疑态度的医生和法学家,猎巫者和不信巫术之人,皆认为这种神判是
“
不可靠的证据
”
。他们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其谴责却完全一致。某些人
(
如约翰·魏尔医生
)
认为,嫌疑者可能由于自然原因而漂浮。魏尔在此触及对神明裁判的一种纯粹的唯物主义批判,这样一种方式,不禁令人回想起
350
年前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然而,更普遍的是来自宗教或法律的妥当性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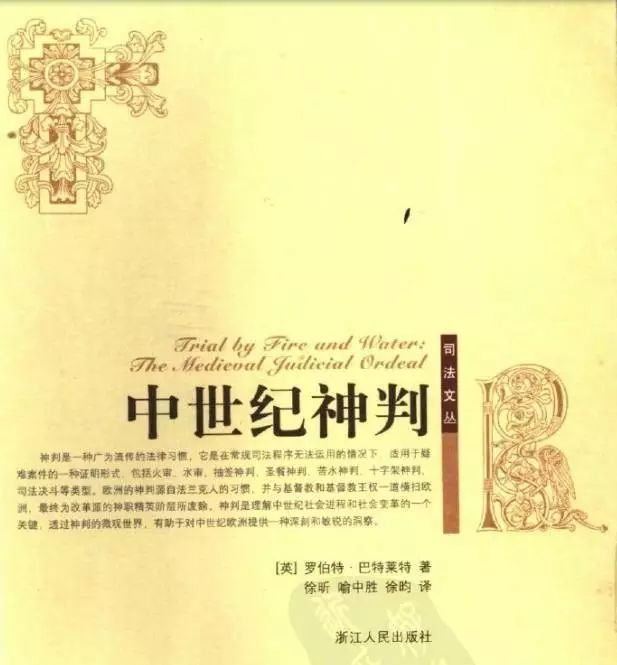
神学上的反对类似于
12
世纪改革派神职人员所提出的那些异议。对于天主教和新教的许多牧师来说,水验女巫似乎与设计它来揭露的巫术一样,也是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魔法。它使用
“
恶魔的手段来追捕恶魔
”
,
它是迷信的,且试探上帝。清教徒牧师威廉·帕金斯
(WilliamPerkins)
将水验及类似程序说成
“
有些像未经上帝的命令授权的巫术行为
”
。
1692
年,使用水验的殖民地康涅狄格的僧侣宣称,
“
我们不能不与大多数神职人员的观点保持一致,即试图以水验对巫术定罪是非法且罪恶的
”
。
正如某些反对者指出,它是
“
一种对立的魔法
”
。
激烈的反对尤其来自上级法院和大学的法学院。他们瞄准这样一种以粗俗之人和无知的下层法官为特征的证明形式,反复发表谴责。法学家戈德尔曼在
1591
年写道,
“
冷水神判如今已被禁止,这是学者们的共识……这一共识为德国大学的所有法学院所赞同。背离这一共识的法官是错误的。
”
莱顿
(Leyden)
大学法律与哲学系就该主题提出了一项篇幅浩大且满怀敌意的意见。
此类反对本身常常表明上级法院或中央当局力图阻止下级法院对水验的使用或纵容。一起有关此事性质的著名的意见冲突发生于
1590
年代的法国。两位女巫被香巴尼地方法官施以水验,并宣判有罪。案件提交到拥有上位管辖权的巴黎高等法院,
*
并因这些
“
奇异的程序
”
而被宣布无效。
最终,高等法院于
1601
年作出一项判决
(
arrêt
)
,在巴黎高等法院辖区内的所有法庭禁止该习惯。
不过,
17
世纪中叶的反复禁止表明,下级法院仍在违背巴黎高等法院创立的规则。
上层当局与下级法院之间的摩擦也会在其他地方见到。在
1595
年对佛兰德斯议会作出的一项命令中,腓力二世
*
政府指令,应
“
依法并以正当的司法程序
”
审判女巫,而非水验,并力图限制下级法院对女巫审判的管辖权。
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连一世
(Maximilian Ⅰ)
于
1622
年发布的有关猎巫的一般指令中,明确禁止水验。
1677
年,施蒂利亚
(Styria)
一位地方官员被政府禁止使用冷水神判。
不只是下级法官受到诱惑而诉诸于水验女巫;完全在司法程序外,该习惯在愤怒的农民或暴民中亦
屡见不鲜
。例如,在
1644
年的勃艮第,
“
每个人,凭借自身的私人权威,篡夺了司法权;最底层的农民将自己提升为治安法官……他们排除一切司法手续,而企求仅仅依赖于水审
”
。
翌年,马太·霍普金斯在英格兰发起的大规模猎巫运动也将水验的使用视作一种特别的证明,直至
“
有能力的神职人员
”
的批评才促使霍普金斯就此罢手。
在内战已扰乱正常司法运作时发起的歇斯底里的霍普金斯运动,是出现水验女巫的一种绝对独特的环境:
而他在不足一年中
于一郡内绞死六十人?
某些人仅因无法下沉
……
最引人注意的,水验不仅是暴民强迫身不由己的嫌疑人承受的一种习惯,而且经常是嫌疑人主动请求的证明方式。例如
1635
年,勃艮第的一位农民
“
让其同伴对自己进行了两次水验,以向他们证明自己无罪
”
。
1696
年,法官不得不再次在勃艮第的乡村干预两位教区牧师,他们
“
经一些农民请求而组织水审,这些农民被其同伴指控施行巫术,又未能找到任何更好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无罪
”
。关于冷水神判,
18
世纪早期一位德国作者观察到,
“
即便今日,我们被指控施行巫术的女子仍习惯诉诸于它……
”
霍普金斯也熟悉这一现象:
“
魔鬼的手段高超,为了说服许多人自愿接受审判……他建议他们进行水验,并告知他们将会下沉且以此方式洗刷嫌疑,其后,当他们以此方式受审而漂浮水面时,他们会恍然大悟,魔鬼欺骗了他们。
”
正是地方法官乐于采用水验与大众对该程序的敬畏相结合,使得在
17
世纪根除水验困难重重。进而,在猎巫本身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将一项程序的例外从猎巫运动中分离出来是难以实施的。因此,尽管学者和官员对水验女巫的抨击显然抑制了该习惯在
17
世纪的发展,但只有当法官和立法者不再相信巫术本身时,这种神明裁判的最后残余才会逐渐烟消云散。
18
世纪水验的案件不难发现,但它们日益限于擅用私刑的暴民的行动。至
19
世纪的英格兰,水验的通常后果是会引发一项有关袭击水验者的指控。例如,
1864
年,两个人因对一位女巫施行水验,而依《切姆斯福德法》
(Chelmsford Assizes)
被判袭击罪。作为一种选择,开明的治安法官可能会在该行为成立前阻止潜在的水验者。至该时期,水验女巫在这些治安法官眼中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大众迷信,若不加控制便可能走向邪恶。
16
和
17
世纪的水验女巫,从未获得中世纪神判在
1200
年前所博得那么多的官方认可。它被轻视了。这并不如此令人诧异:在
18
世纪早期,一位新教徒作者可能会谴责它是
“
头脑简单者仍暗地相信
”
的
“
一种天主教的迷信
”
,而早在
1590
年代,它便明确地与“无知的民众”联系在一起。对于现代研究者来说,此处存在一个陷阱。直至
20
世纪初依然残存的神判——适用于巫术的冷水神判,被视为大众的、迷信的、甚至
“
天主教的
”
,并且是一种乡民无知的产物。至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水验确实仅由未受过教育的乡民发起。然而,这种神判的残留和退化形式的特征,不应影响我们对该习惯在其全盛期的描述。在现代世界中更为隔离的乡村地区发现一种中世纪生活方式的某些学者,其思维倾向带有一种误解。中世纪社会不仅以小规模的农民共同体为基础,而且以军事贵族和神职人员精英为基础。在中世纪末期与
18
或
19
世纪之间,贵族受到教育并部分地温和化,神职人员精英的一部分则被世俗化。这种受过教育的新兴世俗精英阶层瞧不起乡下人
[
对女巫
]
的指控,在某种程度上指责他们是早期的非理性迷信的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的治安法官,既需抑制村民施行水验的迫切要求,也身为
19
世纪神判研究的先驱者;他们将会发现,自己时代的无知乡民与中世纪先辈的信仰和习惯一脉相承。他们编排了一幅关于过往者、大众、无知者、未开化者、典礼官和乡民的令人信服的影像。该影像向我们讲述了大量有关近代早期阶级关系和文化的转型。这无助于我们对中世纪司法神判的理解。

回复关键词
获取相关文章
检察 | 烟花 | 大案 | 司法 |
宪法 | 伍雷 | 死刑 | 机场 | 枪
丨
上访
丨
司改
丨
无辜
丨
冤案
丨
申冤
丨
刑法
丨
刑讯
丨
律师
丨
人权
丨
旁听
丨
日本
丨
咨询
丨
阅读
丨
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