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七岁的时候在一场旧货义卖会上发现了一本1961版的《Eagle年刊》漫画年刊。其中有一篇漫画讲丛林探险者的故事,每天清晨他们都会把靴子脱下、倒过来抖一抖,以防里面有蝎子之类的东西。这给年幼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我也开始这么做了,而且习惯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所以,那是第一本改变了我人生的书。

1961版《Eagle年刊》书封 图片来源:stellabooks.com
我在伯明翰长大,那里当然没有蝎子。甚至,想找棵能爬的大树你都得走好远才能找见。我们小时候的确整天在外面闲逛,通常一个口袋里装着一本书,另一个口袋里则装着一把小刀防身,因为有时不免会走过汉兹沃思公园(Handsworth Park)——帮派的地盘。我从不是个乖孩子,而是个彻彻底底的“狠人”。三言两语很难说清那样的社会:任何的冲突、特别是小孩间的冲突,都以打架告终。想要成为人上人,这是唯一的方式。
我的父母不是十分热衷的读者,显然他们有许多其他事务缠身。但是他们尊敬书本。我们大多数书都是从图书馆借的,那时候我们家还有了一套体系,只要有亲戚来就要申请一张票,这样我们每周就能从图书馆借更多书了。甚至我们的狗也有一张票。我们就是靠着这样的小把戏才读书认字的。

父母的书我读得不多——不过我记得有一天在他们的卧室兜兜转转,结果在衣橱下面找到一本橙色的、企鹅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显然,他们是因为那场审判而买了它,想看看究竟写了些什么,同时又不想被我们看到。但就像所有怀着理想的家庭一样,我们加入了读书俱乐部,每个月都有装帧不那么精致的硬面小说寄到家里。过去我总无视它们,直到有一天我生病从学校请假回家,躺在床上养病随手拿起一本Nicholas Monsarrat的《白拉贾》(
The White Rajah
)。
这本书中,一个小地主去世了,他的领地和头衔传给了大儿子,而小儿子只得到了一个木盒,里面有两把枪。于是小儿子踏上了征途,一路上遇到了海盗和各色人等。最终他到达了一个遥远的岛屿,并成为了统治者——白拉贾。他是一个贤明的群主,然而有一天来大英帝国的人到岛上,宣称他们对岛屿拥有主权。而大英帝国派来的所谓的总督,竟然是他的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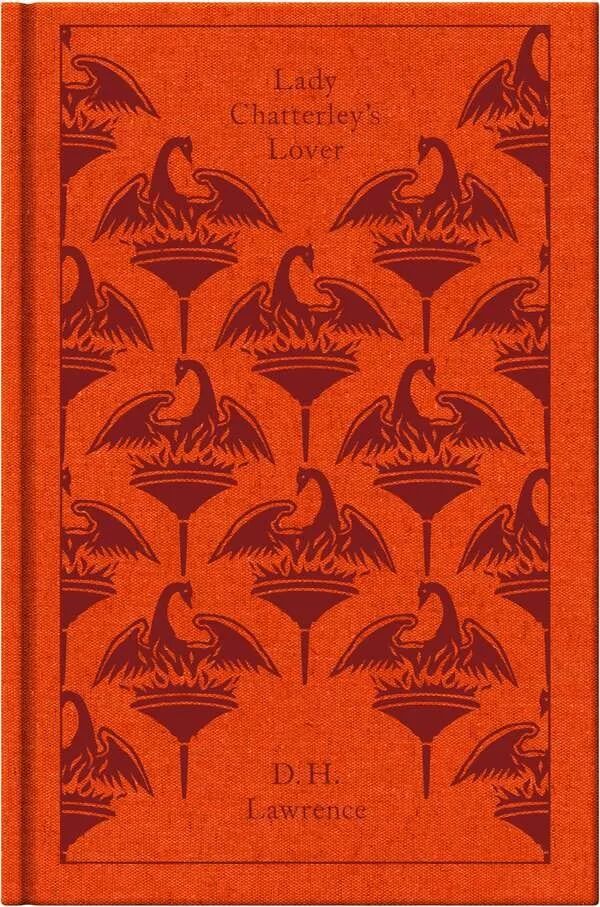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书封
Penguin Clothbound Classics Series
这样的情节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假如是现在的我,可能早就猜到了情节,但是那时候这是第一本让我大吃一惊的书,天哪作家竟然能对读者做出这种事来!童年读这些探险故事是否为日后写杰克·里奇(Jack Reacher)埋下了种子呢?这是个好问题。小时候我确实更容易被动作、历险的故事吸引。但是再过35年、差不多40年我才开始写作,所以很难说有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相信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又过了几年,我又发现了Alistair MacLean的《北极站:代号斑马》(
Ice Station Zebra
)。除去不忠实的旁白之外,这是本非常精彩的书。我的意思不是它采用了现在我们所谓的“不忠实的叙述者”(an unreliable narrator),而是他在临近尾声的部分为了达到操纵悬疑的目的,刻意避开不讲某些事物。
我之所以这么在意,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释怀。我以为阅读体验不佳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是我的阅读方式不对。后来过了很久,大概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才能肯定地说:是作者不按规矩出牌。是他错了。如果一本书读起来没有畅快淋漓的感觉,那是作者的问题。在如此尊敬书本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萌生出了“一定是某人的错”这样的想法,这在观念上前进了一大步。

Ice Station Zebra 电影剧照 (1968)
来源:Imdb.com
从此我焕然一新。现在,我觉得身为作者有责任不带给读者类似的、困惑的体验。我非常非常仔细地确保在我的书里不会出现毫无征兆、毫无铺垫的意外。得按规矩出牌嘛。
我总是给人推荐William Styron的《苏菲的选择》(
Sophie’s Choice
)。我太太是纽约人,我就是在刚谈恋爱那会儿在纽约的一家书店找到了这本书。那年我22岁,大学最后一年,念的法律专业。当时我渴望进入娱乐行业,最后进了电视行业。不过,那时候我对当作家完全没有概念。
这本书讲了一个叫内森的人来到纽约,找了份出版业的工作,然后在这间粉红色的屋子里租了一间房——之所以是粉红色的,是因为房东装修的时候粉色漆最便宜。他有两个室友,三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神经兮兮的对峙。这既是一本西部小说,又是纽约小说、欧洲小说、二战小说、大屠杀小说,一部了不起的悬疑小说。我觉得它的情节慢慢铺开的同时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和张力。看似松散,但实际上有着一个强有力的叙事引擎在后方推动,带你前进。我非常喜爱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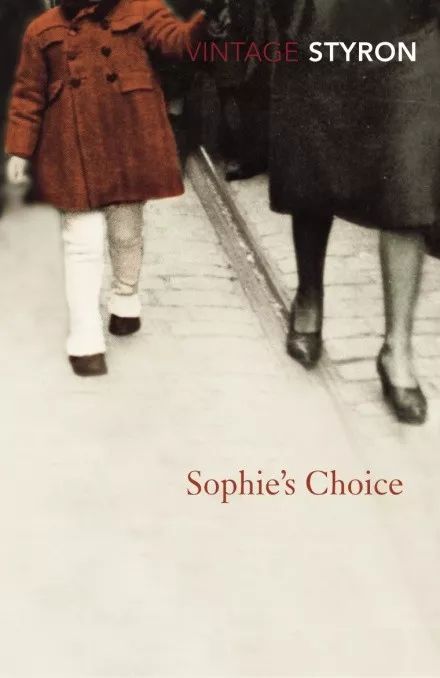
《苏菲的选择》书封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9年我出生了,纳粹德国就像一朵阴云笼罩一切。我对其远不止 “感兴趣”。Daniel Mendelsohn的《失去:寻找六百万之六》(
The Lost: A Search for Six of Six Million
)里讲到作者童年时期一年一度拜访佛罗里达州年长的亲人们,所有的老太太看到他就会情不自禁流泪,因为他长得太像没能逃出欧洲的叔祖父。这件事深深影响了他,长大以后他有了时间和能力就决定找出当年的真相,叔祖父一家究竟经历了什么。这本书以十分学术的眼光审视那段时期,因此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了讲故事的本质和旧约的历史,全部交织在这个紧凑的侦探故事中。
它是否触动了我去写非虚构呢?并没有。虽然我才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写完了一本叫作《英雄》(
The Heros
)的书。我想表达观点之一与进化遗传有关,这是数百万年的生存遗留下来的产物。让我着迷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上一次经历的气候剧变是大约一万四千年前结束的最后一个冰河纪。它持续了大约八百个世代,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祖先。

《杰克·里奇》系列 Box Set
我的问题是:那些为自己的生存豁出去的、杀出一条血路的人都是谁呢?我们都是野蛮人的后代,所以我们想象中的文明和体面的表象都是无比单薄的。杰克·里奇呢,你知道他身上流着一个部落保护者的血液,但是他没有部落、只有自己。因此,该出手时,他就会出手。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在纽约的客厅。这间公寓里其实有三个客厅,在我的图书馆非虚构部分的最深处,我有一张9英尺长的沙发。我常常躺下来抽两支烟,放松神经、排空杂念,这样才能获得最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只要有机会,有烟灰缸有咖啡,我就能一躺好几个小时。我一点都不想停下来,甚至都不想站起来吃东西,所以我常常饥肠辘辘。这样的感觉简直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