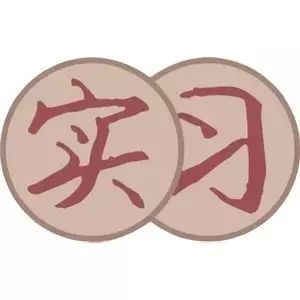综合比较2024年与往年的中介机构行政处罚案件,中介机构提出的陈述申辩理由及监管部门对相关理由回复重点的重合度较高。除处罚时效等程序性抗辩以及积极配合调查等情节抗辩外,中介机构提出的主要陈述申辩理由包括:中介机构已勤勉尽责、公司恶意造假因此中介机构无法发现、中介机构没有主观故意等,可以将这些理由归纳为“该做的都做了”。而证券监管部门对前述理由的回复则包括:中介机构未关注到项目中的明显异常事项、中介机构未严格执行职业规范、中介机构工作底稿存在缺失等,可以将这些回复归纳为“该做的没做(好)”。本文拟分析以上中介机构与证券监管部门的观点分歧:
(一) 中介机构“该做什么”
如前所述,中介机构提出陈述申辩本质上可以归纳为“该做的都做了”,而证券监管部门的回复与之相对应,认为中介机构“该做的没做(好)”。由此可见,明确中介机构“该做什么”是有效申辩的首要前提。界定中介机构“该做什么”需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介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中介机构是否需对超出专业能力范围的事项负责,以及中介机构是否需对“无法发现”的事项负责。
1. 中介机构的职责范围
界定中介机构的主要职责较为简单,各类中介机构的职责内容即为保证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证券法》第163条规定,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及其他鉴证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
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为例,《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7号——招股说明书》第87条至第91条明确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律师、为发行承担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发行承担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为发行承担验资业务的机构应作出的声明,声明内容均为确认招股说明书与其所出具的专业意见无矛盾,若相关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因此,若中介机构出具的相关专业意见失实的,则证券监管部门即有较充分的基础认为中介机构“该做的没做(好)”。由于出具文件失实是客观事实,中介机构只得主张存在失实部分的内容不是其“该做”的,进而不应承担相应责任。
2. 中介机构的“特别注意义务”与“一般注意义务”
中介机构主张出具文件相关内容不是其“该做”的方式之一即主张相关内容超出其专业能力范围,属于其他中介机构的职责范围,其不应对相关内容失实承担责任。这就涉及特别注意义务与一般注意义务的区分问题。特别注意义务与一般注意义务的区分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问题:
其一,特别注意义务与一般注意义务的范围。
保荐机构与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执业规则对于注意义务的划分规定较为明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22条、第23条与《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较为明确,保荐机构对于其他中介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可以合理信赖,承担一般注意义务,对于无专业意见的内容承担兜底性的特别注意义务;律师对法律专业内容承担特别注意义务,对于其他事项承担一般注意义务。
其二,注意义务的履行标准。
中介机构对于其他机构的专业意见负担一般注意义务,对其专业领域内的意见负担特别注意义务。其中特别注意义务的履行标准应与前述审计机构的勤勉尽责标准保持一致。以保荐机构为例,保荐机构一般注意义务的履行以“重大性”为标准,对于其他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其中存在重大异常、前后重大矛盾,或者与保荐机构获得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保荐机构负有调查、复核的义务;保荐机构的特别注意义务要求其对于无专业意见支持的内容,应获得充分的尽职调查证据,在对各种证据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
其三,合理信赖制度。
合理信赖制度是中介机构一般注意义务的重要内容,当中介机构充分履行一般注意义务时,即应有权主张合理信赖其他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尽职调查操作指引》等规则中皆已规定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合理信赖制度。2022年初发布的《关于注册制下提高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的指导意见》《监管规则适用指引——法律类第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则进一步完善合理信赖制度,明确在履行必要的调查、复核工作的基础上,可以合理信赖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并且细化“必要的调查、复核工作”的工作标准,明确对于符合合理信赖条件的中介机构,可以免除行政法律责任。
因此,如果中介机构能够证明相关失实意见不属于其专业领域,且其已经充分履行注意义务的,即可以主张合理信赖其他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换言之,发现相关信息虚假不是其“该做”的。
3. 上市公司舞弊下的中介机构责任
将发现公司故意隐瞒或恶意舞弊纳入中介机构“该做”事项范围需慎重考虑,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例,若公司存在系统性造假、与相关主体恶意串通造假等情况的,则会计师事务所即使执行了充分的审计程序仍无法识别造假,要求会计师事务所识别此类造假,无疑会为会计师增加过高的执业成本与违规风险,不利于证券服务机构整体的发展。因此,公司存在系统性造假、恶意造假是中介机构主张不应承担责任的常见理由。然而,审慎核查、发现造假是中介机构作为“看门人”的应尽职责,因此,针对中介机构是否应为公司系统性造假、恶意造假承担责任的问题还需充分讨论,具体应关注:
首先,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案件并不要求主观故意。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违法性认定的重点围绕中介机构的服务过程本身是否存在重大过错,公司具有造假故意以及中介机构不知悉公司具有造假故意并不构成免除未勤勉尽责责任的事由。
其次,中介机构重大过错需单独认定。未勤勉尽责的认定应围绕中介机构服务过程本身,中介机构应当保证对公司重大事项予以充分关注,对于异常情形应当进行充分核查。
最后,中介机构主张公司系统性造假应承担举证责任。公司系统性造假提高了核查难度,中介机构经充分核查仍无法发现造假的,应存在免责的空间。针对公司存在系统性造假的事实,中介机构应承担举证责任。
具体到2024年中介机构未勤勉尽责的案件中,仍有较多的中介机构提出公司存在故意舞弊的申辩理由。对此,监管部门的关注点则在于中介机构是否对明显异常的事项予以充分关注。对于中介机构而言,具有重大性的事项本就是其应关注的重点,中介机构未匹配相应关注进而导致相关事项出现虚假记载的,即会被认定为未勤勉尽责。在此部分列举2024年度中介机构行政处罚案例中涉及重大风险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