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高考故事,我们一起来聆听关于医生们的高考故事。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年,让我们回望属于我们自己的,那段既漫长又短暂,既难眠又苦捱的岁月,回望其中的痛与喜,苦与泪,忧与惧,并由此更深刻地体验,高考所独有的塑造人生、改变命运的力量。
不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高考故事。
我们一起来聆听关于医生们的高考故事:

“我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当年的高考题目。”
——李光昭,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外科主任医师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的高考题目,语文作文有两个题目任选,第一个是“给越南人民一封信”,是为了鼓舞他们的士气。另外一个是“学习与革命”。政治题目是“一分为二”,还有就是学习了《纪念白求恩》,谈谈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我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都是名列前茅,高考备考的时候,我并没有专门去复习或是准备,也知道以我的成绩肯定考得上大学。

李光昭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

1965年李光昭上广州报到的汽车客票
直到后来,我的两个女儿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们夫妻俩在医院忙于工作,根本无法顾及孩子高考的事情,女儿填写志愿,我们俩也完全没有参与,女儿自己选择了与父母一样的从医之路。

大学录取通知书

“如果考不上大学,就要上山下乡。”
——许美燕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原眼科主任、眼科主任医师

许美燕准考证
我是1965年参加高考的,当年我18岁,在填志愿的时候,填了三个,第一个志愿就是中山医的临床医学系。记得1965年7月高考的那天,天气非常好,我是在汕头一中考场考试,因为以往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考试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我们这一届高考也很特殊,如果考不上大学,就要上山下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即使上了大学,仍有许多学校都停课了,但我们中山医的学习生活依旧是紧张、忙碌,我们也会跟着教授们一起下乡与农民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服务贫下中农,为当地村民看病治疗。

1965年高三毕业的许美燕

“我们的教授自己献血割皮去抢救重症伤员。”
——姚楚征,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原烧伤科主任、烧伤外科主任医师
我对大学最深刻的记忆,是1971年,我跟著名烧伤医疗专家吴国勤教授到揭阳县人民卫生院下乡,参与了一次大型的群体性烧伤的抢救行动。某一个电机厂突发火灾,许多工人被严重烧伤,命悬一线。我的老师吴国勤教授为了抢救一位烧伤面积高达90%Ⅲ°烧伤病人,除了献血之外,还割下自己的皮去救这个体无完肤、素不相识病人。我清晰的记得,是我给教授的大腿做了局部麻醉,然后取下一层薄皮,献给病人做植皮手术。

感恩第一军医大的每一位教授,是他们用火一般的情感,让我们领悟第一军医大传统精神的魅力所在。吴国勤教授“割皮救人”的无私奉献,成为了学生心中一辈子的楷模。在生活的大海上,第一军医大教授们就像高高的航标灯,屹立在辽阔的海面上,时时刻刻为我指引着前进的航程!

1977年没有冬天,只有充满着希望和憧憬的温暖阳光。
——胡顺广,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名誉院长、口腔主任医师
从知青到考生
40年前的夏天,胡顺广还是广东饶平县知青下乡点的一个知青。那年,也是他在农场做工的最后一个夏天。第二年阳春3月,怀揣着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口腔系录取通知书,胡顺广从77届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首批大学新生。

“感谢这个时代给予这个机会”
记得,我们的考场(联饶中学)有660多名考生,只考上了三人,1个中大,1个中山医,1个是武汉大学。我觉得当时能考上是幸运,而不是自己很厉害,恰恰是我们这些人不甘心沉沦,想着有一天知识有用,所以一直有准备。当风云突变的时候,赶上了时代的步伐。当年考上的人后来证明是回报了这个时代,但首先要感谢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这个机会,如果没有邓小平说要恢复高考的话,怎么可能从山沟田野里走出来呢,绝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很幸运。

1977年高考现场
关于高考的记忆,有几个地方是我感受非常深的,第一是要先填志愿,填完再考试,考完了之后如果觉得不好可以再改一下。当时考前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填中山医,第三志愿是填华南理工,那时候叫华南工学院。考完之后我自己估算了一下,平均分大概有87分(100分制),我觉得清华可能是考不上的,于是我就把第一志愿改成中山医学院。
考上的人都是有准备的平时坚持不懈学习的人,这点很重要,现在回过头来看,77年高考那些题都是很简单的题,现在的初中生都会做,但是那时候的许多人还真的是都不会做。
当知青的时候,我对数学很有兴趣,自认为数理不错,平时会偷偷看像《微积分》之类的书籍,那时候一位中学老师见我对数学感兴趣,就送我十几本老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出版的《数学通报》杂志。拿出来一看,发现全部看不懂,几乎没有一道是看得懂的,那时候如同当头浇下一盆冷水,信心都没了,打击很大。报考时都想放弃理科报文科了。但是平时的学习仍然回报了我:后来在数学考试中出现了加分题,考线性方程,两道题20分,我虽然也有忙中岀错,但也基本上做出来了。当时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
“大学录取通知书,妈妈帮我缝在内衣口袋里”
我一直没有接到通知书,而周边镇考上中大、华南理工的知青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时候去祝贺其他考上的知青,去车站给他们送行,他们都安慰我说不要紧,你考得那么好,通知书很快就会来的。直到1978年三八节那天,领导和所有的女知青都到镇里开会,只有我们男知青没有休息,还要继续下地干活。
我现在还记得,当天非常冷,碧绿的秧苗已长得有三四寸长,我挽着裤腿下田泼粪施肥。水很冷,一直冷到骨髓里,上来后腿都没有了知觉。正在那时,有人来通知我到镇里学校领录取通知书,其实之前有人跟我说可能是被某个技术学院录取了,可是我并没有填那个学校啊,不过只要有书读就行,什么学校都行。
记得我那时候最后一个志愿填的是武汉钢铁学校炉前专业,就算是烧煤,我也愿意。我从田里上来后跑步去学校,校长跟我说要到县教育局去拿,我换了衣服借了辆单车踩去,七八公里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那叫一个飞奔!拿了录取通知书后发现距离学习报到时间只剩下一个星期了。那时候七天是远远不够的,我还要移交农场的工作、账目,还得办户口、办证明等等,后来就给中山医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申请延期一个星期,中山医都受理了。

旧时的中山医学院
1978年3月22日,我乘着破旧的汽车颠簸了14个小时才到达广州,因为晕车,不敢吃东西和喝水,怕呕吐,到了广州已是晚上九点多,下了车两眼一抹黑,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远远看到有一个接生点,走进一看是中山医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师,原来学校为了两名延期报名的学生特意派了车去接,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学校,很感动。
在核对信息时,录取通知书是我妈妈缝在内衣口袋里,拆除缝线时老师还打趣说,今年的学生都怎么了,录取通知书不是妈妈缝就是姐姐缝,还缝的那么严实。
“城里的树还包水泥”
到学校已经是凌晨12点多,借着昏暗的夜色,我看到校园里一些巨大的百年棕榈树,我踢了两下、抱了抱树干说:“城里的树还包水泥啊”。多少年过去了,时至今日,还不时有人拿这来调侃当年来自农村的知青师兄。
那时候学业非常紧,暑假三个星期,寒假两个星期。星期六日课室里也坐满了自修的学生。77年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因为十年的断层,小的学生15岁,大的学生35、6岁,相差20多岁。第二个是学生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阅历非常的丰富,能够非常自觉地学习,对自身的要求近乎苛刻,会自觉地审视自己。很多人都是知青,学习非常刻苦,没有他们吃不了的苦和克服不了的困难,做过知青的人都明白一点,他们是在命悬一线的地方回来的,突然有个机会可以让他们读书,学习的机会视之比生命还珍贵,他们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一心一意“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就是77、78级学生的状态。

胡顺广的毕业证书
非常感谢中山医给予我们的教育,母校的华盖让别人很尊重我,愿意跟我交流,这是母校给我的便利,前辈的荣耀分了一份給我。高考是时代给予我们的机会,77、78级的大学生刚好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舞步一起前进。


“去大学报到,除了带上录取通知书、粮票、户口本、政审证明,还需要带上十几本厚厚马列主义的原著。”
——王学林,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原耳鼻喉科主任、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1980年王学林在中山医留影
我是1979年参加高考的。1975年高中毕业,作为下乡知青被借调到市文化宫工作。77年恢复高考,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殊原因我无法报名参考。到了78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但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即便我考了很高的分数,还是没有被心仪的学校录取。我不甘心,于是在1979年的第二次参加高考。

1979年的高考准考证

王学林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记得1979年高考的那一天,天气非常非常热,我是在汕头二中的考点,考试教室在顶层,实在太热,桌椅都被烤得滚烫,监考老师无奈用报纸将学生考试用的桌椅包上来降温。考完之后,从教室出来,就感觉走出蒸笼一样,但我对我的考试成绩满怀信心,一考完试我就跑去新华影院看电影了。后来放榜,我的高考成绩比国家重点线高出了20多分,顺利考上了中山医。去大学报到,除了带上录取通知书、粮票、户口本、政审证明,还需要带上十几本厚厚马列主义的原著。

王学林大学时期的实验课

“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金榜题名’的幸福。”
——温文川,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大内科、呼吸内科主任、内科主任医师
对于高考的记忆,我记得那是人生第一次体会到“金榜题名”的幸福,放榜那天,就在汕头市招生办(现大埔会馆)的外墙上贴着几张大红榜,我在300多个人名中找到了自己名字和录取学校校名,无论用什么样的言语都无法表达当时的兴奋与激动。

原汕头市招生办
1980年高考前,一直在市中学生乐团任圆号演奏员的我,并没有像有些同学一样往音乐学院的方向努力,而是在最后一年调到汕头一中冲刺普通高考。怀着对生命、医学的敬畏,和一股内心抑制不住的冲动,我报考了苏州医学院。感谢苏医,苏医是一所正规传统的好学校,勤奋向上的校风影响了我整个职业生涯,不止是受益匪浅这么简单。

1980年,苏医篮球场

温文川在校门口留影

“对于农村的孩子,只要有一点点条件,都会拼尽全力去过高考这座独木桥。”
——胡钦擎,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麻醉科主任医师
只有考上大学,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就可以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对得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的艰辛养育。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农村孩子的梦想。
我是家里的长子,高三那年,我是一边备考一边还要帮家里干农活。感恩我的父母,他们虽然从未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十分支持儿女的学业,总是想尽办法为子女创造学习条件。记得那个年代,晚上经常停电,为了不影响我复习,父亲找来了蜡烛、煤油灯给我们照明,还有⋯我父亲平时话不多,但这句简单而朴实的话却经常挂在嘴边“要认真读书,要考大学,考不上就得在家种田。”作为农村的孩子,只要有一点点条件,都会拼尽全力去过高考这座独木桥⋯⋯

“‘医二代’当上医生与爸妈做同事。”
——李卓华,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产科主任医师
我是个“医二代”,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眼科医生。从小在医院家属院长大的我,成长的过程似乎都与医学有关。因为从小的耳濡目染,我们更早感受到医生这份职业“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内蕴,更深体会到这份医生职业背后汗水、泪水与笑容交织的复杂。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在寻找职业的路上,我选择了穿上和父母一样圣洁的白袍,选择了负上和父母一样救死扶伤的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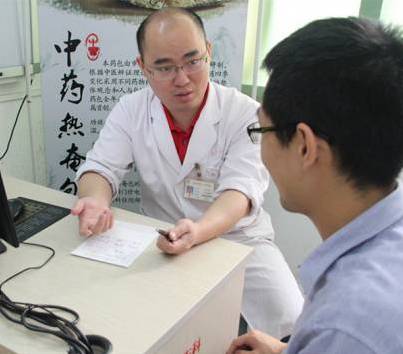
“清楚自己未来的路,所以报志愿的时候填的全是中医。”
——纪少丰,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骨伤科副主任、中医骨伤主治医师
从小觉得中医师坐诊很帅,由此与中医结缘。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很果断,清楚自己未来的路,所以填的全是中医。

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曾跟随学校志愿者服务队走进大山为村民义诊;大学暑假的时候曾经跟随肝病专家谌宁生在门诊坐诊;看到附属医院哪位中医专家出门诊就蹭课学习一些招法。在研究生期间,我跟随骨伤科名老专家姚共和教授,姚教授专业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们经历了一场非典型高考”。
——吴声恺,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肾内科主治医师
我们这一届经历了一场“非典型高考”。2003年,全国高考首次提前一个月进行、广东考生自此开始网上填报志愿……非典疫情在全国蔓延,尤以广东为烈,为了防止非典疫情通过考场传播,所以高考的考场都必须测温,进入考场前,校医都会手持耳温计对我们的前额测试,体温正常者才能进入警戒线以内的考场,超过38°的就会被马上隔离。

2003年,我表哥在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他参与了广东第一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的抢救,自己也不幸也被传染,万幸表哥被成功抢救回来。在抗击非典抢救生命的战场上,医务人员总在最危险、最紧急的、人民最需要的场面出现。医务人员与非典病魔进行殊死斗争的事迹让我深刻感受到医务人员的神圣与伟大,于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全部填报了医学院。

“选择医学检验专业多少也有点受电视剧的影响。”
——林欣乾,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师
因为高三的大量做题,练习,考试,让整个人一直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但真正上考场拿到试卷的时候反而冷静下来。很怀念高考前拼搏的日子,也希望在自己未来学习上找回那份感觉。选择医学检验专业多少也有点受电视剧的影响,国外检验是归类为病理学科,通过血液体液检查就能了解人体基本状况,第一时间反应异常部位,是医学诊疗的第一步也是最前线。

“高考带给我的那段回忆,是纯粹努力的自己。”
——林子玟,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剂师
那个时候我们拥有的理想,大概是人一生中最明确清晰的时候了。每个人都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广州中医药大学,我早就认定了这个大学。很单纯的想法,我以后要跟中医药打交道。那时候的自己,对中医药的理解少之又少,只因为那份对中医药的喜欢,敬重与崇尚。很幸运的是,我如愿以偿了,虽然学业并不轻松,但我并不后悔,对中医药的爱意也从未减少。
我很珍惜高考带给我的那段回忆,和我一起奋斗的朋友,还有那个纯粹努力的自己。我更希望,我能一直保持一种热情,对中医药事业的热情,明确而清晰。
来源 |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订阅号 作者 | 郑瑞年 陈洁
版权归属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