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农·葛兰伯格
(Arnon Grunberg,1971-),荷兰当代著名作家,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一个德籍犹太裔家庭,1995年迁居纽约。
葛兰伯格多聚焦现代生活场景,犹太文化和历史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其题材和文风多变,擅长以滑稽、反讽或冷幽默的方式探索沉重灰暗的主题,如暴力、色情、原教旨主义、日常生活中的非理性、人际间施虐与受虐的关系等等。《锱铢必较》(
Huid en haar,2010
)以荷兰和美国大学为场景,探讨“爱的经济学”及其后果。主人公罗兰·奥布斯坦是一位离异的大学教授和经济学家,力求将经济学原理贯彻于一切人际关系中,甚至将爱情也视为双方各自谋利的交易关系。由此,在主人公、女友瓦奥莱特、丽以及其他人物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欺骗与背叛的戏剧,小说最终将读者引向关于理性、情感、爱、责任和道德的思考。

阿农·葛兰伯格作 尚晓进译
当瓦奥莱特厌倦了,厌倦了那些人,厌倦了闲谈,厌倦了聚会,当她想走开却又懒得解释时,她会说:“我去做瑜珈了。”
有时候说做瑜珈说不过去。所以,她另有托辞:“我要去睡了。明天得早起。”这也许显得不够有活力,但不是什么非得显得有活力,只要实际上有活力就好。
无论如何,她不喜欢熬夜。凌晨两点对她够晚了。她喜欢跳舞,但不会跳通宵。有时候,她设想着有人跟她说:“咱们换个地儿去吧。”但没人说过。当然,真有人这么说也无妨,总之你可以回答:“不行,今晚不行,或许改天吧。”
她的床靠着窗户。抬头可以望到窗外,她能看见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有个游乐场。她喜欢这景物。她喜欢住在市中心。
有时候,她在房间里的镜子前跳舞。镜子不大,但足以照见她的全身。

她一头暗金色的头发,现在染成浅金色了。她头发浓密,汗毛也重。她有时剃汗毛,但剃得光溜溜的也不是她的做法。她不再是小学生了。
她睡着了,头压在一本书上——村上春树的《奇鸟行状录》,是两个朋友送的生日礼物。小气鬼的朋友,两个人合送一本书。
瓦奥莱特喜欢村上春树,但这本书的问题是太大了,不方便带在列车上阅读。
村上春树的旁边躺着她的手机,手机旁是她的毛绒熊。有阵子,她觉得自己早过了抱毛绒熊的年龄,她从六岁起就抱着这只熊了,她一直把它唤作“熊先生”。她去上大学时,把熊先生装进了塑料袋里,可是大三新开学时,她反悔了,把熊先生从塑料袋里解放了出来,从这以后,它就一直睡在她身边,就好像从未分开过。
它急需动手术了。在它屁股靠上的地方有个小洞,填充物慢慢从洞里漏出,但她太忙了顾不上。没时间去找玩具医生,她自己做似乎也不合适。她有时对熊先生说:“马上会给你安排做手术的。你别担心啊。”
不过目前她忙得没工夫管手术的事,而且工作是会越来越忙的。
手机铃声把她吵醒了,她接手机,依然睡意蒙眬。“嗯——”她说。接下来,还是:“嗯——”睡梦中,手机铃像闹钟在闹,等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时,她才喃喃地说:“你好?”
此刻,她感觉到脸颊还压在书上,她把书推到床下,砰地一声,书落在地板上。
这是厚书的另一个坏处。掉落的动静太大,能把邻居吵醒。
“哦,是你啊,”她说。“我以为是管道工呢。”
“
你当我是管道工?”罗兰·奥布斯坦问。
“
我以为你是来通马桶的。”
她嗓子眼里呼隆了几下,这才彻底清醒过来。“通马桶?”
“
我正梦见管道工呢。他明天过来。马桶堵上了。你在哪儿呢,亲爱的?”
“
在宾馆房间里,”罗兰说。“堵了多久了?”“今天下午堵上的。怎么样?”
“
挺好的,”罗兰说。
“
他们喜欢么?”
“
喜欢什么?”
“
你的演讲啊?”
“
是,我想是的。”
她叹了口气,翻身趴在床上。“就这些?”她彻底醒过来了。就好像天大亮了,她正要起床一般。就好像她随时准备骑上车上班去。她有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她想着自己的工作,还有男友。
“
是,就这些。”
男友寡言少语,有些日子就跟熊先生一样沉默无语。她想让他说话,但不知怎么办。她试过很多办法,比如休假、浪漫晚餐。有一次,她甚至说服他帮她给意大利咖啡杯涂彩绘装饰,但干完后,他告诉她,他好像把五年的咖啡杯都涂完了。而且,他们一起涂彩绘时,他也没多少话。
下午,她坐在桌前,吃着一袋甘草糖,有时会想,自己是无计可施了。她唤不出他内心深藏的温情。他像是一只烧木柴的火炉,而她无法点燃。
“
你还忙别的吗?你在看邮件么?我听见你打字的声音了。如果你宁愿回邮件也不肯和我说话,那你也不必半夜打电话给我。”
“
我没打字,”罗兰说。“我听见了。”“我没打字,”罗兰又说。
“
我听见了。”
“
我刚才没打。”
“
你以为我疯了?你打电话叫醒我,然后你打字。如果你在打字,干吗打电话给我?”
“
我刚才没打字,”罗兰重复道。“我打电话是因为你打给我了,你还发了短信。两次,确切地说。”
“
那你为何不说点什么呢?”瓦奥莱特追问。
“
我不是个健谈的人,”罗兰说。“你知道的。管道工什么时候来?”
“
早上,我想。你又在打字了。”
“
我没打字。”
“
请你停下好吗?你在和我说话。你专心和我说话。不要打字了。”
“
我专心了。”
此刻,瓦奥莱特在床上坐直了身子,怀里抱着熊先生。它情况很糟糕,一只腿要掉下来了。
“
谈话的目的是交流,不是吗?如果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为什么打电话?就没有值得说说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罗兰说。“很晚了,我累了。我爱你。”
“
哦,你能不能说得更真诚一点?听起来像是讨见鬼的支票一般。”
“
我爱你,”她听到,还是一样的调子。
她曾经想过参加空军,她想做点人家没怎么做过的事,无论如何,驾驶F-16战机的女性不多,但她放弃了这个念头。
“
下回不了,我保证。可我不打电话吵醒你,你也一样会生气。我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我就没有做过对的事。”黄页上有玩具医生的电话吗?这是个很老旧的行业了。
“
听着,我再努力一次。谈话是两个人的交流。而我们在做什么呢?”
“
我们在谈话,”罗兰说。
“
不是!”瓦奥莱特喊了起来。“我们不是在谈话,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我听见你还在打字。请你停下来好吗?”
“
我可以一心两用。我一边打字,一边和你说话。我累了。我现在打字的话,过会儿就可以去睡了。我在节省时间。”
“
我不是你省时间的工具。我是你女朋友,该死的!”
“
两者并不矛盾,”罗兰说。“好的女朋友也是省时间的工具。”“好吧,我再说一遍。你的演讲怎么样?”
“
你已经问过了。挺好。没什么不满意的,本来可以更好些。实际上,还行吧。不过,后来的讨论有点沉闷。”
“
我们可以不谈了么?”瓦奥莱特问。“或者,你有别的可以跟我说的?还是不说了吧,这不是谈话。什么也不是,根本不是。”
“
不,我想接着说,除非你不想说了。我不想让你伤心。我继续说,直到你挂电话。我不放弃。”
“
那么,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事吗?”
“
我已经都告诉你了。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
有,”瓦奥莱特说。“是有事情想跟你说的。我背叛你了。”她听见罗兰在笑。
“
你在笑吗?”她问。
“
是,我笑呢,”罗兰说。
“
你为什么笑?”
“
因为好玩,你不觉得好玩吗?”
“
不,我没觉得好玩,没有。我背叛你了。”顷刻间,一切沉寂了。“什么时候?”
“
哦,你现在停下打字了!”她喊道。“突然间你全神贯注了!你不打字了!”
“
什么时候?”罗兰问。
“
我说,大经济学家停止打字了,是么?”瓦奥莱特尖叫道。“不打字了!”
“
我还在打字,”罗兰也提高了嗓门。“如果你不那样尖叫,还是能听到的。听,我还在打字呢。咔哒咔哒咔哒。我想知道的只是:什么时候?”
桌子很小,几乎摆不下手提电脑了。电视机占了太多地方。房间里有一扇窗,但窗子打不开。也许是为了防止有人自杀。罗兰的外套放在床上。他脱了鞋。他喜欢穿着袜子在房子里走动。
他好几次猛力拉窗想打开它,甚至要求过换一个可以开窗的房间,但是没有,所以,他放弃了。反正他明天就离开。就算窗户永远打不开,他也无所谓。
从早上最后一次查邮件到现在,他又收到了二十八封新邮件。他喜欢尽快回复。于是,他回复完了。可这样的坏处是不断有新邮件发过来。没完没了。但他喜欢把工作做好。学生的或同事的邮件他都回复,即便内容是不必回复的,他也回复。他知道这很恶劣,但他想尽善尽美。男人的天性就是要出类拔萃。
“
前天,”瓦奥莱特说。
他起床,走进浴室,打开灯,又回到他的手提电脑前。键盘原本是白色的,现在已经发灰了。上面还有颜色古怪的斑点,他纳闷是什么时候沾上的。
“
和谁?”
“
一个男人。”
“
男人,就这些?就是个男人?”
“
就这些。”
“
哪一种男人呢?”
瓦奥莱特设计手袋。女用手袋。手袋在中国制造,但在欧洲设计。有时,她也设计别的,比如公文包。
白天,她在商业区边上的一间很好的工作室里工作,工作室设计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有时候,设计师也到中国去,这看起来是件喜忧参半的事。
“
男人,就只是个男人。”
“
我认识这男人吗?”
“
不,不认识。”
“
你肯定?我认识很多男人,有些你不知道我是认识的。”
“
你不认识他。”
他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间,打开小壁橱,里面有三个衣服架。这地方小气巴巴的,连衣服架也吝啬。他还是这样夹着电话,一边挂上了他的外套。
罗兰·奥布斯坦很快乐,这点他没有异议,因为他从不奢望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他想要的都是他能获得的。无法获得的,他不去想望。幸福的秘诀就这么简单。这也意味着,幸福或许最终不过意味着安逸、知足、无忧无虑而已,但对此他安然处之。
当然,他还有些未曾实现的抱负,但他总能期望,有朝一日这些抱负大多能实现。
“
为什么?我是说,你爱上他了?”
罗兰·奥布斯坦又坐在手提电脑前了。邮件里没有急需处理的,然而,他还是要全部都回复掉。他力求做到兢兢业业,体贴周到。对,就是这个字眼:体贴周到。
没有回答。
“
你爱上他了?”他又问,那口气就像你问:“电影好看吗?”
谈话没有按熟悉的程序展开,这令他兴奋。不仅是性意味上的。几年前,当他发现署名哈耶克(英国经济学家)的两封不为人知的信件和一张明信片时,他也兴奋了起来。不幸的是,信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会让他举世闻名。
“
没有,我没爱上他。我不是因为这个选择他。”
“
选择他,你选择了他?哦,那你为什么和他上床?如果你没爱上他?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
“
你和人上床都得先爱上吗?”
他想了想。以前他就这个话题发表过意见。只是他记不清自己怎么说的了。他喜欢时不时地就性这个话题发发议论。谈论性有时比这事本身更有意思,做爱必然是一种对峙,常留有遗憾,而且,只是凭借想象的力量才得以真切地存在。
“
不,不必,”他说。
“
只是一种挑衅。”
“
什么?”
罗兰合上了手提电脑。通常他能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阅读邮件或论文,但这会儿他无法兼顾了。夜深了。他累极了。他同时喝了几种不同的葡萄酒,随后,又喝了杯格拉巴酒。但还不是这些,不是格拉巴酒,不是葡萄酒,也不是因为夜深了。而是因为他所看到或勾勒出的场景:女友赤裸着躺在一个男人的怀抱里。他若是静心来分析这场景——他的工作就是分析事物,他必须承认,相对于有其他男人在,他更介意的是他本人不在场。他不在那里,这点困扰着他。他错过了什么。
“
要挑衅谁呢?”
“
你。”
“
我?哦,这就差不多解释清了。”
那么,他到底是在场了。缺席中的在场。但这听起来很别扭,这分析——如果可以称之为分析的话——无法令他信服。她躺在那男人的怀里时,他在何处呢?
他等她说点别的,但她看起来并不打算说得更多了。谈话显然结束了。
“
那现在呢?”罗兰问。
“
我不知道。”
“
你希望我说什么呢?”
“
我希望你说什么?”瓦奥莱特答道。“天啊,你没有任何感觉吗?你女朋友背叛了你,你反倒问她:‘你希望我说什么?’这是爱吗?是激情吗?你在乎吗?你到底在乎我吗?”她听起来不再开心了。她在大声说话,电话里传来她尖利而绝望的声音。
前天,他前天在做什么?他在开会。然后是晚宴。他在有两张空椅的桌前坐下。“这里有人坐吗?”他问。“你坐吧,”一位年长的历史学家乐呵呵地答道,接着,又自顾自地讲开了他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丽坐在他的右侧。在历史学家滔滔不绝地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当儿,她几次朝他抛眼色,眼神里尽是讥讽,但他不能确定这讥讽的眼色究竟是针对条约、他本人,抑或是滔滔不绝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讲到一半时,他们起身去呼吸新鲜空气。之前丽悄声说:“我再也受不了了。”
“
这是不是有失风度?”他问。
“
什么?”瓦奥莱特说。
“
你在我开关于二战大屠杀的会议时背叛我,这是不是缺乏尊重?”
“
这两者有什么相干?”
“
哦,照我看,很有些关系。我参加的是一个讨论二战大屠杀的会议,你是我女朋友,我在会上听人家宣读关于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论文,和我一起相处的那些人所思所想也都是二战大屠杀,而你却在背叛我。你跟他说这些了?”
“
谁?”
“
那人,你的那个男人,新男人。”
“
我要跟他说什么?他不是我的新男人。”
“
你俩在床上时算吧。”
“
那是。”
“
你跟他说了?我男友在开一个关于二战大屠杀的会议。”
“
没有,我自然不会说这个。”
“
或者你们不在床上?站着做的?”
“
我拒绝回答这个。太荒唐了。跟你没关系。”
“
那,是在哪张床上?”
“
我的床。”
“
你的床。难道没有其他床可用吗?难道你不能去他的房子吗?或者说,他没有房子?他无家可归吗?”
“
不,不是无家可归。”她听起来有些疲惫,他跟她开这类不宜对旁人开的玩笑时,她总是这种疲惫的样子。
“
你们用安全套了吗?”
“
是,那是自然的。”
“
也没有那么自然。你房间里有安全套?”
“
以前没用完的那几个还在。”
“
噢。他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
是,我告诉他了。”
“
他怎么说?”
“
我猜是这样。”
“
没说别的?”
“
你要告诉他吗?”瓦奥莱特问。
“
谁?”
“
这是他问我的问题。他是这么问的。你要告诉他吗?他离开前问的。他正在穿外套。冷不丁地,他问我:‘你要告诉他吗?’”
“
那你怎么说?”
“
要。”他,是说他,罗兰·奥布斯坦。有什么要告诉他。
消费者需要获得正确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问题是,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往往比消费者知道得更多。消费者存在一个信息上的滞后,需要弥补起来。至少,理论上如此。
他就是那消费者,现在正谨慎地着手解决他的信息滞后问题。
“
那他怎么回答?”
“
我不愿知道。”
“
他这么说的?他不愿知道?”
“
他是这么说的:我不愿知道。他原话就这么说的。”
为什么你不愿知道某些事情呢?他不想知道这件事吗?你又如何能肯定自己知道一切?
电视机旁有一面镜子,他可以看见镜子中的自己。他无法理解为何有人会在桌子的上方挂一面镜子。

“
噢,我想,这个我们已经谈完了,”罗兰一边说,一边望着镜中的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显得轻松,还是努力表现得轻松呢。
有些时日,他认为自己是个挺有吸引力的男人。这样的时日,他怀疑自己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但他绝不会形容自己为自我中心,远非如此。这样的好日子很少。即使对一个懂得不奢求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的人也是如此。
“
就这样?”她问。“你还想说点别的吗?”
“
别的什么?没有。我认为,这是一个故事,很刺激的故事。我是这么看它的。”
“
刺激?”“是呀。”
“
我和其他男人上床,你觉得这是刺激的故事?”
他坐在那里,面前摆着手提,手里拿着电话,这就是他在镜子中看到的情形。瓦奥莱特认为他照镜子花了太多的时间。有时候,她指责他虚荣,但谁不虚荣呢?照镜子也可能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他对着镜子,看自己是否疏忽了什么,比如,剃须膏的沫子、面包屑、圆珠笔的划痕等等。
结局未知,但最糟糕的后果也可以承受,这就是刺激。绝症不刺激,因为结局已经揭晓。于无望中怀抱希望,是悲剧性的,但不刺激。
“
你在哭?”他问。
“
没有。是的。我流了点泪。
”
“
这都颠倒过来了,”罗兰说。“该哭的人是我。”绝望需要时间,如果有一样东西他缺,那就是时间。他得在备忘记事本里找个空当把它塞进去。也许今年冬天他可以留出一个周末给绝望。
“
那你为什么不哭?”
他想了想。他所处的道德优势很有趣味。
但他哭不出来。这无济于事。电影有时能让他流泪。但极少。
“
我不知道,”他说。“就像我说的,我把它看成个刺激的故事。另一个男人。你。你们两人。赤身裸体。床。安全套。像是色情片,但不一样。所以,我哭不出来。”
“
真荒唐。”
“
具体是什么荒唐?”
“
你的反应。”
他上床前,去洗了个淋浴。他久久地冲着热水。然后,他要去睡了。回家的航班是明早的。他要思考,他要工作,他要给学生答疑,必要的话,温文尔雅地给他们以适当的嘲讽。他的幸福波澜不惊。他的幸福也就在于他自己的波澜不惊。
“
那我该如何反应?”
“
我不知道。这得看你了。你什么感觉?你有感觉吗?”罗兰想了想。他听见隔壁房间冲马桶的声音。感觉。一次聚会,有个同事——是另一个学院教伦理学的,告诉他:“你的行为让人觉得仿佛情感毫无价值。有点傲慢了。”
他不喜欢聚会。不等你回过神来,你就被那些连自己的情感都把握不了的伦理学家们团团围住了。或者是多年忽略你的教授们,喝得醉醺醺后,开始喋喋不休地发表不知所云的宏论。
“
他对熊先生说什么了?”罗兰问。
“
谁?”
“
那个男人。你的男人。他对熊先生说什么?”
“
他说:那只熊怎么回事?大概这个意思吧。他觉得我在床上放只熊很好笑。”
“
我敢说熊先生不喜欢这话,”罗兰缓缓地说,近于恍惚了。
“
我敢说,他压根儿不喜欢。”
原载于《世界文学》2011年第4期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经公众号责编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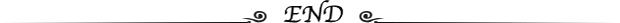
《世界文学》征订方式
订阅零售
全国各地邮局
银行汇款
户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户行: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账号:0200010019200365434
微店订阅

★ 备注:请在汇款留言栏注明刊名、订期、数量,并写明收件人姓名、详细地址、邮编、联系方式,或者可以致电我们进行信息登记。
订阅热线:
010-59366555
订阅微信:
15011339853
订阅 QQ:
3076719982
征订邮箱:
[email protected]
投稿及联系邮箱: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