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治·桑德斯:《林肯在中阴界》
文︱陈以侃
这下评诺贝尔奖的老兄们没有借口了。

乔治·桑德斯
可能你前两年正好走开,没有留意美国文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不但是个天才(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庆祝《无尽玩笑》出版的派对上跟大家说现在美国最激动人心的作家是乔治·桑德斯),而且是个圣人(都说他不只是个作家,觉得他写作时接通某种更高贵的性灵)。四部短篇集之后,今年2月,他终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篇,叫《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扎迪·史密斯读了之后发出上方的感想。1992年,乔治路过林肯葬下十一岁儿子的墓地,当时有人告诉他前总统曾两次打开棺木拥抱孩子的遗体。但这个意象太肃穆了,他觉得自己写不好,一直到2012年才说服自己动笔。小说到了天才手中气象一新,整本书由成百上千条独白构成,翻开来像排版很舒朗的聊天纪录,大部分是那块墓地里众多鬼魂的交谈,或长或短的几句话之后署上发言鬼魂的名字。
此处没法细谈,只能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质疑过我对一本书的质疑。一方面,叙述有种能量,简直像妖术,就算只是为了这份怪异,你也忍不住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另一方面,整个小说用的劲似乎和所谓的central conceit(或许可译作一个虚构世界的“三观”)不相协调;特别是到最后,乔治为了最后推高潮掏出的一个戏法,是如此任性地真善美,实在让我感觉像一个被强行扶过了马路的老太太。小说的力量,最根本来自于明知道是编的却还要相信:我们都很诚恳地想跟着作者作那“信仰的一跃”(Leap of Faith),这时在半空中如果作者突然从肚皮前的口袋里掏出竹蜻蜓或者传送门之类的东西,未免会让读者觉得所托非人。既然说好了,就不能想一出是一出,这种像是作者拍脑袋掉出来的机关,也有叙事学的术语,叫deus ex machina,指的就是以前舞台上把扮神的演员请出来解围的装置。
我并不支持,也从来没有支持过,黑人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两个人种间身体上的差异让我相信他们的共存永远不会是在社会和政治权利平等的意义上。……既然要共处,那么必然会有等级高下,我并不比任何人更加怀疑应由白人占据更高的等级。
因为近期最喜欢的一个叫做Backlisted的podcast里面,把《林肯在中阴界》和《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并列成让他们重新思考“小说能做什么”的当代经典,就把后者也找来读了。一开始的抵触情绪是想到多年前,为了求生从电气学院逃到英文专业,上来第一本布置要读的书就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一言难尽——这本书无趣到让我开始想念编程和挂科。大概也就几个月前,终于读到詹姆斯·鲍德温的一句公道话,他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小说,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只是用一种“这一切真是太可怕了”的态度写黑奴制度,那么对小说家来说就完全是失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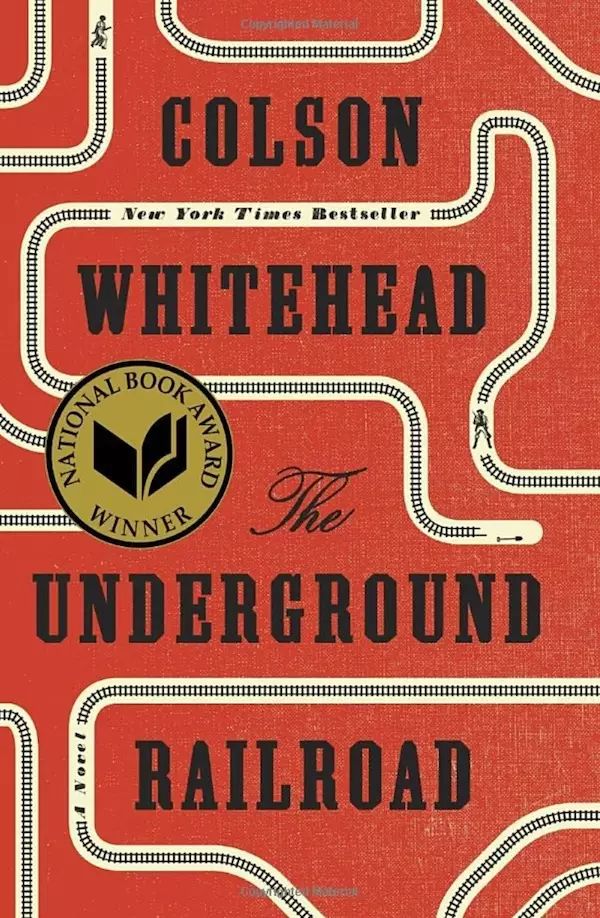
科尔森·怀特黑德:《地下铁道》
写黑奴写得好,恐怕是要下笔时能把那种骇人听闻和当事者的习以为常都收纳进来。上面引的这段话并不出自怀特黑德创造的某个丑恶人物,它是“解放者”林肯在当年一场辩论中表述的——可想而知,其他思想更落后一些的人抱持的是怎样的态度。读过《地下铁道》第一章,就觉得要不是奥普拉把它弄成了畅销书,我一定祝贺自己发现了一个文体家;在塑造残暴时,那种带着反讽的镇定和澎湃的洗练本身就算是惊心动魄。怀特黑德说他2001年听到有人提“地下铁道”,想起小时候曾误以为它是真实的,之后每写完一本书就会拿出来,但觉得自己写不好。2009年,他甚至写了篇《接下去该写什么》的文章,假装帮作家同行出主意,实际是讽刺了各种题材,其中就包括“关于黑人苦难的南方小说”,把它看做是黑人作家通往正经创作的练手材料。零零散散补了一些怀特黑德之后,就知道《地下铁道》又是一个作家才华可以驾驭任何主题的励志故事。
真实与现实是这样丰富、苛求,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对艺术责任的一种无趣的逃避。
麦克尤恩对《百年孤独》的不耐烦一直助长着我的某种气焰。上面这句话是他和扎迪·史密斯对谈时说的。扎迪认可,说此类写作有个标志,就是一种停不下来的能量,为了这种能量可以牺牲一切。麦克尤恩说,对,就像打网球不用网。怀特黑德那篇《接下来该写什么》的文章里,也嫌弃了一下魔幻现实主义:“对那些写不下去就要撕稿子的人,这是种完美的体裁——用魔幻现实主义,麻烦的角色只要凭空起一阵带火的龙卷风就能把他们捎走了。”麦克尤恩自豪于“我写小说从来没有给角色长过翅膀”;有些评论者说《地下铁道》奇幻,我一点也不认同,这部小说的力量全源自真实,要是科拉能变身,或者她娘能像桑德斯的小说中能“托梦”,那还有什么可看的。

伊恩·麦克尤恩:《坚果壳》
读完《林肯在中阴界》,彷徨,找了麦克尤恩去年九月出版的《坚果壳》(Nutshell),只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粗俗到没法接受荒唐的小说设定了。这部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还在娘胎里的哈姆雷特,偷听母亲和叔叔做爱、吵架、谋杀自己的父亲。麦克尤恩也知道很可能挨骂,他说自己当时参加一个关于自己作品的研讨会,无聊到走神,突然就在笔记本里写出一句:“我就在这里,倒挂在一个女人身体中。”小说改了那么多版这句话一直都留着,成了全书的开场。“一切都寄托在第一句话上,要是你接受不了一个胎儿正在跟你说话,那么把书放下就行了。”对于麦克尤恩,虽然我一直与“小说写这么完美,一定不是最一流的艺术”那一派的做作想法眉来眼去,但在悲壮的阅读速度允许范围之内,还一直尽可能多地读着他的小说。每一回都惊讶于完全被小说家操纵是如此醉人的体验——就技术而言,想不到当代有比麦师傅更出色的小说家了。
小说家的优势、奢侈,以及痛苦和责任,就在于他作为执行者可以尝试的事情是无限的。
我对《坚果壳》的喜爱,还是归结到这个道理,就是读者是最愿意上当的一群人;但即使是胎儿的第一人称,也有就此立下的“现实主义”束缚,我们的好意在于信你这份不容易。麦克尤恩谈小说的艺术喜欢提亨利·詹姆斯,说你总会回到大师,“詹姆斯说在读者和作家签下的合同里,只有一项预设必须接受,那就是作品的主题”。乔治·桑德斯的文集《脑残扩音器》(The Braindead Megaphone)里,也造了一个词,叫做“叙述表面逻辑依据”(Apparent Narrative Rationale)——“作者和读者之间就这本书是‘写什么的’所达成的默契”。“合同”似乎是麦克尤恩自己的说法,但大师的确反复强调,作者想写什么你必须先接受,“法国人把这叫做donnée”,就是他们用“给”的被动态直接指代一个作品的主题和设想。上面引的这句话出自大师名篇《小说的艺术》,也就是主题和预设作者说什么就是什么,读者只跟你探讨执行得如何。“我只有先接受了你的数据,才开始测量你。”

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
另一位和大师关系密切的小说家科尔姆·托宾,2009年来复旦,讲的题目是“小说的缘起”,主要就是说他如何十二岁的时候听到一个陌生阿姨跟母亲聊天,几句话的事情,潜滋暗长,五十年后写成了那部《布鲁克林》。小说家爱讲小说缘起,意思就是剩下的全是我编出来的,多了不起。麦克尤恩说小说开头总是很细微的东西,是纳博科夫教学生阅读时所谓的“摩挲细节”。大师把它称为胚芽、种子,在《博因顿的珍品》(The Spoils of Poynton)的序言里是这么描绘的:“那些走失的提示、游弋的字词、朦胧的回响,作者的想象为之触碰时会抽搐,如同被尖锐之物刺痛;有一个真相很美妙,就是它们的好处全在那如针一般极度细腻的穿透力。”
·END·

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