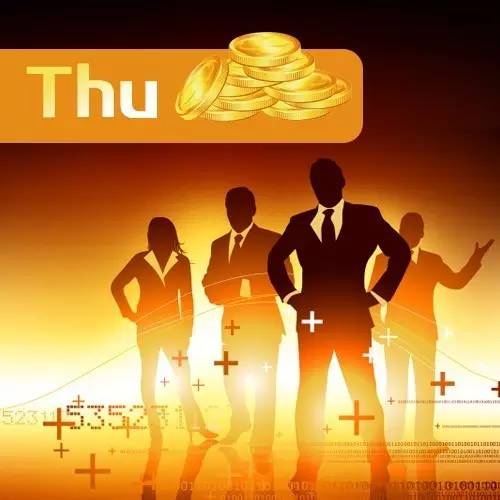正文
为什么文人骚客们会怀念《花花公子》创始人?不仅仅因为这本杂志是美国少男们的春梦指南,更是他们的品味圣经。不相信,请看他们对“电影界的莎士比亚”威尔斯的采访,看完你就会发现,他们要的不仅仅是肉体,更是“操灵魂“这件事情。
前两天,《花花公子》创始人休·赫夫纳过世的消息刷爆了各大社交媒体,理由不是他的那些长着俏皮尾巴、大胸长腿的兔女郎们,而是因为“反差萌”——这本杂志不仅仅是美国少男们的春梦指南,更是他们的品味圣经。
按道理来说,本来这种软色情杂志,定位就应该就是厕所读物,阅后即撸的卫生纸替代物,但《花花公子》明显志不在此,当年,它不仅以天价稿酬吸引了海明威、厄普代克这样全美顶尖的作家前来发表小说;更专门邀请各领域的学者,采访政治、艺术、学术圈的一票名流,内容也不完全是时尚杂志那种轻浅无聊的“你最喜欢的做爱姿势是哪种”,而是严肃到甚至有点苛刻的学术论文。
比如这篇
传播学宗师马歇尔·麦克卢汉的采访
,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其间各种箴言、学术讨论齐飞,更辅以称麦克卢汉为“ 流行文化的育儿圣手”(Dr. Spock of pop culture)这样有趣有料的段子。从中可窥见,《花花公子》是真的很严肃地对待“操灵魂“这件事情。
下面这篇是杂志在1966年邀请著名的英国剧评人肯尼斯·泰南,
对”现代电影界的莎士比亚”奥逊·威尔斯进行的采访
。这篇采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泰南所写的记者手札,在这里面他概括了威尔斯的生平,以及采访前后发生的趣事。如果你除了《公民凯恩》之外对这位大导一无所知,那么这段对你理解表演艺术界的达·芬奇,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第二部分则是两人就电影艺术、莎士比亚、生活在别处、好莱坞的各类谣传,以及威尔斯对他人评价的态度进行的讨论。不过不同于麦克卢汉那篇的深沉晦涩,本篇内容非常有趣,威尔斯甚至还透露自己16、7岁时,曾经和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希特勒一道吃过饭。
ps.有关这位剧评人,文末还有一个彩蛋,和
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田纳西·威廉姆斯
相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拖到最后。
记者札记
舞台艺术已经承蒙乔治·奥逊·威尔斯的专业照顾长达35年之久了——从1931年开始算起。当时他只有16岁,一到都柏林大门话剧院就敢自称是纽约著名演员,最后还真的成为了领衔主演。而就在前一年(1930年),威尔斯刚从伍德斯托克的一家男子学校毕业,就在一家美国报纸上登了求职广告:”奥逊·威尔斯——有货,有型,有量,年轻,璞玉一块........精力充沛,经验丰富,能力十足。”很明显,小乔治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树立其自己的品牌了。
威尔斯于1915年出生于威斯康辛州,父母都是中年得子。他的妈妈是位美学家、美人,并且在音乐方面才华横溢。跟着母亲,威尔斯认识了拉斐尔和斯特拉文斯基。而他的父亲,是个走遍全世界的赌徒,热爱明星——通过他,威尔斯接触了无数的演员、魔术师和马戏团的人。在奥逊·威尔斯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的丰功伟绩树立在20世纪中叶每一个娱乐行当之中。
威尔斯的目光投向哪门艺术,它就会臣服其脚下。第一个沦陷的是话剧,21岁时,威尔斯在纽约哈雷姆导演了一出全黑人班底的《麦克白》,之后又在水星剧院制作了《裘力斯·凯撒》,剧中开天辟地式全员现代装打扮,而凯撒则是秃顶复刻版墨索里尼。
全黑人版《麦克白》甫一上映,就获得了巨大成功,首映当天,看剧的人群挤满了马路。
紧接着,他征服了广播届,奥逊·威尔斯用H.G.威尔斯的《世界大战》庆祝1938年的万圣节,全美国人的血液都凝固了。(当时,威尔斯故意在广播时故意造成播音室已经被火星人入侵的假象,导致了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美40万人大逃亡,一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以为末日来临了——译者注)。
电影业成为下一个“裙下之臣”,他的处女作《公民凯恩》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好莱坞的地动仪仍然记录着这部电影留下来的震级,它教会现代电影了成人的词汇。在最近的全球调查中,《公民凯恩》仍是最伟大的电影。接下来的1942年,《伟大的安巴逊》再次证明,颠覆世界的巨匠已然降临。
1938年,威尔斯出席《世界大战》广播剧新闻发布会
威尔斯只要一接触哪门艺术,立马就成为顶级的大师,这是他的成功,也是其软肋。只要威尔斯的作品稍微有一点点没那么伟大,人们就会说他江郎才尽。
过去的20年里,威尔斯主要蛰居于欧洲,成为大多数表演艺术领域的“离群之恶象”。他或者出现于摩洛哥,捉襟见肘地拍摄《奥赛罗》;或者是在伦敦,把《白鲸》改成舞台剧;亦或是在巴黎一家残破不堪的火车站拍摄卡夫卡的《审判》;在西班牙,他还留下了一部至今未完成的电影《堂吉诃德》;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威尔斯到处演烂片赚钱糊口;甚至在好莱坞,他还导演了部震惊四方的沧海遗珠《历劫佳人》。
《上海小姐》结尾处这个镜子迷宫,竟然成为威尔斯一生最好的影像注脚
你永远没办法知道他下一次会在何时、在何地证明自己。在威尔斯的职业生涯之中,除了编剧、话剧和电影导演、演员这几重身份之外,他还是个小说家、画家、芭蕾舞剧美术师、魔术师、专栏作家、电视明星,以及业余拳击手。有一个颇具代表性,不过很有可能只是传闻的逸事这么说,威尔斯参加了一场粉丝稀少的聚会,说道:“难道有这么多的我,却只有这么少的你,这事不丢脸么?”
现在,威尔斯的身材像吹气球一样地膨胀起来,不管去哪儿,他都会带着自己硕大无朋的肚子,和一只巨型雪茄。只要威尔斯一出现,一定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哪怕是瞎子,也会被其山呼海啸般的笑声所震颤。
威尔斯在欧洲的第一个落脚点是罗马近郊的一间农舍,不过现在他和自己的意大利太太,以及女儿一道住在马德里郊区昂贵的宅子里。“我过去是个移民到意大利的美国人,”他说道:“我现在是个流亡到西班牙的意大利人。”
我去年春天在伦敦采访了威尔斯,当时他还带着彼得·塞勒斯(演员,代表作《奇爱博士》)。果不其然,威尔斯坚持要住伦敦最好、最贵的餐馆对面,这样他的客房服务就是顶级大厨给亲自操办的了,要知道这家餐馆每台桌子上的调料,都是鱼子酱。
当晚,威尔逊穿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僧袍,浅浅地咂着唐佩利农香槟王,侃侃而谈,直至半夜。
在晚年经常与威尔斯共进午餐的雅格洛,可以从这张照片看到威尔斯标志的僧侣长袍
之后,威尔斯很快就拍摄了法斯塔夫电影《午夜钟声》(本片在美国上映时就取名为《法斯塔夫》),还参加了戛纳电影节。不过不是所有的影评人都喜欢这部电影。有人就写到:“威尔斯搞不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需要减肥演大胖子法斯塔夫的人。”
不过戛纳和观众非常热情,他们还给威尔斯颁了奖,以表彰他对世界电影的贡献。别的电影人获奖时,也会有掌声和口哨,但威尔斯不一样,所有人——不管是先锋评论家,还是广告导演——都起身鼓掌,喝彩,长达数分钟。威尔斯则喜笑颜开,满头大汗地站在电影宫的台上,看上去像座融化的冰山,他还时不时地微曲身体,看上去勉强算是鞠躬。
之后,在酒店里,他告诉我自己下一部电影准备拍《金银岛》,自己会扮演独脚海盗西尔弗,接着还会完成《堂吉诃德》,再拍一部《李尔王》电影。后面还有一堆电影项目等着他呢,“蜜蜂,”他欢快地说道:“总是在酿蜜。”
访谈录
花花公子(下文简称花)
:你已经做了30年的名人了,别人对你的描述,哪个是最准确的?
威尔斯(下文简称奥胖)
:我不希望有任何准确的描述。我要大家拍我的马屁。我不觉得那些需要卖场喂饱自己的人会希望别人诚实地记录——至少书里没这么写过。我们都要靠卖票养家,所以需要的是好口碑。
花:
私下里,你听过最愉悦的评论是什么?
奥胖:
罗斯福说我会是个好政客,巴里摩尔说我和卓别林是在世最好的两个演员。也不是说我就相信这些夸奖,但你用了“愉悦”这个词。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夸赞我把不擅长的事情做得好。当一位老拳击手跟我说,你是世界上少有的懂拳的人,或是魔术师告诉我你魔术变得不错,这就正好挠着我自尊心的痒痒肉了,你不需要给给我票房,就会让我开心。
花:
所有的口头或是书面的评论,哪个最让你生气?
奥胖:
口头上的到没有。我比较在意书面上的评论——举个例子,沃尔特·科尔所写的东西(《纽约时报》记者,一直对威尔斯比较严苛)。我花了巨大的精力,告诉自己那些恶评都不是真的。我对那些印成铅字的评论有着天然的敬意,特别是负面消息。
我到现在都能记得自己18岁时在丹佛演戏,评论说我是“有着男低音的海牛”,这可是30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我现在还是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我从来都记不住好评,可能是因为这些坏消息离奇地伤人,这和我所处的行业有关,广播、话剧和电影,我们就是靠着别人的评论吃饭的,所以会非常担心这些差评影响到最后的票房。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是我玻璃心的辩解
16岁的威尔斯赶着驴车周游全世界,最后靠着大胆在爱尔兰谋得工作。
花:
说到评论家,你曾经说过:“他们不讨论我的作品,只是在评价我这个人。”你现在还这么认为么?
奥胖:
是——但是食得咸鱼抵得渴。就因为外界传的神乎其神,所以我挣得多,活也不少。但问题在于当我想要认真做某事,做些自己真正在意的事情时,许多评论家就没法就事论事,而是大而化之,只评价我。他们量产出威尔斯的文章,不论好坏,都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
花:
在什么都要细分专精的年代里,你却横跨了几乎所有的艺术媒介,你曾经想过只取一瓢么?
奥胖:
没有,我没法给自己设限,现在这个专家遍地的世界简直是操蛋,我觉得大家给其的尊敬也太多了。我一生中认识了四五位好医生,他们总告诉我现在的药还在开发阶段,自己几乎一无所知。我只认识一位伟大的摄影师——格雷格·图兰德(《公民凯恩》),他曾经跟我说,能在四小时之内教会我所有的摄影机知识——他也做到了。我可不相信这个时代他就只能当个破摄影师。
花:
那现在还能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一个人既是艺术家,也是科学家?
奥胖:
有可能,而且很必要,因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综合能力。我们需要把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拼贴起来,让它变得有意义。最神经病的一件事就是一条道走到黑。这不仅仅是对个体的人来说的,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你提供的道路越宽越多越好。要是一个普通的聪明人都没法学会的东西——前提是他天资聪颖,而且诚实好奇——那就不值得学习。举个例子,我除了能给你讲伊丽莎白时期的话剧外,还能简单讲讲核裂变的基础规律——生活在这个时代,会这个非常正常。我不会说:“这玩意儿太神秘了,留给科学家解释吧。”当然,简单讲讲核聚变也不意味着我就能去国家安全局捞个大官当当。
花:
二战后,你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外,你会称自己为海外侨民么?
奥胖:
我不喜欢这词。从小时候我就自诩为游历四方的美国人。“海外侨民”是个过气的词,让人想到1920年代的老古董,而且还把生活在别处给罗曼蒂克化了。我对这个词有偏见,但对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以后有很大可能,我就不当美国公民了。但原因很简单,你要是在欧洲开家电影公司,做个欧洲人更省钱。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没法为国服役,那为什么不挑个自己喜欢,而且活最多的地方呢?毕竟,伦敦满街都是匈牙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而美国更是全世界哪儿的人都有,你会管他们叫“海外侨民‘?
威尔斯在西班牙拍摄的《堂吉诃德》在其过世后,经过重新剪辑变成了电视节目。
花:
你选择生活在欧洲,是不是因为美国政府拒绝了你针对自己1946年百老汇话剧《80天环绕地球》票房惨败,而申请的减税?
奥胖:
确实,我的税负问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这不是我选择住在欧洲的理由。我待在欧洲数年,辛勤工作,就是想把自己欠政府的钱还上,他们不愿意把这笔损失一笔勾销,因为我的账填的乱七八糟。我喜欢住在欧洲;但我可不是个逃犯。
花:
你并是天主教徒,但却选择在两个极度虔诚的天主教国家——先是意大利,现在又是西班牙,为什么?
奥胖:
这跟宗教没什么关系,地中海文化更棒,没那么强的负罪感。任何一种天生没那么开心、没法笑看生死的文化,我都会待着不太舒服。这倒不是说我这是在谴责那些北方佬,那帮新教徒导演,比如英格玛·伯格曼。去瑞典玩很有意思,但伯格曼镜头下的瑞典,让我想起了亨利·詹姆斯形容易卜生笔下挪威的那句话——充满了“灵魂石蜡的体味”。这也太可怜了!
花:
如果你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和时间,还会是1915年的美国么?
奥胖:
这个选择在我的排行榜上位置也不是那么低,但任何人都希望生活在黄金时期的希腊,15世纪的意大利或是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还有一些其他的黄金年代,波斯有一个,中国有四到五个。现在,我们确实有着非常辉煌的时代,但这在我看来连白银年代都算不上。我觉得自己可能更喜欢出生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就算是出生在美国,那刚开始离开帐篷,建造房顶的年代,也会让我更加开心自在。
花:
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美国大人物的品格?
奥胖: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希望能拥有一些林肯的品格;但是,我没有。我没法想象自己如此伟大,如此热忱。我觉得自己身上唯一有的美国精神是托马斯·佩恩(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著有《常识》),他是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完全独立——不是在这个舒服的、自由的现代社会里,而是那个动荡的时代里,他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念进牢房。这是我的运气、优点、短板,但我别无选择。
花:
你父母在你6岁时离异了,之后跟着母亲四处游历,两年后她过世,你就和父亲一道继续周游世界,他也在你15岁时撒手人寰。对于这段早年云游八方的经历,你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
奥胖:
1926年之后的柏林非常美妙,我在那儿待了3年,芝加哥也有这么长的时间。但最好的城市肯定是布达佩斯和北京。那儿一直有最有趣的对话,最多的活动。但是我无法忘记1920年代奥地利的一场聚会,那时候我们一群男孩子一道旅行,由老师带着去了一家大型的露天啤酒花园。当时我们占着一个长条桌子,旁边坐着一群纳粹,那时候还没什么人认识出他们的疯狂本质。我被安排坐在一个身材矮小,性格晦暗的人旁边,他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但之后,当我再次看到他的照片时,我意识到自己曾和希特勒共进午餐。
花:
在你编剧和导演的许多电影里,主人公都是没有父亲的。我们队凯恩的父亲一无所知;《伟大的安巴逊》中乔治,毁了他的寡妇母亲,就是不让她改嫁。最新的作品《午夜钟声》中,男主角哈尔王子的亲生父亲,英国亨利四世,是个谋权篡位者。而哈尔的精神父亲,则是有你扮演的——
奥胖:
法斯塔夫。
花:
对。电影中这种对父亲的态度,跟你的生活有关么?
奥胖:
我不这么认为。我记忆里的父亲,非常亲和,独具魅力。他是个赌徒,也是个花花公子(虽然说相对来说,他当花花公子还是老了点)。我的父亲是个非常好的人,当他离世时我很伤心。不,一个故事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而非我可以顾影自怜。
法斯塔夫是莎士比亚最好的故事——不是他最好的剧作,但是最好的故事。父亲、儿子和法斯塔夫三者间关系的丰满程度,无可比拟。这个故事完全是莎士比亚原创的,其他的剧作总是从其他地方借来的故事,而它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莎翁向其吹了口气。但是没有哪部中世纪编年史曾经暗示过一点点法斯塔夫和哈尔之间的故事,这是莎士比亚的故事,法斯塔夫完全是由他编造的,他是戏剧文学里唯一一个既出色又伟大的角色。
花:
你认同W.H.奥登将他和基督徒联系在一起么?
奥胖:
我不会反驳,虽然我从骨子里反感“基督”这个词。我倒认为法斯塔夫是株用离经叛道装点的圣诞树。这棵树本身纯真又有爱,但相反,帝王家总是用王道之术装点它。他是个纯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花:
你认为《午夜钟声》会惹怒莎剧爱好者么?
奥胖:
无所谓,我一直都在改编莎士比亚的作品,我的其他莎剧改编电影也受到了同样的困扰。鬼知道这部电影会出现什么情况。在《麦克白》和《奥赛罗》中,我只是想把一部话剧编成一部电影,而《夜半歌声》之中,我尝试将五部话剧——《理查德二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融为一炉,改编成一部时长不超过两小时的商业电影。当然,我会惹怒那些自诩维护莎翁文本纯粹性的剧迷。但是对于那些承认电影是独立艺术的人来说,我还是有成功的把握。毕竟,当威尔第写《法斯塔夫》和《奥赛罗》时,没人会批评他乱改莎士比亚的话剧。劳伦斯·奥利维耶已经拍出了忠实的电影版本,我则是用莎士比亚的语言和角色拍自己的作品,它将会是莎士比亚戏剧主体的变体。
花:
下面我们来辟辟谣吧,有传言说你的电影一定会超出预算,是真的么?
奥胖:
假的,我不是个大手大脚的人。虽然有时候我的钱会赚的稍晚一点。拿《公民凯恩》作为例子,它花了85万美元,我也不知道直到现在为止这部电影一共赚了多少钱,但肯定是够了。这些盈利都需要时间,我又拿不到一毛钱。我拍的所有电影都没有超支。唯一的例外是在1942年《伟大的安巴逊》完成之后,我拍摄的一部南美洲纪录片。当时我义务受雇于政府,一分钱没拿,需要把成本控制在100万以内。但那是大制片厂的钱,不是政府出资的,制片厂在我花了60万的时候炒了我,理由是我乱花钱。这时候我的名声就臭了。大制片厂花了不少人力和物力保证这些个谣言能满天飞。
花:
还有一个谣言是你能预知未来,这是真的么?
奥胖:
好吧,如果真的有这么个超能力,我肯定是有的;如果不存在这么这种超能力,但我能让别人误以为我可以。我有的时候确实会告诉别人他们的未来将会在哪儿栽跟头——请理解我憎恨算命,这根本是好管闲事、危险,以及对自由意志的嘲笑——人类发明的最教条的玩意儿。
但是有一次我在堪萨斯城确实做了回预言家,当时我正在那儿表演一周的脱口秀。作为一名兼职魔术师,我确实见过不少半是魔术,半是欺骗的话中,也学习了专业的占卜。当时我在一个便宜的地方租了个小屋子,然后竖了块牌子——2块钱算一卦——每天我都会去那儿,包上头巾给人算命。一开始我用的是“冷读术”,这是一种镇住他人,并令其卸下防备的话术,这样他们就会敞开心扉讲自己的故事。
“你好,失败者们”奥逊·威尔斯会用这样的话来为自己的魔术秀开场
一个很典型的“冷读术”是告诉对方他的膝盖上有一道疤,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有一道疤,因为他们小时候肯定摔过跤。还有一个是告诉对方,他在12—14岁的时候,人经历过巨大的变化。但最后两三天我不这么做,只是和来访者聊天。
这时,一个穿着漂亮裙子的女人来了,她刚一坐下,我就说道:“你刚失去了丈夫。”她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并且潜意识帮我做好了推理,于是我就这么让自己的第一个想法脱口而出,情况确实如此。这时我就患上了算命的“职业病”,我们真的相信自己能“开天眼”了,这个想法很危险。
花:
最后一个问题,你已经见过许多伟大的男人和女人了,你还想见谁?
奥胖:
周恩来,纯粹出于好奇。
彩蛋
在《与奥逊·威尔斯共进午餐》一书中,提到本文作者泰南曾经写过一个段子,说是自己与田纳西·威廉姆斯受卡斯特罗的邀请,一道前往古巴参加国宴,切·格瓦拉也在现场。泰南因为会西班牙语,与卡斯特罗相谈甚欢,而觉得无聊的田纳西,则打着手势,操着一口美国南方口音,对格瓦拉说:”
可否劳驾你出去替我拿几个墨西哥肉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