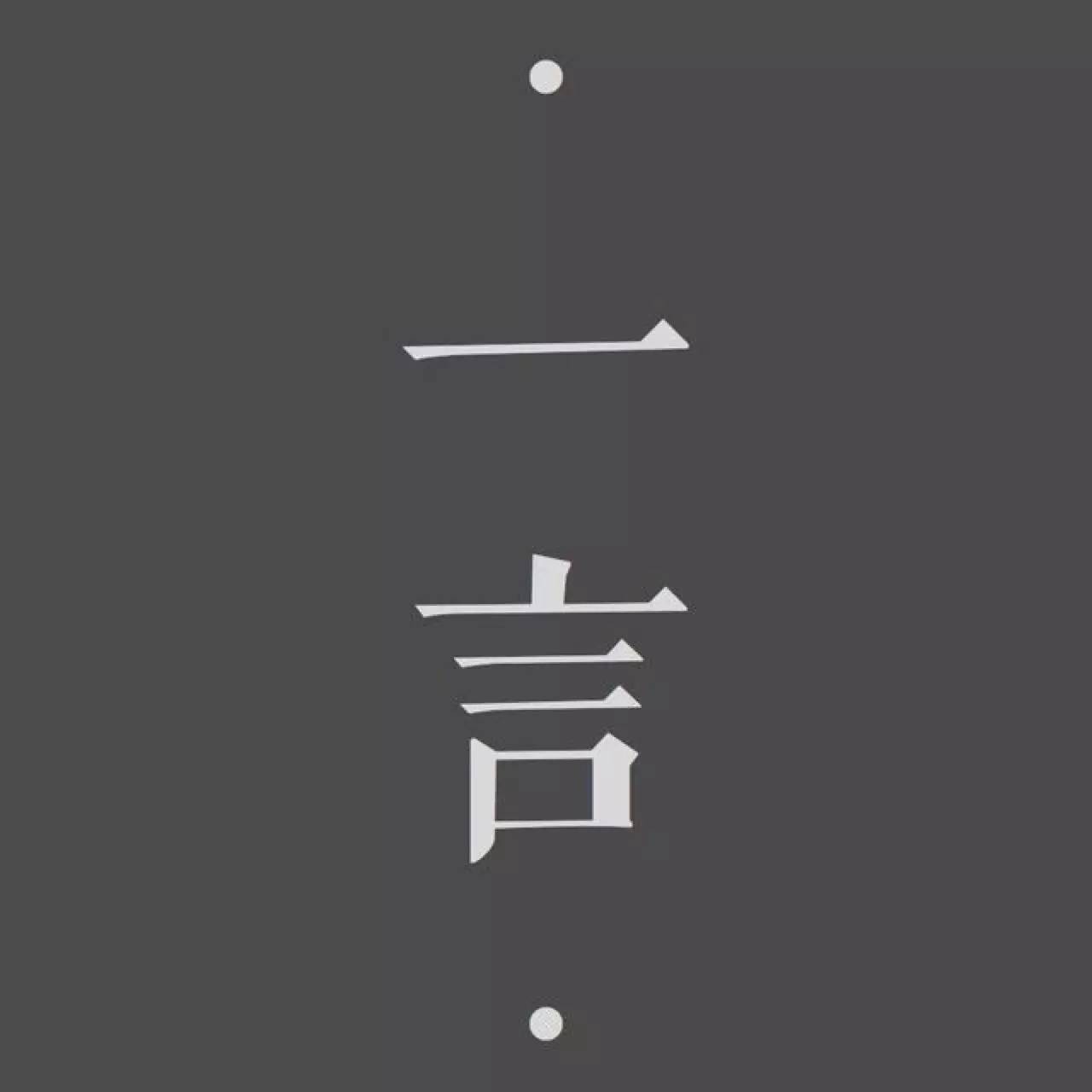作者: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内容提要
北约亚太化是美国固守冷战思维妄图遏制中国崛起而采取的重大举措。美国通过渲染和编造“中国威胁”话语叙事,为北约亚太化炮制理由。北约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推进亚太化路径:一是采取“北约+伙伴”框架,推进同日韩澳新亚太四国的深度合作;二是通过加强在亚太的军事行动和增加安全存在固化其亚太安全利益;三是以北约内部的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协调作为保障机制。尽管如此,北约亚太化面临成员国意见不一、亚太伙伴国利益诉求多元、成员国国内危机严重和美国内政外交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其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关键词
北约亚太化有着较为复杂的背景,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北约主导国美国固守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逻辑,妄图遏制和打压中国,以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就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并逐步推动北约亚太化,陆续推出“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等战略概念,并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经济和科技投入。此后,美国通过渲染所谓“安全威胁”推动北约亚太化,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北约峰会,以将北约影响力扩展至亚太地区。然而,北约亚太化也面临不少阻碍,对于亚太化战略取向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内部难以形成一致意见,且乌克兰危机导致大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内部危机加重。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出现的政治对立和族群撕裂等因素也影响北约成员国的政策选择。

2024年7月10日,美国华盛顿,北约峰会举行。
(Evelyn Hockstein/澎湃影像/IC photo)
美国推进北约亚太化的动机较为复杂,但其核心议题之一是应对中国崛起以及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国利用其话语霸权,不断在国际舆论场制造“中国威胁论”和“应对中国挑战”话题,强化“民主对抗威权”叙事,极力塑造有利于北约亚太化的舆论环境。
一是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与中国竞争的方方面面都纳入所谓挑战美国国家安全的叙事范畴,以凸显应对“中国安全挑战”的全面性和急迫性。美国泛化“中国安全”威胁与其对华战略定位密切相关,从2008年至今的数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华政策定位经历了从“伙伴”到“敌手”的转变。奥巴马政府对华定位由“朋友”向“中间地带”转变,特朗普政府从“竞争对手”向“敌手”过渡,拜登则将中国定位为国际体系内“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将“敌手”判断正式定型。在这种战略判断下,美国将包括经济与投资、供应链、太空、高科技、核能、通信、流行病、人文交流等统统纳入中国对美西方安全挑战范畴,炮制“中国安全挑战”无处不在的叙事。尽管美国极力渲染中国安全挑战的全方位性,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历次峰会公报,基本强调跨大西洋安全挑战而并未直接提及亚太和中国问题。然而,2019年北约伦敦峰会正式点名“中国安全挑战”,话语叙事开始紧跟美国,泛化亚太和中国安全挑战,美国持续经营的“中国全方位安全挑战”成为美西方“小集团”的叙事话语。
二是不断加码“中国威胁论”,持续塑造舆论环境。在美国主导下,北约从2019年开始逐步强化所谓“中国威胁”叙事。2019年12月,北约伦敦峰会发布的《伦敦宣言》强调,“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2020年12月,北约发布“北约2030”改革报告,称尽管俄罗斯在未来10年仍将是北约的主要对手,但北约“必须更加认真地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及其军事崛起”。此后,北约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2022年马德里峰会、2023年维尔纽斯峰会和2024年华盛顿峰会均不降调门,持续鼓吹“中国威胁”。通过不断加码“中国威胁”叙事,“中国威胁论”逐渐成为西方媒体、智库和主要舆论场描述中国的高频词,不断影响全球媒体和民众的对华安全认知。
三是进一步强化阵营对抗思维,将跨大西洋安全和跨太平洋安全捆绑。2021年6月,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发布公报称,“来自专制和专制大国的系统性竞争对我们的国家和公民形成了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试图破坏全球的民主”。《北约2022战略概念》则称,俄罗斯是北约“最大且直接的威胁”,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2024年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则诬称“中国持续挑战北约利益、安全、价值观,已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支持者,加剧了俄罗斯对邻国和欧洲—大西洋安全的威胁。北约正增强集体意识和准备状态,防范中方分化北约的胁迫策略与行动”。北约试图通过阵营对抗宣传,将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安全捆绑,强调中俄正在挑战西方的利益和秩序,为北约亚太化寻找借口。
四是扩大北约安全防范地域,强调亚太安全和北约亚太合作的重要性。拜登上台以来,北约亚太化步伐明显加快。2021年,北约出台“2030年议程”,宣布要“加强与亚太地区的长期伙伴——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的政治对话和务实合作,以促进合作安全并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同时强调北约安全的全球性,探讨“在北约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共同方法,通过更深入的政治参与分享观点,并寻求具体的合作领域以解决共同的关切”。2023年北约维尔纽斯峰会前夕,时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宣称北约安全“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北约“需要与印太地区伙伴密切合作”;2024年7月,斯托尔滕贝格又在北约华盛顿峰会上称,为应对中国构成的严峻安全挑战,北约须加大同“印太国家”接触,计划同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共同启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虚假信息和威慑中国相关项目,支持盟国同亚太伙伴举行更多海上演习。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则进一步渲染亚太地区紧张局势,充斥冷战思维和好战言论,涉华内容充满偏见、抹黑、挑衅。
从北约叙事来看,其强调的所谓“中国威胁”主要包含下列几层含义:一是北约面临的全球性威胁日益加重,尤其是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二是中国崛起使西方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利益受到挑战,必须将北约安全防卫覆盖到亚太地区;三是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安全利益密切相关,中俄挑战的不仅是具体安全利益,还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总之,北约试图通过多角度渲染安全威胁以为其亚太化铺路。

2023年7月12日,立陶宛维尔纽斯,北约峰会期间,韩国总统尹锡悦主持北约亚太伙伴领导人会议。
(최재구/澎湃影像/IC photo)
除了渲染所谓的“安全威胁”“安全挑战”为转向亚太造势,北约还采取实际行动持续推进亚太化,其采取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将亚太安全纳入北约集体安全战略框架内。北约有32个成员国,但也与40多个非成员国和国际组织保持着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网络旨在增强北约领土以外的安全。美国主导亚太伙伴关系网络,采取“北约+伙伴”框架,确保同亚太区域伙伴合作的弹性和空间,为北约亚太化打下基础。2006年,美国驻北约大使纽兰通过“全球伙伴关系”,与日韩澳新四个亚太国家建立联系国机制,扩大北约全球影响力。2012—2014年,北约与日韩澳新分别签署“个别伙伴关系与合作计划”;2014年,北约提出“伙伴关系互操作性倡议”,让非成员国能够参与北约军事行动,日韩澳新均加入该倡议框架下的互操作性平台,使北约在亚太的安全伙伴关系网络进一步制度化。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主导在亚太地区建立区域安全集团或合作平台,为北约亚太化夯实基础。2007年美日澳印四方安全会议启动,经过多年沉寂后,于2021年重启并日渐活跃。2021年,美英澳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连同冷战时期(1946年)组建的“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步建立多种“小集团”,通过与这些伙伴在传统安全领域尤其是军事领域合作来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
二是加强军事活动和安全存在,宣示北约安全关切。除了制度化同亚太伙伴的安全合作外,北约国家通过派遣军舰和航母、加强军事演习以及与亚太国家深化军事合作等方式,增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2021年,英国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赴亚太,并宣布在亚太地区永久部署两艘军舰。同年,德国派遣“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前往亚太。加拿大军舰近年来也多次在西太平洋地区活动。2024年北约华盛顿峰会后,在美国主导下,北约多个国家派武装力量参加在亚太地区举行的“环太平洋2024”军演,其中美意法英都派出了航母。同时,北约国家不断加强与一些亚太国家的军事合作。法国2021年与美日首次在日境内展开联合军演;德国2023年参加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联合演习,2024年与日本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2024年6月26日至8月2日,“环太平洋2024”联合军演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演习由美国主导,主题是“伙伴、融合、备战”,共有29个国家参加,基本由北约成员国组成。“环太平洋”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始于1971年,2024年是第29届,此次演习针对中国意图比较明显,也意在宣示北约在亚太的军事存在。
三是加强美欧在北约内部协调,为北约亚太化提供保障。作为北约迈向亚太的保障,美国积极强化跨大西洋涉华议题协调,以避免北约内部出现对华政策不一致或偏航的危险。2019年10月美军从叙利亚北部撤军、2021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以及当年9月宣布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相关举措削弱了大西洋两岸的信任。马克龙在2019年秋批评北约已经“脑死亡”。拜登政府从2021年开始致力于改善与欧洲伙伴磋商机制和政策协调,在欧盟委员会的提议下,美欧于2021年5月启动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协调机制。2021年6月北约峰会召开前,美国明确表示,总统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澄清北约对中国的立场。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峰会的目标之一是在盟国之间就中国问题达成“共识”。目前最具效果的机制是2021年6月15日建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美国和欧盟试图通过该机制在关键的贸易、经济、技术和安全问题上加强协调。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虽然是独立于北约而运行的机制,但考虑到参与协调对话的大部分是北约成员国,客观上有助于协调北约内部跨大西洋两岸国家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分歧。该机制自成立至今举行了六次部长级会议,在技术标准、供应链安全、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数据治理、威胁到安全和人权的技术滥用、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审查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协调,“在全面防范中国安全挑战上进行了深度协调,也努力夯实美欧在应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威胁上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北约亚太化的核心是增强与亚太地区新伙伴的关系,必要时将其纳入北约成员国框架,最终将北约集体防务安排扩展至亚太地区。冷战期间,北约盟伴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就有接触,随着形势发展北约与亚太四国伙伴关系日益紧密。20世纪90年代,四国与北约成员国参加了一系列联合国框架下的行动。2005年,四国都与北约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对话,但北约将其身份定位为“接触国”。2006年北约又进一步将亚太四国定义为“联系国”。2008年北约在布加勒斯特峰会提出与四国合作的“量身定制合作计划”(Tailored Cooperation Programmes,TCPs),其重点包括交流信息、参加培训活动、联合演习、情报和技术交流。2010年,北约里斯本峰会期间发布了新的战略概念,正式将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确立为北约的三大核心任务之一,明确表示“与全球任何国家和相关组织发展政治对话和务实合作”。2012年,北约进一步扩展与亚太四国合作领域,陆续与四国签署《个别伙伴合作计划》(Individual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Programme,IPCP)。2013年,北约开始在军事领域推进同亚太四国的合作。2014年,北约为让伙伴国家参与其领导的军事行动,提出“伙伴关系互操作性倡议”,亚太四国均加入该倡议框架下的互操作性平台。2016年北约加速与亚太四国政治接触,第一次在布鲁塞尔与四国举行政治会晤。2019—2021年欧洲北约盟国紧随其后,英法德荷等国开始发布自己的“印太战略”。这些战略中的大多数都指出“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跨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的价值和重要性。亚太四国在北约集体推动下,进一步深度融入北约军事合作框架。乌克兰危机爆发与升级,对亚太四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客观上推动了四国和北约关系的走近。在美国的推动和邀请下,四国政府首脑出席了北约2022年马德里峰会、2023年维尔纽斯峰会和2024年华盛顿峰会。2022年,北约与亚太四国谈判制定新的《量身定制伙伴关系计划》(Individually Tailored Partnership Programme,ITPP)。ITPP比IPCP更全面和详细,明确了特定国家与北约合作的具体领域和活动,并每隔几年进行一次进展评估。北约也试图重新定义与亚太四国的双边关系,以真正的“北约+亚太四国”的方式,而不是四个单独的伙伴关系,把这些伙伴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看待。为此,北约和亚太四国就一些优先领域达成一致,包括在新兴和颠覆性技术方面的合作、抵制虚假信息、维护海上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提高复原力、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理解/分享对全球安全形势的见解等。总体而言,在亚太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美国的大力推进下,亚太四国加强了同北约的协同合作,北约亚太化进而有了明显的战略支撑。

当地时间2024年3月16日,德国霍恩费尔斯,名为“盟军精神24”的军事演习举行。这次大规模演习由美国陆军主导,旨在加强北约和主要合作伙伴之间的互操作性和战备状态。(Daniel Vogl/澎湃影像/IC photo)
北约亚太化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北约强化“中国威胁”话语叙事,容易被外界解读为冷战的回归,这种论调不利于地区稳定,使得本地区国家更加感到不安,破坏各国正常的经济发展议程,更可能导致潜在的安全焦虑而使地区军备竞赛升级,进一步增加相关国家经济负担并干扰破坏正常的经贸活动,这种情况最终会影响美欧在该地区经济利益,也增加北约盟伴的预算负担。北约亚太化面临重重挑战,其前景充满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