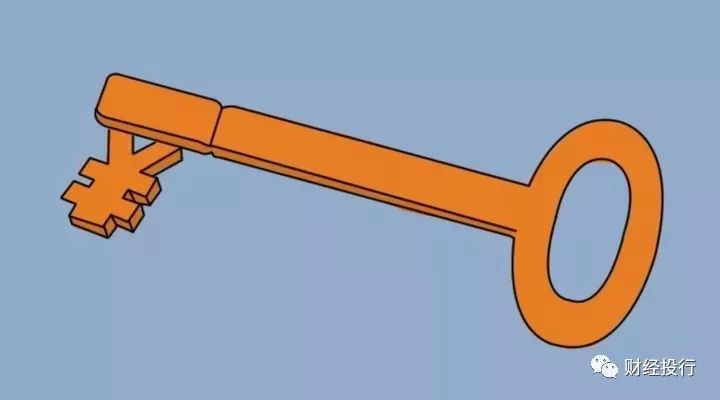
先说结论
:
❶ 幸福取决于频率
,
而非强度。再大的单次幸福事件
,
持续的时间也不会比较小的多太多
;
❷ 财富取决于单次的幅度
,
而非频率
;
❸ 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
,
决定了你此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1
诗人别涅季克托夫,是第一本俄罗斯数学难题集的作者。下面是他出的题:
三姐妹各自卖鸡蛋,分别有10个、30个、50个,要求:
1、任何时候共同销售价格;
2、最终每个人收到的总钱数一样多;
3、卖十个鸡蛋的总钱数不少于10分钱,卖90个鸡蛋的总钱数不少于90分。
请问如何卖?
这道题符合我对“好题”的定义:
1、无需复杂的公式或记忆型常识;
2、令人产生错觉(并因此校正人的直觉);
3、能够解释现实中的一些关键性难题。
再看个欺骗性更强的题目:
斯坦福讲义里的例子:某大学历史系和地理系招生,共有13男13女报名。
历史系5男报名录取1男,8女报名录取2女。地理系8男报名录取6男,5女报名录取4女。这些数据给出一个令人迷惑的结论:
1、每个系的女生的录取率却都高于男生录取率。历史系女生的录取率(2/8)大于男生录取率(1/5)。地理系女生录取率(4/5)也高于男生录取率(6/8);
2、整个学校统计,男生录取率(7/13)高于女生录取率(6/13)
当然本文不打算陷入趣题求解,解题能力未被证明有益于幸福(尽管我在不幸时常以题解忧),如开篇“好题”定义之三:能够解释现实中的一些关键性难题。
关于第一题“卖鸡蛋”,尽管任何时候必须执行相同的价格,但鸡蛋少的姐妹,可以
在价格低的时候少卖鸡蛋,而在价格高的时候多卖鸡蛋,
从而实现同样的总销售额,请您自行验证(或者让一个学奥数的小盆友帮你)。
关于第二题“录取率”,倒过来想容易很多,历史系女生被淘汰6人,男生被淘汰4人。地理系女生被淘汰1人,男生被淘汰2人。
男生在基数较大的地理系申请人群中,绝对录取数更多,从而令整体淘汰率更低。
02
财富取决于较大的幅度
如上所述。
在关键环节下大注,能够让你在拥有相同或较少鸡蛋时比对手赚更多钱。
“我从(乔治·索罗斯)身上学到很多,但可能最为重要的并不是你是对还是错,而是
在你正确时你赚了多少,而错误时你赔了多少钱。
”基金经理人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说。
事实上,当年狙击英镑狂赚10亿的创意及操盘者,皆为德鲁肯米勒。那么,索罗斯做了什么?
德鲁肯米勒在演讲中称,当时索罗斯所做的交易中,约90%都是他的点子,但索罗斯比他“更有胆”。
在那个“索罗斯大战英格兰央行”的传奇故事中,德鲁肯米勒的15亿美元押注即将到期兑付,正考虑进一步增加头寸拨备,甚至建议把所有钱都押上。索罗斯称,这“太荒谬了”,“你知道这种事情多久才能出现一次吗?”
“信心十足但是只投入很小头寸,这么做是没有道理的。”索罗斯说。最终他们加上杠杆,押上了100亿美金,并大获全胜。
索罗斯的策略是:“专攻要害。”索罗斯敢于下大注于狙击英镑,是因其判断:假如错了损失不大,假如对了能赚不少,而且对的可能性大很多。
索罗斯获取利润的另一秘诀是:投资在先,调查在后。
提出假设,建立头寸,小试牛刀考验假设,等待市场证明正确与否。
若正确则追加头寸,否则及时撤出。有时候确认一个走势相当费时,很可能犹豫不决之际市场已开始逆转。“提出假设后立即建立头寸”,有助于其抓住最佳投资时机。
巴菲特曾说,每个投资人都应该假设自己手中只有一张可以打个20个的投资决策卡,每作一次投资就在卡片上打一个洞,用完为止。
很多投资频繁买卖,挣点小钱,期待积少成多,但总体盈利不多。一旦市场下跌,全贴回去了。文艺复兴基金的高频交易,虽然看起来是“极高频+细微套路”,但核心是算法,而非高频。
巴菲特在2010年写给股东的信中写到:
“好机会不常来。天上掉馅饼时,请用水桶去接,而不是用顶针。”
用水桶去接机会,不是人人都会,人人都敢。
2008年9月金融危机的最悲观时刻,巴菲特用超级大盆抄底,巨额投资先后超过300亿美元。但到年末,公司市值缩水115亿美元。到2009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净值增加218亿美元。
抄底总是嫌早,股神也不例外。
巴菲特1973年买华盛顿邮报不久便跌二成左右,1988年股灾后买入可口可乐不久下滑30%。最近的例子,巴菲特从2011年3月份开始买入IBM的股票,平均每股成本近170美元,后来股价跌至143块。同期标普500大涨约60%。但巴菲特依然继续加仓。时至今日,巴菲特说:我错了。
你会跟股神下大注去抄底吗?毕竟,巴菲特的舞台,是二战后持续60余年的美国大牛市。假如这超级牛市不再呢?
我戏称索罗斯和巴菲特是“索菲特”:
他们都是那种伺机而动、咬住就不放口的致命性攻击动物。
这固然令人生厌,然而,人类社会的某个底层逻辑,依然是丛林法则。
成功投资了facebook、京东等公司的米尔纳,其核心策略是:
贵精不贵多、大手笔押注、尽早入场并以巨额回报为目标。
过去五年,米尔纳的团队审核过全球250家公司,只对其中一小部分下了大注。
麻省理工学院前教授丹·艾瑞里在《怪诞行为学:可预测的非理性》研究:人们在面对多个选择时,即使明知其中一项可以获得最大成功,他们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其他选择。
专注,聚焦,可能是最众所周知、又最难实现的。
尤其对于聪明(但又不够那么智慧)的人。
而彼得·蒂尔推崇幂次法则:
一小部分的公司完胜其他所有公司。
而撒大网的投资者因为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仅仅几个日后价值势不可挡的公司上,就会与这样的稀有公司失之交臂。
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家总结出了两个很奇怪的规则:
● 第一个规则:只投资给获利可达整个投资基金总值的有潜力的公司。如此就将大多数可能的投资消除了。
● 第二个规则:因为第一条规则太严苛了,所以不需要其他规则。
高瓴资本成立后,张磊把从耶鲁大学投资基金筹集了3千万美金,大部分都投给腾讯。
随后他投资京东。张磊认为京东是“亚马逊 +UPS国际快递”。刘强东本来想要7000万美元,张磊答:“你如果只要7000万,我就不投了,要投就投3个亿。”
张磊就是彼得·蒂尔眼中那些懂得幂次法则的投资者:
他们所列的投资标的会很少,因为最具特色的公司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公司会胜过其他所有公司。
真理往往有两个特点:1、很简单;2、没有操作指南。
一个真理可以用另外一个真理去解释,但另外一个真理还是没有说明书。你可以持续地用另外一个真理去解释,直至如贪食蛇般解释回最初的这个真理。
“机会来临时敢于下大注。”
——需要两位天才方能使用这一真理:德拉肯米勒负责发现机会,索罗斯负责下大注。
我等凡人,如何下这类大注呢?
03
幸福取决于较高的频率
出版的畅销书《哈佛幸福课》的哈佛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说:
虽然这些因素能让人变得更幸福,但它们所起的作用之轻让人意外。没错,一套新房或一个新配偶确实能让你更幸福,但这种新增的幸福感并不多,也持续不了多久。
其实,人们并不清楚哪些事物能让他们更幸福,以及这种幸福可以持续多长时间。他们既高估了积极经历对提振心情带来的影响,也高估了消极经历对压抑心情带来的影响。
最近的研究发现,很少有经历能对我们产生超过3个月的影响。当好事来临时,我们会庆祝一阵,然后冷静下来。当坏事来临时,我们会哀嚎一阵,然后振作起来并接受现实。
简而言之,好的事物好不了太久,坏的东西坏不了太久。
吉尔伯特进而总结道:
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最能影响我们的是生活里的一两件大事,但幸福似乎是上百件小事叠加的总和。一个每天经历十几个小开心的人,很可能比只遇到一件大喜事的人更幸福。
心理学家埃德·迪纳研究发现:
快乐体验出现的频率要比快乐体验的强度能更好地测量你的幸福感。
奚恺元在《别做正常的傻瓜》提及了一个概念--适应性偏见:
人们常常低估了自己的适应能力,从而高估某些事情在一段时间之后对自己的影响。
事实上,人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而且是一种完全超乎想像的,惊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他举例说:公司奖励,两个选择,要么可以把他们现在住的120平米的房子换得更大一些,换成150平米;要么可以带着他的爱人在今后的10年里每年都到国外旅游一次。
你选哪一个?
奚恺元认为,换一个比较大的房子可以带来一时的开心,但这种开心往往维持不了多久。
但每年一次出国旅游,他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地方,体验不一样的异国风情,人们一般不会对不同的旅游地点感到厌倦。而且每次旅游回来后每当翻看旅游时拍的照片,和爱人一起回忆起旅游的经历的时候,还是会感到非常开心。
考虑到这本书出版于2006年,这十余年间的房价血泪史我们就不提了。但奚教授的观点仍值得我们自省:
我们忽视了适应性效应,对物质性的东西看得过重。
这或许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证了房价高企的原因与荒谬所在。
性和金钱,强欲望的东西,高潮总是短暂。碧桂园的杨国强好像说过,财富带来的幸福感,其实非常短暂。
看起来,幸福和财富似乎是两件不相干、彼此间有矛盾的事情。
但是在2017年后,身处一个极度焦虑的时代,面向迫切需要答案的读者,我必须飞刀脱手而出,鸡汤倾盆而下。
04
几个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