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写作可能已经从某个层面上具有了被迫的意味,弗兰兹·卡夫卡感到一阵惊讶和悚然。

▼ 本文由豆瓣用户@不流 授权发布 ▼
1920年9月的星期三早晨,弗兰兹·卡夫卡醒来了。
昨晚的睡眠是近日以来最好的一回,所以当胸部的隐痛牵连着头部的搐痛在他眨眼的时候渐次浓烈时,他又陷入到对白天的厌倦感里。一切仍旧是老样子,他想,再深沉的睡眠也不过是夜晚的一个小小骗局,晨曦透过窗帘的缝隙,轻易就揭穿了这个骗子[1]。
窗帘关着。在昏暗的光线里,他看不清楚远处的房门。是的,他觉得门在远处,由于疼痛、虚弱和对初秋微凉的早晨的些丝拒意,掀开鸭绒被、穿上拖鞋走到那门,几乎成为了近日以来最为困难的事情。
母亲来敲门了,卡夫卡抖嗦一下,从被子里坐起来,朝着门喊:“您稍等一下,我已经起来啦!”他说这句话的时刻习惯性地卡在最为恰当的点:可以让母亲听清自己说的,并以此阻止她推开门走进来或者看进来。这并非是说他不想见到她,而是对于每一回从睡眠中来到现实,他都感到要重新认识整个布拉格,这是一件让他觉得艰巨的事情。
当然,即便不费多少力气,他也可以快速在头脑里重现自己已经生活于兹三十多年的小城的样貌,那些建筑的线条、墙壁在秋光下的反射、条石路面早已被踩踏光亮的模样,甚至是雅各布教堂中铁链悬挂的贼之手臂的皱纹、查理大桥被雾摩挲湿润的扶手、圣维特教堂的尖顶刺破城堡区的树林向阴沉的天空聚焦的画面……
晨起的真正困难是,他得小心翼翼地、快速地复原所有的记忆,并带着这个庞大的看不见的行囊走出房间,去到工伤事故保险局或者任何其它需要他去的地方。在这种感觉下,面对母亲,他已经没有力气表达出合宜的耐心和爱意。
卡夫卡吃完早饭了,他起身走到窗边,注视着还没有多少行人的街道。还有几分钟,就得出门去工伤事故保险局的办公室,今天,对座的特雷默尔休假旅行去了,他将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度过整个上午,想起这件事,他感到轻松一些,甚至有一点微笑地转回客厅提起公文包,准备出门。但在离开前,他想起雅诺施{2},犹豫了半分钟左右,回身到写字台前,在三摞皆约半米高的书里查找,他找到了,新一期的《新评论》和《树干》杂志,后者中刊登的几首诗里有一首,他觉得有必要备在手边,在小伙子雅诺施下次来时(下次也许就是今天,他来找他全凭自己方便和一时兴起),让他读一读。末了,他又从文件夹里抽出刚完成的《波塞冬》手稿,约摸着如果今天不是很忙,可以再做做修改。然后,他出门,向办公室走去。
走过查理大桥时,他的速度会慢一些,虽然以现在的体质,他总会在伏尔塔瓦河薄似轻纱的水雾中咳嗽起来,但缓慢走过查理大桥,已经是他的习惯了。自他对布拉格真正的街道和建筑有印象开始,查理大桥就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喜欢伏尔塔瓦河的水流穿过脚下的桥孔,恒久地向一个方向运动,怎么会有这么无穷无尽的水,你可以放心它一直流淌而不干涸呢?它流到哪里去了?仿佛布拉格只是这个运动的大地绳子上的一颗珠子,也是一个笼子,关住一只叫卡夫卡的寒鸦的笼子,当飞出笼子已经没有什么可能的时候,剩下的就只能是仔细观察它那些栅格的纵横交错了,不远处老城区的街道也正是这样旋转着交错着的。所以,有时候也可以说,每天醒来重新记起和认识布拉格,也并非一件坏事,总是有新发现的机会,即便发现过去已经知晓的东西,在每一个发现它似曾相识的时刻,也仍然是新的。自从打梅林地疗养回来,他也在尝试更积极地去观察这座小城。
到达办公室之后,卡夫卡还在延续着自查理大桥上带来的思索,所以把公文包放到桌子上,他并没有立刻坐下来,而是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此刻,他已经联想到了锤子和园艺铲子,他一只手在裤边不自觉地轻轻摩挲,另一只手略抚面庞和下巴,时而压住薄而坚挺的嘴唇。锤子和铲子,对金属的改造与对泥土和植株的养护,一直以来是他的兴趣,如果能选择不做一个暴躁富商的儿子的话,或者这缠人的肺结核病魔离身的话,铁匠和园艺师倒真是最理想的工作选择,正想到这里的时候,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是雅诺施。
雅诺施的脑袋伸进来快速巡视一圈,伴随着还未停下的气喘吁吁和泛红泛汗的脸,有点断续地问:“博士先生{3},就您一个人吗?”
卡夫卡回答:“是的,雅诺施。”
“太好了!”雅诺施莽莽撞撞地随手啪的一声关上门,径直冲到卡夫卡办公桌边的椅子上坐下来,简直可以说风风火火,卡夫卡有点不适但仍克制好自己没有表现出来,第一次见面时那种少年的腼腆因为逐渐相熟早已无存,卡夫卡想着,如果不是因为他还是个不太更事的年轻人,这种鲁莽将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难受和担忧。
雅诺施把包提起再啪的一声放在桌面上,解开纽扣,掀起布盖,然后两手拎起包的两个下角,哗啦啦,把一堆书倾倒在办公桌上,他说:“博士您看,我又买了好多书,我打算接下来两个月就全部读掉!”
卡夫卡蹙着眉,但仍保持可辨的笑意:“要我说,亲爱的雅诺施,您读得太多了,而且我注意到你买了很多新作家的书。”
雅诺施:“也许您是对的,博士先生,但是您上次批评我的诗,说它们太喧闹了,我想,也许多读些书可以让我安静一些。您不这么认为么?”
卡夫卡:“亲爱的雅诺施,这样吧,我正好在《树干》杂志看到一首诗,打算给您读一读。”卡夫卡坐进办公椅,对于一般人来说尺寸适宜的椅背,却在他高大的个头下显得局促狭小。他从包里掏出那几本书,然后把《树干》抽出来,翻到首页的四首,把右手修长的食指压在那首《谦恭》{4}的标题旁边,然后左手旋转书本,那首诗就像以他食指为中心转出一个优雅的圆圈儿,以漂亮的落舞姿势停在观众(雅诺施)面前,等待掌声。
雅诺施伸着脑袋,并不自觉地读了起来:
我越长越矮,越长越小,
变成人间最矮小的人。
清晨我来到阳光下的草地,
伸手采撷最小的花朵,
脸颊贴近花朵轻声耳语:我的孩子,你无衣无鞋,
托着晶莹闪亮的露珠一颗,
蓝天把手支撑在你的身上。
为了不让它的大厦
坍塌。
卡夫卡观察着、聆听着雅诺施的朗读,他欣赏他在诗的面前既热情又宁静的状态,这也许是他能和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年轻人交往而不觉得特别难受的原因吧。实际上,与这样一位年轻的诗人(或者说文学爱好者更为确切)的交往总体来说是安全的。不是指通俗上的安全,而是从对“孤独”影像力度来说,雅诺施虽然时常莽莽撞撞,但并不会追根究底,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能看到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和自己相似的悲剧意识。卡夫卡早已深刻体会到在通俗情感和生活的角度,与在写作的角度进行选择时的困境,他甚至可以很直白地下结论说:保持孤独的状态,是对于写作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每念及此,他禁不住想起自己每一次在最后关头解除婚约时的痛苦,以及不久后又一而再地跌入爱情中,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条永久运动的情感河流,他体内的伏尔塔瓦河。他甚至能预感到雅诺施一生将会在痛苦中度过,这与对他自己的前景的预感很相似。只不过,自己可能很快就要抵达那个灰暗的结局了。
“亲爱的雅诺施,您得一个人待一会儿了,我要去办个事情,不过保证会尽快回来的。”卡夫卡说。
雅诺施还沉浸在福尔克的诗句里,恍惚间应了一声好,在卡夫卡走出办公室的当儿,他入迷地翻阅着这一期杂志,想找到更多好的作品。
接下去的一个小时左右,年轻的雅诺施先是翻完了《树干》上感兴趣的内容,然后又去翻了翻那本《新评论》,并且发现了《波塞冬》的手稿。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卡夫卡的手稿,优雅流畅的手写体很吸引他,他很快就读完了,并且又读了几遍,直到红胡子赫尔托夫(他父亲的助手)推门进来打断他:“您好,雅诺施先生,卡夫卡博士让我给您捎个话儿,他在查理大桥那头等您,他说为了表达让您等候的的歉意,他将请您在老城咖啡馆吃午饭,这不也到了午饭时间嘛!”
雅诺施在桥头塔楼下见到了卡夫卡,感觉到与他在办公室里的样子差别很大。使用多年的办公室并不很宽敞,光线也不好,卡夫卡高大的个子在里面永远都显得有些过分醒目。而在老城街头的卡夫卡,则显得孱弱不已,他修长的身材、精灵般的眼神都在更大尺度的城市建筑的狭缝中被压扁了,再加上暴露在室外空气里,让他忍不住频繁地咳嗽,让雅诺施跟着忧虑不安起来。也许我该走了,我不应该老是缠着博士先生,而让他获得更多的休息。
卡夫卡看出了雅诺施善意的犹豫,用手拢住两声咳嗽,等它们过去,尽量挺直身体,用修长、灵巧得让人羡慕的手势辅助语言,说服雅诺施和他一起吃午饭。“我们还没讨论完诗歌呢,雅诺施,难道您不想听听我的想法么,关于读书这件事情?”像之前每一次一样,雅诺施留下来了。
饭后在老城区环形岛上散步,他们继续着刚才的讨论。雅诺施说:“我可真没想到您会喜欢狄更斯。”
“为什么不能喜欢他呢,雅诺施?恰恰是他的作品里那些饱满的善良和希望的光泽,是我们这样的作家们缺少的呀。”
“但是,您不觉得希望和善良如此虚妄不真么?现实残酷多了,仿佛上帝已经不再照看我们了。”
“我们不该自己照看自己么,虽然这很艰难。”
“嗯,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的那样……”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早已讨论过了,雅诺施,我更想建议您去看更早的经典作品,比如福楼拜,如果您也认同寻找文学上的宁静和坚定是如此重要的话。”
“博士先生,那您怎么看待那些新的文学呢,您不觉得它们很有趣么?它们难道不是已经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么?”
“亲爱的雅诺施,如果说有什么新的事情会发生,那一定不会发生在文学上,您应该再读一读歌德,伟大的歌德,我们只不过在以某种方式重复他而已,而您要知道,在文学里,形式永远都不重要。”
“那什么才是重要的?”雅诺施问,旋即补充道,“如果形式不重要,您为什么写《变形记》呢?”
他们已经走到了老城广场,来到胡斯雕像下面,卡夫卡抬头看着雕像的面孔,却因为涌来的咳嗽而弯下腰。等痛楚过去,他对雅诺施说:“既然您提到了它,亲爱的雅诺施,我想说它可能是我最糟糕的作品了,并且,您稍微细心一些的话,也许会发现,它一点儿也不是并且不在乎是不是新的,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更老的、更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持久性的东西。亲爱的雅诺施,这也是阅读歌德的意义。”
“我上午恰好看到了您的手稿《波塞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很喜欢那个故事,海神忙碌得没有办法巡视海洋,我想,您是通过修辞达到永恒的吧!而且,波塞冬一定是您的自我写照,我知道您对工作也早已厌倦了,这太明显了!”
“还记得《谦恭》么?对于永恒,我们只有愿望,通常来说,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对于永恒,我们是矮小的。至于您说的厌倦感,我不能否认,但对于矮小的花束来说,他又如何有资格厌倦草原呢?”也许是由于身体不适,或是由于觉得这样的对话已经在羁越某些界限了,卡夫卡提出了告别:“亲爱的雅诺施,和您在一起是如此愉快,但是抱歉,我的身体要求我回到家里去了,我们下次再谈吧。”
他们在城堡区圣维塔教堂入口的空地上分手,各自回去了。
弗兰兹·卡夫卡从黄昏时开始,躺在床上睡去了。在入睡前的那片时间里,他试图忽略掉疼痛而专心睡觉,但是越是抛除想法,宁静的房间里,就越发出在睡的制辖之下的巨大噪音。弗兰兹·卡夫卡,在布拉格九月黄昏的暗光逐渐昏然的过程中,试图进入睡眠,试图通过睡眠掩盖一种持久性的无奈感,这感觉几乎由生活中一切的东西在参与构成,如对工作的厌倦、对与人沟通的担忧、对持久性岌岌可危的害怕,也包括对自己短暂而黯然的未来生活的无能为力,等等。
弗兰兹·卡夫卡,终于睡着了。而他本来打算今夜继续写作的想法,也因为这一回的睡眠过长而没有达成。在次日早晨醒来的时刻,他的疑虑又加深了一层,他在想,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今天比昨天更绝望么?今天比昨天更疼痛嚒?今天被迫要写昨天没写的东西么?意识到写作可能已经从某个层面上具有了被迫的意味,弗兰兹·卡夫卡感到一阵惊讶和悚然。
弗兰兹·卡夫卡也同时感到饥饿,恰在这时,母亲又敲响了房门,宏大的声响,让他止不住垂头哭了起来……
[1]卡夫卡曾写作《揭穿一个骗子》,收录于他的首部作品集《观察》(1913年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
[2]卡夫卡同事的儿子古斯塔夫·雅诺施(1903-1968),后来的《卡夫卡谈话录》作者。
[3]卡夫卡获得过法学博士学位,在工伤事故保险局从事法律咨询方面的工作直到最后提前退休。
[4]捷克诗人基里·福尔克所作,1920年9月刊登于《树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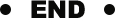
本文版权归 不流 所有,
任何形式转载请点击【阅读原文】联系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