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送:
2019年01月书单
本月读书21本,有好多本是重读,还有9本小说。当写总结书单时忽然觉得,这些书其实绝大多数都说的是同一件事,我在寻找着一个主题。
这次写得很认真,一万三千字,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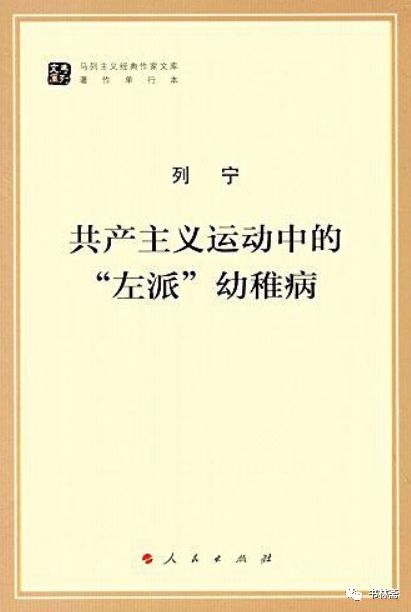
为什么很多问题撕扯不清楚呢?因为撕扯这些问题的双方,经济基础来源本质上是一样的,再仔细一点,很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有的是偏左一点,有的是偏右一点,有的狂热一点,有的保守一点,本质上没有差别。
都不事生产。于是小资产阶级是通过读书了解这个世界,他们会从书本的阅读中形成一套自洽的逻辑,在推理上攻不可破,但只要实践,立刻就会变成马蜂窝。
「
这岂不是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
」

周天子为什么是周天子?因为他是周天子,这是不容置喙的。秦始皇为什么是秦始皇?因为他统一了天下,这是无法反驳的。
那么汉家天子为什么是汉家天子呢?周分封也好,秦郡县也好,本质上他们都是五帝之后,天然具有法统。刘邦不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汉家天子很久,终于他们从故纸堆里发现了一个叫儒家的存在,又从中看到了《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对合法性的建构具有极强的魅力,这时经学就正式确立了地位,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不过无论是儒法之争(盐铁大会)还是《谷》《公》之争(石渠阁会议)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看起来总算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但世界形势是会发生变化的,一会儿匈奴来了需要「
大复仇
」,一会儿刘秀登场需要谶纬学说,再加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终于开始正式撕扯起来,合法性基础就如同托勒密体系,一次次地为了修正模型以适应新的观察结果,最后这个模型异常复杂,它叫做《白虎通》。
这个时候,桓谭和王充的存在就显得异常珍贵了。不过,珍贵与否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是主流,而主流是谁呢?是叔孙通、是陆贾、是贾谊、是董仲舒、是司马迁、是刘向、是刘歆、是马融、是何休、是郑玄。
郑玄是两汉经学最后的集大成者,也是汉帝国最后的余辉,当他完成这件事时,经学走到了尽头,汉帝国也走到了尽头。再之后呢?再之后晋武帝以孝治天下,可是没有人相信,那时虚无的玄学就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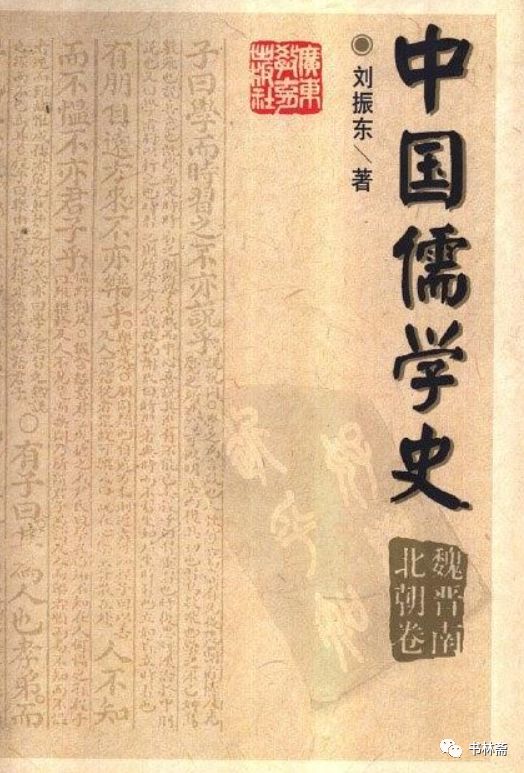
和历史对话。
司马家终于还是篡位了,司马炎想继续儒家思想的推广,但毕竟没法在「
忠
」字上作文章,于是只能着眼于「
孝
」字。《陈情表》里说「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但缺了「
忠
」的儒家体系好似缺了一条腿,不伦不类,随风倾倒。
终究这个「
孝
」字也还是没能立得起来。
两汉经学终于大崩溃,杀戮的时代彻底来临,伴随着的还有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当然能觉醒的都并非寻常人家,夹缝中生存的统治者们开始寻找玄学。荒诞的世界,后现代的人生,西晋终究没能逃过永嘉之乱。
在南方,在玄学兴起的同时,佛教与道教也开始渗透进思想文化主流之中,于是冲突必不可免。
牟子《理惑论》出现在了历史上,终于开始对儒家进行彻底的反对和清算;道教则走向了另一条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里,一方面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另一方面论证了道教与儒家的并行不悖。
在北方,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十六国刚刚封建化,亟需加强稳定,这时儒家的作用便出现了,拓跋宏来到洛阳时,看到了乌鸦,他很难过。
乱世何时结束,南北儒学、玄学、经学、佛学何时渗透并统一呢?
目光放在河西走廊,问问李暠。

在南北朝乱世时期,由于没有一个朝廷给社会以稳定秩序,于是各地宗族们开始独立形成自己的小世界,这就是坞堡。当然坞堡最早出现在王莽时期,我们这里看到的已经是它快消亡时了。
北魏皇权来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刚建立的政权,它必须和中原豪强地主达成妥协,这边是宗主督护制,但随着时代向前,当皇权日渐崛起(皇权必然会崛起)时,宗主督护制则必然会面临瓦解的可能,这时怎么办呢?
可以说有两种办法,也可以说没有办法。一是看着它瓦解,二是抗争。抗争无非是两个结果,一是失败,二是胜利。但胜利后的宗主不可能甘心当宗主了,于是它必然会成为新的皇权。本质上这是历史的进步,只是对历史来说,并不在乎谁是皇权的代言人。
以上是本书第六章的主要内容,但请不要被这些叙述内容误导,本书绝大多数章节并非在讲述这样一个大而化之的历史趋势,而是和李凭先生的博士导师田余庆先生一样,钩沉史料,挖掘出别人没看到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这本《北魏平城时代》可以说是魏收《魏书》的书评。
很多人说魏收的《魏书》是一本废书,因为崔浩国史案,它不可能写太多东西,但读了《北魏平城时代》后你绝不会这样想了,你甚至会觉得魏收和承祚先生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许多地方留下了明显的暗扣,当你把这些暗扣串联起来时,《北魏平城时代》就出现在了你面前。——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一本手册,这是一份秘史,这还是一个动听的传说。
那么本书第五章讲述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样一个动听的传说,它发生的地方——平城。通过对地理史论著与考古挖掘的分析,逐渐还原出了平城的形态,这是很重要的,很多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些不经意的小细节里,正如东汉年间何进如果走了快几分钟也许就不会死了,北魏年间清河王绍动作快一点也许就能登上皇位了。这些很重要。
但这些也不重要,因为无论何进死不死,拓跋绍做不做皇帝,北魏政权的封建化都是必然的,再过一百年,又一个大一统时代的来临也是必然的。
安心等待便是。——这句话是说给历史听的,不是说给漫长岁月中的农民听的。——他们听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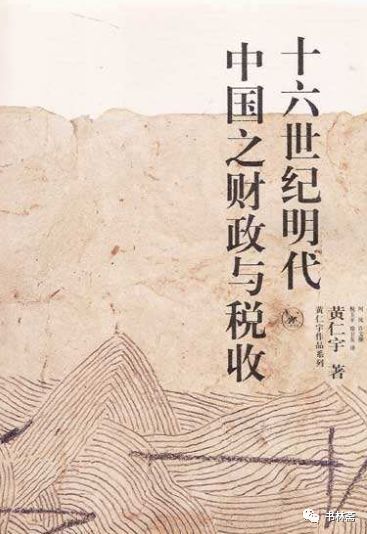
作为第一本梳理明代财政与税收的专著,黄仁宇先生有开创之功。黄仁宇先生通过大量的史料,第一次系统地勾画了明代的赋税和徭役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这些收入都用在了哪些地方,对于读者初步涉足明史有很大的贡献。
然而,本书仍旧可视作《万历十五年》一样的著作,尽管更加学术化,也更加具有价值,但是整体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最后的落脚点道德和开的药方数目字管理是一样的,也因此本书准确说是《万历十五年》的学术版本。
那本书究竟为什么会开错药方呢?其一是黄仁宇先生虽然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万历会计录》;其二是黄仁宇先生一直是在拿明代中国与现代西方作对比,而且只是表面上的对比。亦即无论从具体操作还是哲学层面上,黄仁宇先生都没有能够深入到本质。
尽管如此,我仍旧会推荐这本书,无论你是否读过它,它都是一本比较系统的阐述明代财政与税收的专著,读来是有收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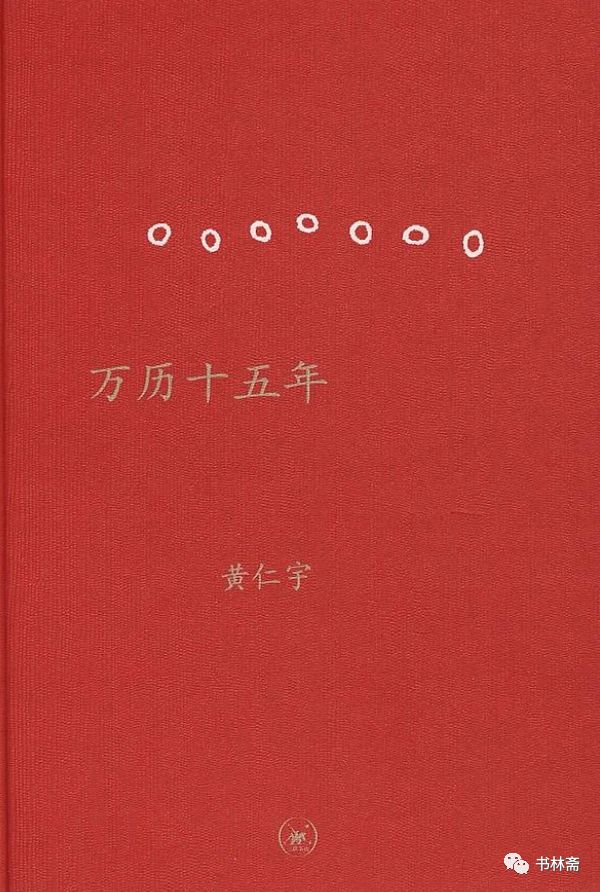
是时候给《万历十五年》祛魅了。
过年回家,又翻了一遍很多年前阅读的《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最好的书是《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这是他的本业,那本书的质量也确实过关,而他最出名的这本《万历十五年》,实在是专著不像专著、小说不像小说。更重要的是,《万历十五年》乱开药方。
由于有明代财政税收的底子,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给明代或者说明清中国诊断的病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黄仁宇先生就像是一个只做理论的医学家,在面对疑难杂症时,开出的药方居然是数目字管理,这未免过于书生之见,属于看不透本质的代表。本质是什么?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里说得很清楚了:「
把封建制的本质看漏,拘泥于政治的表象,以为中国古代领主贵族政治解体了,封建制度也随之消灭,而不知道封建制度的存废,最基本的要看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否还寄生于对农奴或形式上自由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力的剥削上。这基本的剥削事实没有改变,单把剥削方式改变了,即把分封诸子功臣,直接食予其封国封邑的方式,改为以公赋税重重赏之、以俸禄给养之的方式,那并不曾消除封建的本质。
」
此外,黄仁宇先生对道德的判断,也同样没有跳出西方史观的认知,道德的本质是什么?虽然黄仁宇先生隐隐约约触及到了,却未曾真正意识到,道德是一种政治哲学。你想批判传统中国,首先你要先理解生产关系(王亚南),其次你得了解什么是两汉经学和理学心学,只有你充分搞清楚自上而下、帝国和基层都是怎么运转的,你才能真正对症下药地去批判。但黄仁宇先生浅尝辄止,把问题归结为道德领先一切,于是药方只能是似是而非的数目字。
至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文笔是可以的,作为历史散文写作,茶余饭后倒是可以一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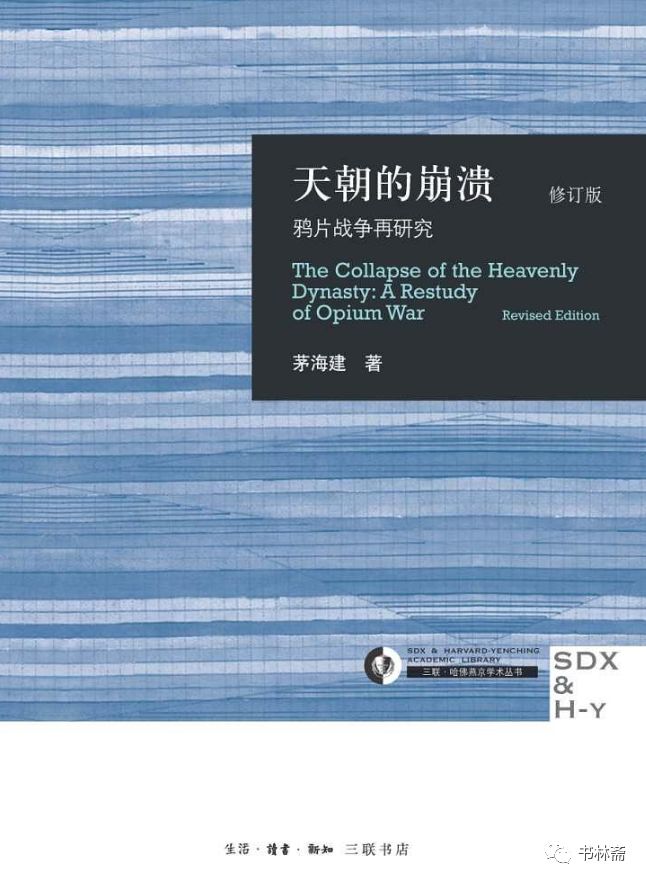
不妨让我们先跳过前面漫长的叙述,看看茅海建先生在本书中的最后一段话:「
150年过去了。19世纪是中国人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人饱尝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的世纪。21世纪呢?人们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呢?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不管历史将做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
本书写于1994年,那正是一个史学界翻案风兴起的时期,茅海建先生这本《天朝的崩溃》自然也不例外,序言里便给琦善翻了案。可以说茅海建先生的史料是比较详尽的,所述及与征引的对象也足够有价值,因此这篇翻案序言是能够立得住脚的。
对于讨论小问题来说,本书很有读的必要,有助于帮你理清鸦片战争前前后后的许多细节,有助于帮你梳理鸦片战争前前后后历史人物的变化。如果茅海建老师的目光聚焦于个体,那么问题不大,尽管会有人说茅海建老师是代历史人物思考,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茅海建老师以几个人的几张面孔,就开始开了药方。开药方之前自然是要找到症结的。茅老师选择的靶子是什么呢?是道德评判和政治体系。茅老师认为,必须跳脱出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必须摆脱这样的政治体系,才能清楚地知道鸦片战争前前后后都发生了什么。
这句话对不对呢?对。但靶子是打在谁身上的呢?
于是我们翻开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里面明明白白写着:
「
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
「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分解和破坏的过程,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京条约后的初期,还没有因以后的条约而开放更多的港口,所以可以称为五口通商时期。在这时期,中国的进出口额比起以后还是很小的,但是在靠近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开始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
「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好像是在其内部深处正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一潭积水,鸦片战争则是投入了一块大石,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而终将使整潭积水激荡起来。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处于十分腐朽的阶段,没有能力对于他们所面临着的历史变局作出灵敏的反应,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模糊地感到,南京条约的订立并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倒是一系列的难以预测的事件的开始。
」
……
引用胡绳先生这么多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在说现当代以来,其实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并未流于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臧否和对政治体系的缄默不语,而是恰恰相反,抛开了对具体人物的评价,直指问题的核心。
而茅先生的研究,恰恰是在给胡绳先生的论调作了最有力的论据,如果您有兴趣,本书其实很值得一读。但对于茅先生的靶子,大可忽略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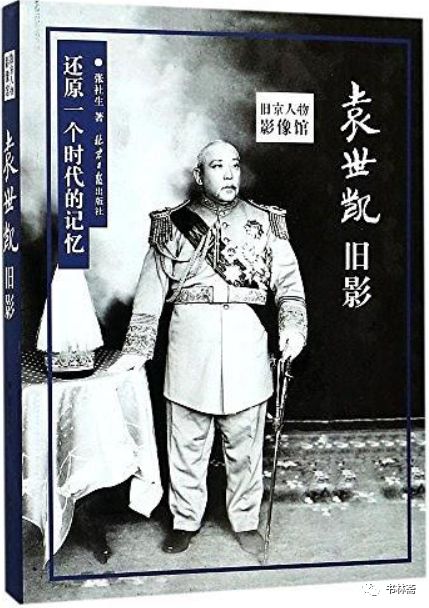
不是很想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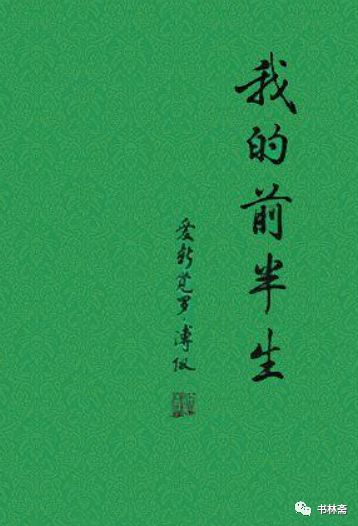
溥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在读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能感觉到,他以强烈的真诚告诉你他是真心的,而我也确实被他说服了。不过如果他不是真心的,不妨分析一下他在这本书中的逻辑是什么样。
首先,溥仪先大量叙述自己过去做过的事情,但是光叙述做过的事情还不够,还要大量叙述做这些事时的心理状态,自我批评越厉害越好,于是大家读着溥仪猛烈的自我批评,则一般不会进一步批评。
其次,溥仪在字里行间中表露出自己之所以有这些想法,是因为他从小就被带进宫中做了皇帝,因此虽然他做了很多罪恶,但是他的天性不一定是坏的,他是被环境影响的。
最后,溥仪在被劳动改造、思想教育时,痛心疾首地告诉读者,当他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凌厉的凄苦和那么伟大的宽恕时,他整个人被震撼到了,于是他脱胎换骨了,他重新成为了一个人。
这一套逻辑非常恰当,既不会让读者觉得溥仪在大篇幅为自己辩解,也不会让读者觉得溥仪唯唯诺诺实在是可怜,只会让读者觉得溥仪在这一连串的叙述过程中,深刻意识到了出生成长环境对他人性造成的极大摧残,并且通过感谢新中国,来让读者意识到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的溥仪诞生了。
我并不清楚溥仪的真实想法,毕竟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而在这之后他也确实没有做过什么,因此不妨相信他是真真正正经过了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后,洗心革面的。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溥仪在这个时候的改变,会让人觉得是真的?
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在用行动告诉溥仪,人类有另一种崭新活法的世界,而溥仪亲眼见到了,甚至在当他被他以为是粗暴的、无知的、容易激动地发泄仇恨的农民宽恕自己时,他彻底明白了。
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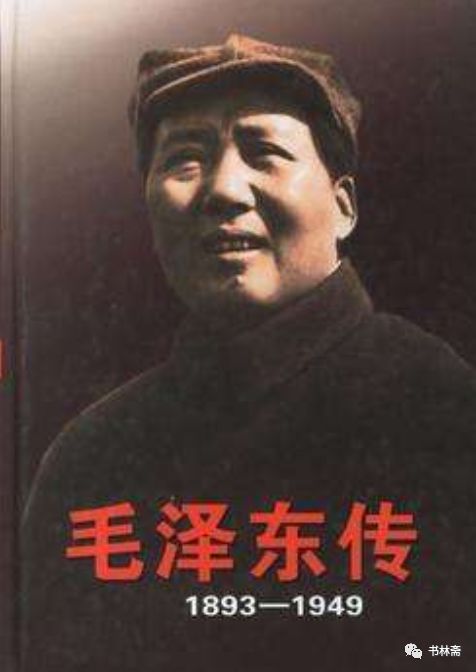
我不止一次写过大量和这个人有关的文字,有的发布了出来,绝大多数保存在我的电脑硬盘里。我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个人,不是我不敢评价,是我没有能力评价。我很清楚,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对这个人产生新的认识、建构新的理解,与此同时我也会不断深入改变自身的想法。
这是第一本每一页都被我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笔记和心得的书,但读完后我仍然无法评价这个人。我可以用很多模型来套用,但这些能否完全完整说明呢?读历史,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更要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每每这么读这本书,都会觉得收获良多。
这本书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把这个人当师傅,一种是把这个人当朋友。你想怎么读,取决于你怎么想他,你怎么想自己。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本书能看出来多少,要看你读史书的能力。比如这个人家里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金冲及先生说这个人的父亲参加过湘军,于是你便可以放飞思绪去畅想。又比如金冲及先生不止一次提及到这个人一直在强调不可过「左」,已经快到逼所有读者都不得不牢牢记住这个人的态度的地步了,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读罢此书,金冲及先生在我心里,不亚于承祚先生。日后要常读。
我相信,对于这样的人,所有人对他的情感都是强烈的。无论是喜欢崇敬,还是厌恶愤怒。虽然我仍旧不知道如何评价他,但这并不重要。他并不需要别人来评价他,他需要的是别人来学习他。

土地革命时期,国军的薪饷和待遇其实是高于红军的,但国军却经常离心离德,相反红军却始终万众一心,显然这不是一句「
革命理想
」就能解释的。这需要我们从更深层次的物质基础来思考。
《苏区研究》2019年01期刊登了任伟的一篇文章《军队民主平均制度的起源与演变》,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了红军的组织架构演变和领导方式,将一个长期以来比较模糊的抽象概念落实到了具体操作。
军队初建时,为什么会有平均主义?为什么会是官兵平等?任伟在这篇论文里分析说,一来红军被四处「围剿」,没有安稳的居所,二来中央经费紧缺,部队没有稳定的外部供给,一切全靠自筹。这就很好理解了,如果薪饷是从外部供给的,那么军官掌握的资源一定高于普通士兵,这时普通士兵再多也会对军官有所不满,但红军的物资和薪饷都是从地主豪绅、官吏财主身上想办法的,官兵在经济地位上是一体的,「
军官没有超越士兵之上的权威凭借,这应该是平均分配的最根本原因,极端贫困状态下,平均主义是凝聚人心的强大武器
」。
因此很快,红军就废除了薪饷制,而改为志愿军制,只发必要的生活费用。这种供给制度虽然让红军士兵实际获得的远不如国军,但却给红军在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粟裕回忆录》里就说:「
井冈山的生活虽然苦,有时连续几个月发不出钱,但因为长官与士兵生活一个样,所以从来没有闹饷的,士兵也不怨恨谁。
」事实上,国军和红军的兵员大都是农民,本身并不存在谁的思想觉悟更高的说法,但因为红军官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当部队遭遇困境时,士兵不但不会向军官发难,反而会采取抱团取暖、共度难关的态度
」,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里就明确提及过这一点。
任伟在这篇文章里进一步说,真正影响官兵团结的,其实是物质分配。只有官兵的生活水平较为一致时,思想与情感才会趋近,士兵才会把军官视作自家人。一旦贫富悬殊扩大,不公平现象加剧,再好的政治教育,都很难弥合军队的整体性裂变。马克思讲,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孔子言,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还有其它好几个层面,只是这个层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拿来与大家分享了。
所以你说,为什么红军能战胜国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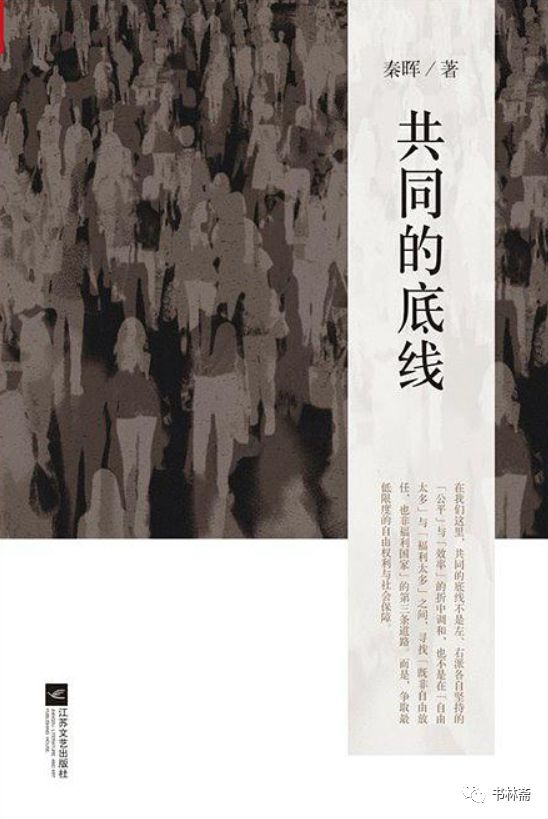
人类的本质还是复读机。秦晖洋洋洒洒一本书,其实就翻来覆去说了一句话:自由主义和社会民生主义,在中国都没有多少,我们要寻找到共同的敌人。
这是秦晖给中国开的药方。不针对他的其它书籍和观点,就单这个观点,我就要反对了。在秦晖的这本书里,只透露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认为只需要知识分子们之间存在共识和底线就可以了。
换言之,秦晖自以为在给中国开药方,其实秦晖是在针对知识分子开药方,在给自由主义和社会民生主义找共识底线,却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
——广大人民群众在乎你在说什么吗?不在乎的。
——但你能不在乎广大人民群众说什么吗?不能。

单说《流浪地球》一篇。相较于电影,更喜欢小说。
电影《流浪地球》看完了。不差,但我看得不够爽。虽然是科幻,但是不新,只有科技是进步的,人类生存方式、社会形态、社会心理没有变化,家庭和国家也还是最传统的那种。当然,作为春节档合家欢电影,这么拍我是可以理解的,那种不太会为之兴奋的理解。
而这一点,恰恰在小说里有所呈现:「
在这个时代,人们在看四个世纪以前的电影和小说时都莫名其妙,他们不明白,前太阳时代的人怎么会在不关生死的事情上倾注那么多的感情。当看到男女主人公为爱情而痛苦或哭泣时,他们的惊奇是难以言表的。在这个时代,死亡的威胁和逃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除了当前太阳的状态和地球的位置,没有什么能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并打动他们了。这种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关注,渐渐从本质上改变了人类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生活,对于爱情这类东西,他们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赌徒在盯着轮盘的间隙抓住几秒钟喝口水一样。
」
不过换句话说,我做制片人的话,估计也选这个主题。
电影里最让我爽到的,应该就是看到东方明珠已经在冰封中突然出现的那一幕,和《人猿猩球》最后忽现自由女神像一样。文明没了。
顺便,如果李一一做主角的话,我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会再高一点。
刘慈欣其实很保尔·柯察金,大家都是费拉,但我与全世界为敌拯救了世界。刘慈欣不是工业党,如果有机会他一定会变成曼哈顿博士。在他的笔下,人类不重要、地球不重要、技术不重要、文明不重要,上帝(他自己)和少部分火种重要。
而这一点在《死神永生》里体现得尤其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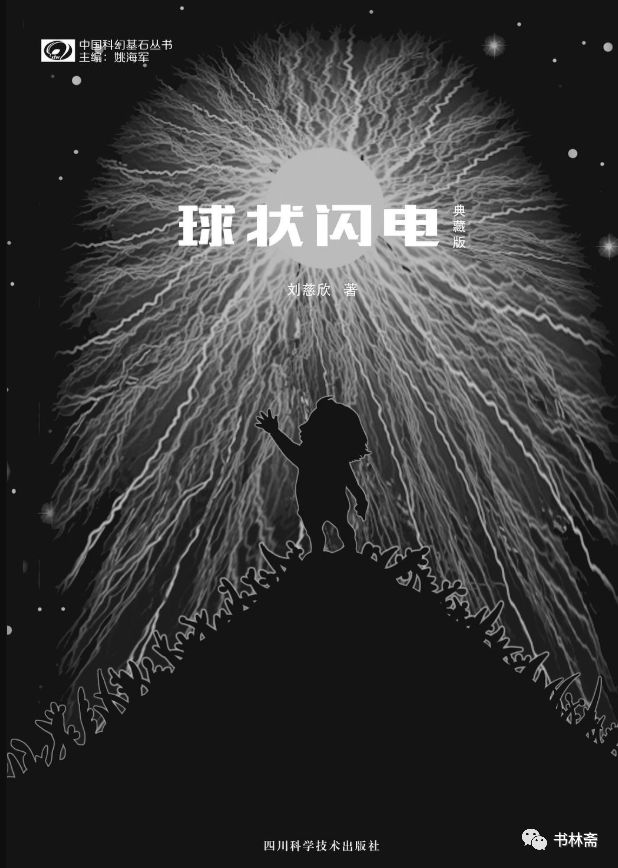
再读刘慈欣的《球状闪电》,愉悦感仍旧是隽永的。那种完完全全的科学式的沉浸体验,故事里没有反派,或者说反派就是科学本身,从一个看似是应用物理的球状闪电入手,在提出它不是被产生而是被捕捉到的那一刻时就已经足够调动起阅读快感,而后还不满足,进一步涉及到了一个自创的新概念:宏电子。当这个概念出现时,这个故事就不只是应用物理了,不是麦克斯韦方程组能计算出来的电力学,而是被迅速拉到了20世纪的物理:量子力学。
但这一点也不会让读者望而却步,因为它接下来涉及到的概念,不会超过高中物理:电子、原子核、量子观测塌缩……只是在这些概念上安插了一个「宏」字,一下子就张开了想象的翅膀,给我们展现出了最深不可测的迷人谜底:「我」的父母究竟死了没有?宏聚变会发生什么?……
和《三体》不同,黑暗森林法则其实是19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变种,二向箔的思维来自柏拉图的洞穴比喻,都是和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描述的是社会性和哲学性,而《球状闪电》是完完全全的科学性,那种冷峻而又迷人的科学真相一步步揭秘到最终时,你会觉得它真的很美好。
啊,那一朵美丽的蓝色玫瑰。它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理科生时,初初接触到物理时的那种震撼。

时至今日,再读《三体》,我仍旧坚持认为刘慈欣的文笔是很好的,刘慈欣写不好的是人物。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其实并不叫《三体》,而是叫《地球往事》。
刘慈欣说:「
我认为零道德的文明宇宙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这就是我写《地球往事》的初衷。
」在这个系列里,第一部叫《三体》、第二部叫《黑暗森林》、第三部叫《死神永生》。刘慈欣在写作这个系列时,锚点不是被叙述的客体,而是《死神永生》的结局,时间之外的那个节点,也因此在他写作时,他必然会不自觉地使用着历史学家才有的笔触,来描摹笔下那个遥远的「过去」:
「
这是1971年秋天一个晴朗的下午。事后叶文洁多次回忆那一时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焦急,盼发射快些完成。一方面是怕在场的同事发现,虽然她想好了推托的理由。但以损耗元件的最大功率进行发射实验毕竟是不正常的;同时,红岸发射系统的定位设备不是设计用于瞄准太阳的,叶文洁用手就能感到光学系统在发烫。如果烧坏麻烦就大了。太阳在西天缓缓下落,叶文浩不得不手动跟踪。这时,红岸天线像一棵巨大的向日葵,面对着下落中的太阳缓缓转动。当发射完成的红灯亮起时,她浑身已被汗水浸透了。扭头一看,三名操作员正在控制台上按手册依次关闭设备。那名工程师在控制室的一角喝水,技术员则靠在长椅子上睡着了。不管后来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如何描述,当时的真实情景就是这样平淡无奇。
」
所以,汪淼不重要、叶文洁不重要、罗辑不重要、章北海不重要、维德不重要、程心不重要、云天明不重要……这是刘慈欣小说的必然,当你的视野放在以百年、千年甚至不可数的时间尺度上时,这些具体的人都不重要,对刘慈欣来说,重要的只有文明。——这是他在前两部半的核心。
直到第三部结局,刘慈欣告诉读者,文明也不重要,因为连宇宙都不重要了,所以物理不重要,所以数学不重要,连数学规律都可以改变,那么还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呢?读完三部曲,很多人会觉得浩渺星空虚无,这像极了《三体》里的那句话:「
空不是无,空是一种存在,你得用空这种存在填满自己。
」
刘慈欣一直有救世主情结,有保尔·柯察金情结,有苏联文学情结,这在上文说过,但在第三部,他连这个情结也给解构掉了,并且没有再对其进行建构。
这意味着什么?我想你知道答案,答案就在你读完三部曲那一刻的感受里。
意味着你是一个上帝,刘慈欣也是一个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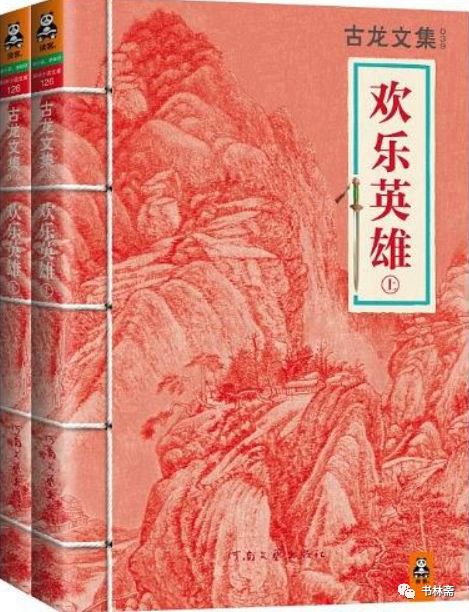
详见:
武侠,超级英雄和地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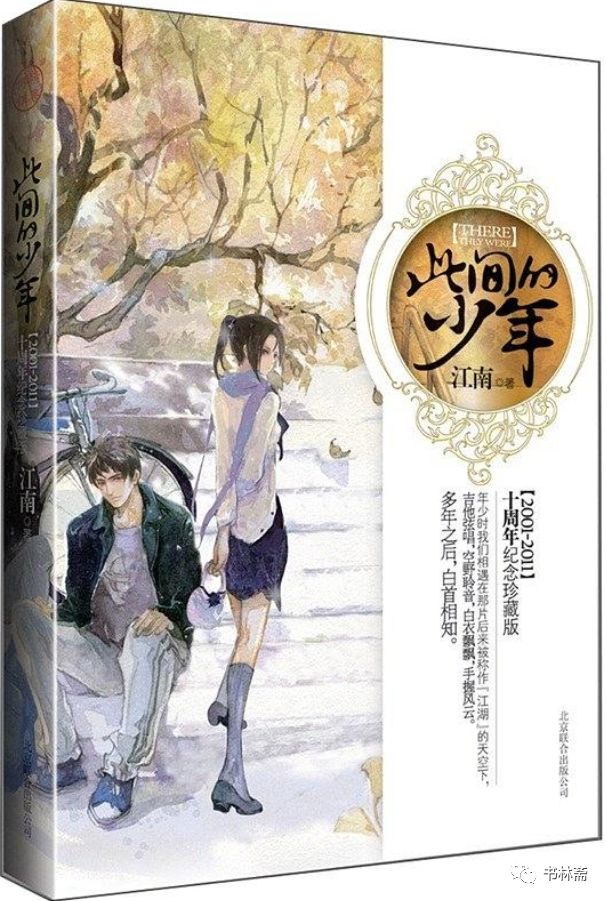
江南文字上的天赋从《此间的少年》就可以看出来了,那些被精心编排过的字句在江南的笔下经常能戳中年少人的心情,而这本书对江南的意义也不仅如此。
虽然江南有天赋,但江南的天赋对他来说是副作用。自从他写了《此间的少年》,于是往后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模板,几乎都是对这本书里好几对人物关系的照搬,郭靖与黄蓉、乔峰与康敏、段誉与王语嫣(实体版未收录)、杨康与穆念慈……有时是性别转换,有时是摘取部分,总之江南后面的那些主角们的人物关系没有超出这几对,他躺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写了二十年小说。
而江南是谁呢?江南是令狐冲。这样一个静静观察着身边一切的令狐冲。尽管他在后记里是这么说的:「
曾经有朋友追问我自己在这个故事中到底扮演哪个角色,我只能遗憾的说这里有我的影子,但是没有真实的我。
」但你会发现,令狐冲是一个旁观者,等到《九州缥缈录》《上海堡垒》《涿鹿》时,就忍不住开始正式书写自己了,内心里永远有一个死小孩,一个空荡荡的地方,这些也许就是江南所说的其他人身上真实的他自己。
而令狐冲是什么呢?
——令狐冲是,我觉得我全世界最牛逼,可是我现在还没那么牛逼,终有一天我要证明我有那么牛逼。
江南做到了吗?你可以说他做到了,大量的数据摆在那;你也可以说他没有,他的过往也放在那。
江南每部小说里都有金句,《此间的少年》里,是乔峰最终没有告诉康敏他的内心,而马大元则跟着康敏去了苏州,不久以后传来马大元和康敏结婚的消息,这时乔峰独自一人跑去操场投了一夜篮球,去之前他扔下一句话:「
马大元以前也就能拿拿篮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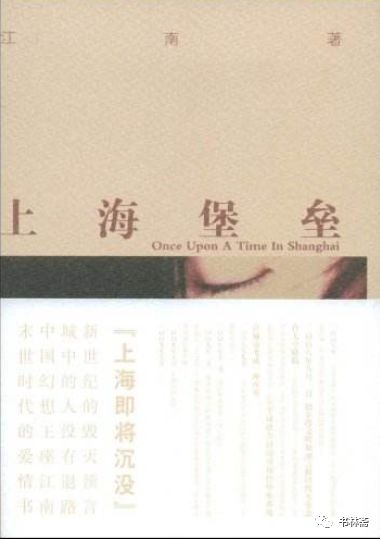
听着《当你老了》,又一次翻完了《上海堡垒》。
江南真的是一个写情高手,无论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了自己多少次,也无论他和过去的人们发生过多少龃龉,他始终是写情的高手。在他的主角心里,永远有一个死小孩,有时叫吕归尘,有时叫蚩尤,有时叫路明非,有时叫江洋……
《上海堡垒》就是这样一本书,它前面所有的铺垫都为了最后两条短信,无论读过多少遍,再一次看到这一页时还是会被撞击,后来路明非和上杉绘梨衣的桥段只能说是两条短信的一次重复。
那么江洋的故事呢?我还是喜欢那个有二猪和曾煜的版本,那个版本更真诚,更少年气。想知道江南在想什么,读《涿鹿》;想知道江南写得最好的,读《上海堡垒》。
江洋呆呆地坐在那里,感觉有种东西从手机里面往外面渗透,像是梅杜莎的目光,她穿越了十几年看着他。他被石化了,他不敢动,他动了他就会崩溃,浑身唰唰地往下掉石粉。
江南最后没有交代,其实我猜他也不知道,正如同江洋不知道、杨建南不知道,而林澜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用书中的话说就是:「
不能追溯了,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你只能循着弦声的余韵去推敲过去的事情,而过去那些事情已经水一样的化去,渐渐变成苍苍白白的一片。
」
好好睡,晚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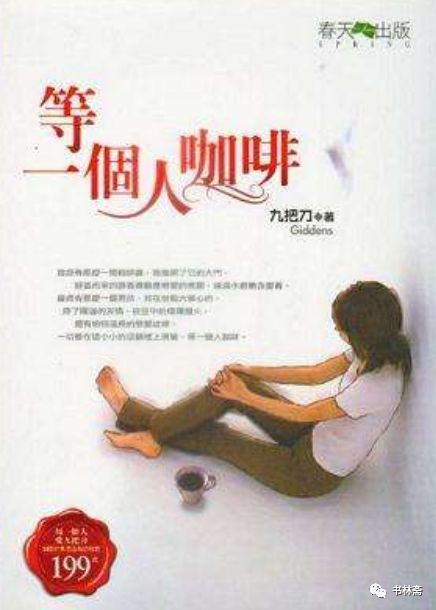
九把刀最好的爱情小说。当然九把刀写得最动人的文字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和《妈,亲一下》,但那都是纪实类的文字,《等一个人咖啡》是九把刀最好的爱情小说。
距离上次阅读这本书过去了大概有七年多了,读完了《上海堡垒》,忽然就很想把这本书拿出来翻一翻,翻完后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九把刀的爱情小说和别人的不一样。
因为虽然看起来每个人的行为都有怪,但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很真诚。技巧和文笔都是锦上添花,但真诚最重要,尽管九把刀这个人很臭屁自大无知,但他很真诚,这一点很多作家比不上。
小说的主角阿拓也一样,他很奇怪,但他很真诚,很多人比不上。
所以谁都会喜欢阿拓,喜欢简单的阿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复杂的人呢?
下面,让我们点题一下,让我们用唯物主义来思考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固有矛盾,这其中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如果你的主要矛盾和另一个人的主要矛盾之间没有大的差异,那么彼此的次要矛盾再大,也是可以调和的。反之,如果想要相安无事,那么必然有一个人的主要矛盾要改变。
所以soulmate很难得,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语言、共同话题、共同价值观是可以做到的。
喜欢阿拓这样的主角很容易,因为阿拓是一个单细胞动物,但是对于复杂的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深不可测的大海。
感性在我看来只是不曾更细致地解构,但感性是好事。正如我们喜欢一个人,我是坚决不同意大多数人想明白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人的,因为一旦解构了感情,那就意味着你知道你喜欢这个人的脸、思想或声音等,不喜欢这个人的打呼噜、一身肉等。
那就意味着,一旦具体化,就可以被替代了,把感情解构下来就很容易变成这样,所以我不支持大多数人解构自己的感情,因为这样会变得很虚无。
心结解开的那一刻,对人的影响是极大的。人的第一反应是会迷茫,如果你不能及时找到填补内心的想法,那最好不要那么做。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开头。你说,为什么要有两汉经学?
你一直在路上,风萧萧的路上,多少金戈铁马,和多少雨雪风霜。
你一定在路上,征尘依然飞扬,你将儿女情长,折叠好藏进戎装。
你总说越是风浪,越生出从容坚强,你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挺起胸膛,我多想变得和你一样。
我想你又在路上,你走得如此匆忙,我沿着你的目光,追赶你的方向,我看到鲜花开满山岗。
阅读原文处可查看文章集锦。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我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