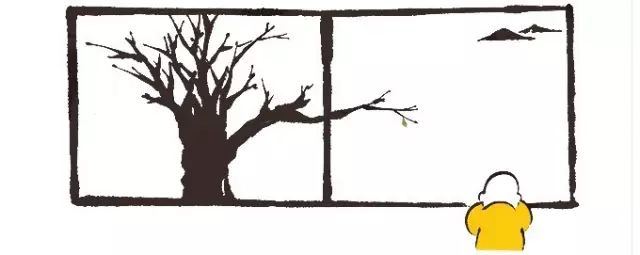2016年,张大磊导演凭借处女作《八月》斩获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一举成名。
此后,他的作品频繁亮相于柏林电影节、平遥电影展等国际影展,并屡获殊荣。2023年,他完成了首部剧集《平原上的摩西》,这是首部入围柏林电影节剧集单元的华语作品。该剧集在“迷雾剧场”播出,标志着张大磊导演的风格进入更多观众的视野,也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与评价。
目前,他正在筹备长片《我们为何要做梦》,同名短片过不久后即将上线。
曾在第二届IM担任终审评委的他是我们的老朋友,最近,IM非常荣幸地与张大磊聊起短片创
作,希望他的分享能为更多年轻创作者提供灵感与指导。

张大磊导演
IM:您的长片处女作《八月》获得了很高的奖项认可。在此之前,您都做过哪些训练和积累?
张大磊:我2006年从俄罗斯回国之前,是在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导演系学习。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拍短片。完成作业的同时,也很渴望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有很强的表达欲。
回来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完成长片拍摄。在2015年之前,拍了一些短片和纪录片,也写剧本。同时也接拍一些婚庆或者政府的微电影项目,保证生活,但每一次拍摄都尽可能的实现一些自我表达,用做作品的心态面对。
有一段时间拍了很多影像的日记,每天要求自己拍一个,十分钟以内,而且不允许
做成配乐小视频那种,是纯粹的视听,要有调度,有内容。直到2015年我终于拍摄了《八月》。
IM:《八月》获奖之后,您继续创作了《黄桃罐头之夜》(2018)、《法兹》(2019)、《下午过去了一半》(2020)、《我的朋友》(2022)等短片。您如何看待短片和长片的关系?
张大磊:
我总觉得短片的自由度更大,完成的可能性更多,就更不应仅仅拘泥于叙事层面。
短片和长片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也许一部短片未来会发展成长片,有这个思路我觉得也不错。
那短片就尽量避开长片的内容,同样的人物,同样的空间背景,但内容是延续或者补充,会很有意思。例如《下午过去了一半》是《八月》的延续,或者是未来另一部电影的补充,当他们联系在一起时会很奇妙。我最新的短片《我们为何要做梦》会有一部同名的长片。
IM:您说过自己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对您而言,电影讲的可以是情绪,而不仅是故事。这种创作思维是怎么形成的?
张大磊:也不是只讲情绪不讲故事,应该说是相对的,或者是尽量别拘泥于叙事吧。
我总觉得电影花那么大力气仅仅是为讲清楚一个故事,就太可惜了。
小说更适合讲故事,想象的空间更大,更有品头,更容易被相信。
电影太实际了,本来就是搬演或复刻。当然好的以叙事为主的电影会给观众带来震撼,至少是坐在影院里那一百多分钟。
我个人会比较关注人物,他们在真实空间背景里的处境,情节是跟着人物的发展去走的。他们要生活,就不可能总出事,大部分是他们对生活做出的反应,也就是情绪状态,也就是我们的常态。喜怒哀乐,更多是常态化的,高兴的时候也不可能一直在笑,反之亦然。叙事在这里是基础,是一个更大的骨架或者容器。
IM:您的几部代表作都主要聚焦于展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生活,为什么对这一段时间情有独钟呢?您觉得这个时代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张大磊:八九十年代是我的童年少年时期,在我的记忆深处,形成了似远似近的感受,这种感受很迷人,它没有那么极端的甜美或残酷,总是恍恍惚惚,分不清虚实。所以八九十年代的时空背景目前成为了我创作的容器。

《八月》剧照
IM:许多影评会说您
影片的安静、缓慢、悠长展现了怀旧感。您觉得这种评价准确么?怀旧在您的作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张大磊:
并不是一定要去怀旧,更重要的是那个空间里的气息很迷人。
过去的时间空间背景、那时的气息,吸引着我,
让我选择来作为创作的容器
。我喜欢讲人,那些让我觉得可爱的人好像更适合在那个时空里。
至少目前是这样。我当前愿意去感受记忆,对此还有很强的表达欲。或者说这是一种我追求的质感,恍恍惚惚。每次拍片都很享受这个过程,像进入一个隧道。
IM:您从《八月》拍自己熟悉的日常故事,到《蓝色列车》建构起一个架空的精神乌托邦,再到《平原上的摩西》改编一部具有悬疑、犯罪色彩的畅销小说,面对不同的题材、素材,您如何调整自己的创作方法?
张大磊:也谈不上去调整创作方法,我依旧是从人物开始,还有空间背景的气息。我首先得被人物打动,会有强烈的愿望想要认清他们,看到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然后去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以整个的创作过程会比较漫长。
人物关系和时空背景起来之后,就会有无限的想像空间,各种人物纷纷出现,不仅是主要人物。他们都会有各自的特点,生活方式,甚至生命轨迹,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功能性的一闪而过。
IM:《平原上的摩西》相比于“迷雾剧场”的其他剧集展现出了更强烈的导演个人风格。很多观众称它为“磊味儿十足”,您觉得“磊味儿”是什么?
张大磊:我不敢接受“磊味儿”这个说法,不论是褒是贬都不敢。我们已经很难有自己的味儿了, 其实很容易从作品中看到很多前辈电影的影子,我们只是在吸收他们的养分,来做自己的表达。
IM:在制作这部剧集的时候有考虑观众接受程度的问题么?打破常规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张大磊:实话讲,我从没有考虑过为了观众去这样或那样,没有这种区分。大家都是生活里的人,谁和谁都不会相差太多,
把自己最真诚的感受表达出来就行了,这就是和观众最好的交流。
只能说有相同感受的观念会喜欢,反之就不太喜欢。难度和挑战更多是制片层面的。制片人会承受更多
压力,承担风险。他努力创造自由表达的条件,我们在不断的碰撞中让创作的方向尽量不流落俗套,也不陷入自恋。
作为一个导演,我认为明确自己的眼光,明确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是至关重要的,这可能就是个人风格。

《平原上的摩西》剧照
IM:听说您大二时就基本确定了想做的影片的美学基调,您当时是如何确定的?
张大磊:大概是上大一的时候,在课堂上看到导师用录像带放的那些影史经典,我那时才开始认真的看电影,并为电影着迷,渴望了解更多。暑假回国就买了一些相关的书,了解电影史,也了解到很多影片和导演的信息,从北京淘了很多dvd和牛皮纸包装的刻录vcd,什么都有,当时特别狂热,感觉就像以前组乐队的时候淘打口磁带。
整整两大箱光盘带到圣彼得堡,过关时险些被扣了。大二开始,平均每天看三部,什么都看。在那一年我看到了特吕弗的《四百击》,侯孝贤导演的《风柜来的人》,杨德昌导演的《青梅竹马》,塔可夫斯基导演的《镜子》,小津导演的《东京物语》,贾樟柯导演的《站台》,之前看过《小武》,但《站台》更打动我。
这些电影唤起了我对时间、空间、记忆的感知。说不清楚,那种感觉似曾相识,很朦胧,恍恍惚惚,还夹杂着气味,很像小时候放暑假一个人趴在窗台上看着楼下发生的一切,时间静静地淌过去了,似远似近,触不可及。
当时就特别沉迷于这种感受,想要抒发。其实从小就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后来看一个侯导的纪录片,他也谈起过这种感受。
IM:您对生活细节的捕捉特别敏锐,这种细腻的观察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么?如何培养呢?
张大磊:好像没有什么方法去培养,我自己会对生活细节会比较敏感,它们都和记忆有关。经常会有人在当下,感觉却飞到曾经的某一刻。这都是因为某个细节,声音,甚至是气味,是那种恍恍惚惚的感觉。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库,有人总去开启,有人很少去留意。
IM:风格的形成需要哪些方面的积累和实践?有没有经验可以给到新人导演,如何去确定自己的风格?
张大磊:我总觉得拍着拍着就应该找到自己的风格了。风格不太准确,可以理解成自己的角度,或者说自己愿意怎样表达。这好像没有什么实用的经验。有就有了,没有就继续
拍,继续表达自己。

《平原上的摩西》剧照
IM:您说过在拍《平原上的摩西》时,不会把演员当成职业演员。您常常会给演员很多自己发挥的空间,甚至在开拍之后就让他们把剧本扔掉。为什么喜欢这种方式?
张大磊:我会很在意演员的选择,要清楚片中的角色到底长什么样,什么性格,怎样的说话方式,尤其是他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这时候最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的特质,所以要选择最对的那一个,演员本身最接近人物的那一个。
所以职业与非职业在这里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人的特质。就去和他们交流,努力把心中的这个人物让演员也感受到,并且相信,然后共同去经历一段我们创造的生活。
IM:您曾说过您的剧本不标准,比如《平原上的摩西》,里面很多都是文学化的描述,没有台词。这种情况下演员和导演之间该如何避免分歧?
张大磊:我觉得剧本最大的作用之一,是代替语言的沟通。有时候讲话会挺没意思的,会意的感觉更好。所以剧本要让人看后有感触,而不是去了解谁谁干了什么,怎么了,说了啥。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剧本感受到人物,感受到他们的处境以及内心、情绪,如果剧本可以有音频功能,最好把音乐也一同呈现。这也再次体现了演员选择的重要性,要确信自己选择的那个人是懂的,是能够感受到的。
IM:最早《八月》是您自己出资拍的,甚至是在未知资金是否能撑完的情况下“冒险拍摄”的。在此之后的作品,还有没有遇到过资金不足的问题,您是如何应对的?
张大磊:很多年轻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在没有人了解的时候只能自己先投入。每一部电影都有可能遇到资金问题,资金有多少才算够呢?永远是多多益善。
我觉得开拍前自己还是要对作品有个大概的预判,最低要多少预算才能完成,能够不凑合,否则就不轻易开始。
创作者和制片工作人员需要沟通好,相互理解,相互
支撑。
如果拍摄过程中钱不够,那就想办法再找呗,或者随机应变改变拍摄方案,删除一些场景,保证可拍的内容能有最高的完成度。

《八月》剧照
IM: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努力寻找机会的新人导演?
张大磊:
我目前也只拍过那仅有的几部作品,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没什么经验可分享。
很多电影节的创投对于创作者是很好的机会。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能力,创造力,强烈的表达欲。
坚信自己要表达的,然后尽自己所能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