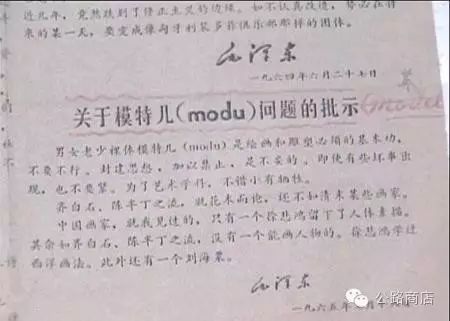“没到过凡尔赛,不算到过巴黎;没到过黄桷坪,不算来过重庆。”随着四川美术学院搬离,以川美为核心的黄桷坪艺术生态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黄漂流失了一半,艺术工作室相继关闭,只剩涂鸦墙上的怪物继续张着嘴巴。

除了梯坎儿豆花和奇味干锅,涂鸦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艺术专业考前辅导班”,和许多所谓的“画廊”。和北京的798艺术区比起来,黄桷坪显得太杂乱,但艺术与本地大众之间,离得并不远。

不止一位黄漂艺术家说过:“有些东西似乎还和以前一样,有些东西却在悄无声息地改变。”
这里生活着几十名“棒棒模特”,他们来自附近郊县,
在美院周边揽活儿,经常受雇于美院师生,帮忙搬东西,抬画,参与一些会展布置的工程。
一边当棒棒一边当裸体模特挣钱。

在重庆,山多坡陡,过去运输不便,所以有了棒棒这一职业,他们帮忙搬运行李货物以赚取工钱。
因
形象质朴,加之价格低廉、随传随到,棒棒
进入美院当模特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特分着衣,半裸和全裸。一般都是从着衣的模特开始做。全裸的薪酬高出不少,虽然不算多,这对棒棒而言也算是笔收入。

留胡须、习惯裸着上身、穿松紧短裤扎皮带、手机套在皮带上、一手拿棒棒,是一些棒棒模特心照不宣的标配。也有人对这份工作表达了自己的敬重:来上课时把头梳得整整齐齐,再套一件西装,尽管旧且并不合身,范儿正。

以前老师们经常去茶馆和棒棒云集的牌摊转悠,招募有意向的裸体模特。教学科的经费紧张,雇佣棒棒当模特是合理选择,劳动生活带来的肌肉线条也符合教学需求。
招的棒棒一定得痩,胖的不要。

和老师关系好的棒棒自然是得到照顾,基本都可以排到课,一周三天,一三五或者二四六,上四十五分钟,休息十五分钟,大家一块儿去画室门口抽个烟。

有时候谁生病了, 还会推荐自己老婆或是女朋友前来顶缺。这份工作得熟人推荐,真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一天六到八节课,多了能挣三四百,甚至衍生出回扣和分成。
裸模已逐渐被发展成一个产业。

对刚入行的裸模来说,身上最后一件衣服就是自己守了几十年的底线。第一次别说脱了,
夹在二三十个学生里,
头都抬不起来。
刚做裸模的棒棒,往往要老模特带一段儿。头一两周里不用脱内裤,习惯以后渐渐就敢了。有些老模特连裸着放屁都悠然自得,不介意被人观察到菊花开合。

学生个人绘画的角度和方向都不一样,同样的一个姿势一个造型,摆好就不能乱动。要不是平日里挑东西培养出来的耐力,很多人是撑不下两三节课的。
画完了,才能换动作。

“我不懂什么是艺术,为了养家糊口,只要能通过正当途径赚到钱就可以了。”
棒棒老刘一直向家里隐瞒自己的模特工作,直到有天儿子来找他,看到学生送给老刘的画。当时他就说,你这个工作根本就不是人做的,脱光的事你怎么好意思去做。吵了很多次,换工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直做到现在。

脱衣服比靠体力赚钱来得容易,但对于一些农民来说,这意味着某种耻辱。老刘说,如果是自己的儿女来当裸模,他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与老刘不同,同样农村出身的赵姐认为裸模也是一种艺术。她年轻时热爱绘画,但是因为家境不允许她继续深造,只能早早出来打工,经人介绍做起了裸模。
“挣钱是其次,绘画给人创造一种无形的美。”

她也曾感受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但并不愿意提起那些议论过自己的人。她的母亲从不主动向亲友谈起女儿在外面干什么,而是默认表示支持。
“有的人不理解,懂的人明白这是为艺术献身。”

“模特就是一个道具,跟其他静物没两样。”
首次画裸女,气氛如葬礼。美院的女生反而更大胆,男生画异性相对害羞,一脸严肃。身经百战的赵姐在休息时会主动点评一番作品:“也!嫩个还阔以。”“嫩个豆不得像我了噻。”

有些棒棒因为长期做模特,帮着做展,会提出建议和意见。
比较开放的艺术家,也会让棒棒帮忙点评。
有个叫田庆华的棒棒,觉得自己当裸模不如别人画画挣钱,自己学起了绘画,收藏的画作据说比有些画家还多。他的作品最终受到了肯定,美院甚至专门为他办过画展。不画画的时候,他依然是一名棒棒。

绘画的人愿意画有细节的东西,女孩儿的脸是很难画的。棒棒的身体和面容,
有沧桑感,有很多细节,值得去刻画,
很容易出效果。
一个动作可能要坚持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一个学期。刚开始做的裸模只需摆一些简单的动作,时间久了就不行了,老师和同学会提出新要求,做难度大的动作。
最难的就是站着,腰杆必须是直直的,侧过来,扭过来,手有些时候都要撑得竖直,两只手吊在上头,脖子也要扭着。

“模特很辛苦,扭捏得让人心疼。但当进入创作状态的时候,画画的人眼中只有结构,效果和感受,没有其他。”学生小王说。可以理解裸模因为酸痛做出了一些姿势上的调整,或是长时间的疲惫导致的瞌睡不断。
但是如果动作有一点走样,局部就白画了。

学生非常尊重和维护他们,不带无关外人进画室。
规矩得有。

裸模们忌讳被拍照,平时都需要把大门关紧
艺术创作一般不会触碰模特身体,有时模特造型特别累或者不标准,同学们也会帮他们校正。遇到蚊子落在屁股上的情况,模特睡着了没发现,男同学会帮他打蚊子,模特也觉得没什么。
在疲惫的人体课程中,温情互动是抵抗创作枯竭的有效方法。

课程结束时,往往是裸模和艺术生关系的低谷。双方都被彼此折磨到崩溃边缘,但出了门他们并没有相忘于江湖。
美术系的学生经常在路边看见自己画过的裸模,他们有时还会跟你打招呼:嗨,你画过我,我脱了个精光。

也有日久生情的情况,不足为外人道也。

某美院男生与女裸模日久生情,终使该女模怀孕。学校要处罚该男学生却苦于找不到相关校规适用,几经讨论,最终以“破坏教学用具,致其严重变形”为由勒令该学生退学。
模特之间也有鄙视链,闯荡江湖几十年,在一些生活琐碎上多的是油滑和刻薄。但那些至多算是玩笑,不构成羞辱。
一个棒棒可能会在下课时问另一个,今天晚上不去找鸡?

在俗称棒棒鸡的性工作者那里,有个不成文的福利,可以去每天最后一个客人家里过夜,早上起来煮碗小面给他吃。
这对棒棒来说特别有诱惑力,好像找到了家一样的感觉。

“棒棒鸡”有时也愿意去作为摄影模特拍个照,挣上三两百。现在少了,严打以后很多人开了自己的门市。
“外面很少有人尊重我们,”当了20年搬运工的老唐说。在校园里,他们和师生之间感到了真正的相互尊重。老唐可以做水电工泥水匠,也可以搬东西参与布展工作,很多工作室灯光电源都是他接的。有时候会被别人叫去打个小长工,每天收入二三百,算下来挺高的,有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到一万。
比起当裸模,他更愿意当个棒棒,“那个钱也不好拿,挑起比坐到舒服。”

“做模特,感觉只是同时在打两份工。”每当生意不好,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去安排上课,当人体模特的时候更像是一种休息。
棒棒们也在转型,有的买车搞起了运输,有的跑起了滴滴。老唐照旧去打牌,手机响了,就去干活。做一天挣下三四百,再耍两天,就是自由。
过几年他打算回到自己的镇上继承父业,办个医馆。挑黑了的扁担要带回去,收好。

“我一趟挑二百多斤。现在年轻人不下力,也不愿意,挑不起了。”
黄桷坪艺术生态区红火的时候,还有棒棒作为人体模特,跟随艺术活动去过外地,坐飞机去的。川美搬迁,501、102走了,艺术生走了,大批老师搬家去了大学城。
棒棒们在帮忙搬家的过程中也捡到过一些被遗忘的画。有的值几千几万的,捡到的棒棒不识货,有人出价几十块也就卖了。现在都知道画值钱了,拾不到了。

“现在不行了,原来这里好看得很。”美院附近混久了,棒棒模特的艺术修养也跟着提高了。画展上的画,拿出来一看就知道哪个老师画的,都认得到。

萧条是一个必经过程。川美离开了,影子还在。仍有艺术家在这里追求梦想,川美毕业的人,也许会重新回到这里建立工作室,这些艺术家和棒棒便是黄桷坪存在的理由。

镜头回到当初,交通茶馆人声鼎沸,老师学生,黄漂们不分尊卑,吐沫横飞地讨论着后现代。艺术空间里,棒棒专注地为展台嵌进每一根钉子。每年总有人加入黄漂的队伍,这是他们生活着经营着的所在,只有经历者才能领悟。十年后,人们谈起黄桷坪和这些棒棒,希望他们用的词不是“曾经”。
道路不会消逝,消逝的是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