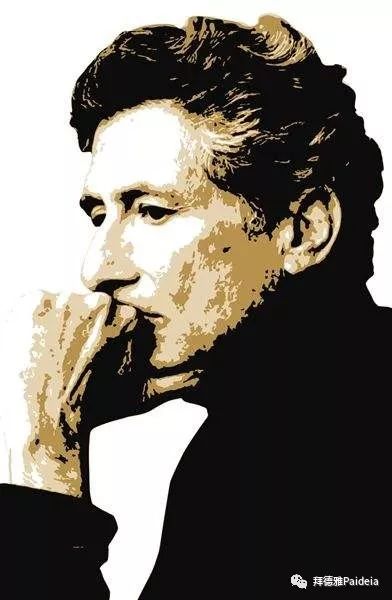
布莱恩·特纳
/
文
王立秋
/
译
在我出版《韦伯与伊斯兰》
(1974)
的时候,关于马克斯·韦伯的零散的伊斯兰社会学的文献还相对较少。盖尔纳
(1975)
在《人口研究》上给了我积极的评论,但我对韦伯的诠释,以及盖尔纳的回应,在后来也遭到了以“赫尔小组”为中心的那些人的批评。这些人是游离在专业的中东学会之外的,激进的社会科学家,他们认为那些学会是保守主义的学术建制。而我,正是学会的成员之一。作为对这场辩论的反思,我出版了《马克思与东方学的终结》
(1978)
。这本书受到了像路易·阿尔都塞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对像丹尼尔·勒纳、和施洛莫·艾维纳里那样的学者所书写的主流的社科文献持批判态度。
出于偶然,我对社会科学的概述刚好与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在同一年出版。我立刻就被爱德华的进路,以及这个人吸引了,他把比较文学研究和政治介入结合到了一起,并亲自提供了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模范。萨义德是迷人的,这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学者都会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而他的自传《格格不入》
(1999)
完美地捕捉了这种感觉。他持续的流亡与错位情绪,在他作为“爱德华”的西方身份,和他作为“萨义德”的东方人格中得到了充分地表达。但尽管我至今也没有改变对他这个人的看法,现在,我也不得不承认,回过头来看,关于东方学的这一整场争论,看起来就是一个死胡同,如果说还不算有害、破坏性的话。
不消说,韦伯对伊斯兰,以及更普遍地说,对“亚洲宗教”的看法,已经被当作习惯于拿动态的西方来和停滞的东方对比的东方学的一个范例遭到了谴责。
[1]
尽管遭到了持续的批判,但是,韦伯的进路,作为一个普遍的框架依然是值得注意的。韦伯的遗产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尽管事实证明,萨义德关于东方学的论述提供了对西方学术的有益的批判,但同时事实也证明,它不是——并且很可能它也不准备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或者说系统的对东方学的替代。在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之后,除更多的文本分析和解构研究外,还有什么——如果有的话?
萨义德的作品当然正当地成为了后殖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怀疑的是,它有没有给社会科学也带来什么持续的好处。回头看,我并不认为除了一些审慎的建议——关于想当然的假设,要有自己的反思;要意识到持续的偏见;又或是要公开批判隐藏的种族主义假设——外,萨义德的批判给我们指明了什么具体的,方法论的方向。不过,这样的建议也很难说是原创的,它们也不大可能引起争论。因此,我的回应的要点是,萨义德的遗产反而给这样的假设火上加油了,这种假设认为,做研究的学者,在研究实际的社会的时候,不需要通过民族志或其他形式的研究来收集数据,而只需要考察文本就好。结果是为服务于对文本的解构,而质疑完全合法的方法论和研究问题。如果说这场辩论给了我们什么教训——而我是第一个吸取这一教训的人——的话,那就是,学者们会无意识地受到智识风尚的影响,急着去抓文学理论和欧陆哲学的无花果树叶。也许,米歇尔·福柯关于伊朗的“精神革命”的著作是另一个能够说明何以时尚会蒙蔽我们对社会实在的理解的例子。
[2]
与任意数量的关于谱系或话语或互文性的作品相比,我更情愿让我的学生去读读马歇尔·霍奇森的《伊斯兰的历险》
(1974)
或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
(1998)
。
无论如何,我不完全相信萨义德的《东方学》完全是原创的。他也说他参考了雷蒙·施瓦布的《东方的文艺复兴》,后者出版于
1950
年,追溯了东方学的早期阶段,特别是梵语研究的发展,并为萨义德自己的《东方学》提供了语境。施瓦布通过详细分析翻译与诠释的兴起而考察了对他文化的智识责任问题。萨义德为施瓦布著作的英译本写过一个惺惺相惜的导言,这个导言后来再版于《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之中。因此,塑造萨义德关于欧洲对伊斯兰及中东之文化占有的理解的,是施瓦布,而不是福柯。从这些研究中,萨义德吸收了语文学的起源信息:所有人类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人类的文化才开始种族化,才出现了按在很大程度上说不可通约的语法来给人分类的看法。
如今,对萨义德作品的批判简直太过于众所周知了。首先,他夸大了西方关于伊斯兰与中东的学术著作的自洽程度,结果,要在萨义德的范式内给路易·马西尼翁、威尔弗雷德·坎特维尔·史密斯、马克西姆·罗宾森、以及马歇尔·
G.S.
霍奇森分类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萨义德注意的主要还是文学界的人物,而不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文学的领域,他主要关注的是法国的贡献。
其次,许多激进的作家已经为攻击西方的殖民主义而充满同情、充满理解地书写过他文化了。近年来,我一直在教关于亚洲社会的社会学的课,在这些课上,我开的阅读书单上的头一本书就是萨义德的《东方学》,但从实践上说,要把萨义德的框架应用到像《印度之旅》、《缅甸岁月》、或《沉静的美国人》那样的文学作品上也很困难。而且,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流文献——如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或斯考切波的《国家与革命》,又或是罗伯特·贝拉的《想象日本》——也很难被指控为东方学。
第三,萨义德很可能也促进了东方学的出现。
[3]
批评西方帝国主义的人经常忽视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对许多亚洲人来说,经济帝国主义的意思,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结果,东方学辩论低估了亚洲为反西方而生成的种族意象的力量。我们应该把东方学看作关系式的、对话式的。黄种女司机、和对白种外国人或者说外人的普遍厌恶的问题,就清晰地表达了传统日本在与外部世界接触问题上的模棱两可。
[4]
亚洲人的刻板印象,也可以说明的确存在一种可以说,是“反向的东方学”的东西。
最后,关于东方学的辩论与中东政治密不可分:因此,要做到客观地评估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泛泛地说,对东方学的批判,并没有看到两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即针对阿拉伯人的种族主义,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之间的讽刺性的关联。萨义德本人也当然也注意到了这点。在《东方学》的导论中,他写道“此外,出于一种几乎无法避免的逻辑,我发现自己写作的,是一个奇怪地、秘密地分享着西方反犹主义的人的历史。反犹主义,正如我在它的伊斯兰分支中讨论的那样,和东方学彼此相似,这,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真相——要充分理解这个真相的讽刺之处,你只需要对一个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说出这个真相就够了。”
[5]
在回应他的批评者的时候,萨义德也提到了他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犹主义之间的相似。在《宗教与社会理论》
(1983)
中,我提出,有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即伊斯兰的缺口,和犹太教的矛盾的概念。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在伊斯兰一直为它的缺失(缺理性、缺自治的城市、缺独立的资产阶级、缺禁欲主义等等)所定义的同时,犹太教也一直为其宗教命令的矛盾性质所定义:根据韦伯《古犹太教》的说法,在犹太教的宗教命令中,它的神法把个人救赎的要求,转交给了一套仪式化的规定。西方是参照懒惰的、感官的阿拉伯人,和不值得信任的犹太人来定义自己的身份的。事实上,正因为犹太教和伊斯兰共享了这么多的东西(一神教、先知与超凡的启示、有经的宗教、和一种激进的末世论),这些对照的范式的建构,才显得尤其悲剧。
在我职业生涯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从萨义德关于音乐的作品,比如说《论晚期风格》
(2006)
中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因此,我开始只批判东方学,而不去指责人。人道主义的价值——这才是比较文学真正的遗产——充盈地流淌在萨义德关于传统东方学的局限与危险的作品之中,他关于智识流亡的想象之中,和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介入之中。实现这些价值是他持续关注的问题,而如今,这些价值在现代学术中的实现,因为他的去世,而变得无限地困难了。
2009年9月
注释
[1]
阿尔曼多·萨尔瓦多
(Armando Salvatore)
:《超越东方学?马克思·韦伯与在伊斯兰研究中对“本质主义”的替换》
(
“
Beyond Orientalism? MaxWeber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Essentialism’ in the Study of Islam”)
,
Arabica
43 (1996), pp. 412-33
。
[2]
珍妮特·艾法里
(Janet Afary)
和凯文·安德森
(Kevin Anderson)
:《福柯,性别与伊朗革命:伊斯兰主义的诱惑》
(
Foucault, Gender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The Seduction of Islam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
[3]
詹姆斯·
G.
卡里尔
(James G. Carrier)
编:《西方学,西方的意象》
(
Occidentalism,Images of the West
,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95)
。
[4]K.
科尔斯基
(K. Kelsky)
:《与外国人调情:日本“国际时代”的跨种族性爱》
(“Flirting with the foreign:Interracial Sex in Japan’s ‘International’ Age”)
,载
R.
威尔森
(R. Wilson)
与魏马尔·迪桑雅克
(Wimal Dissanyake)
编:《全球
/
地方,文化生产与跨国想象》
(
Global/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NC and London, UK: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9-192.)
[5]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