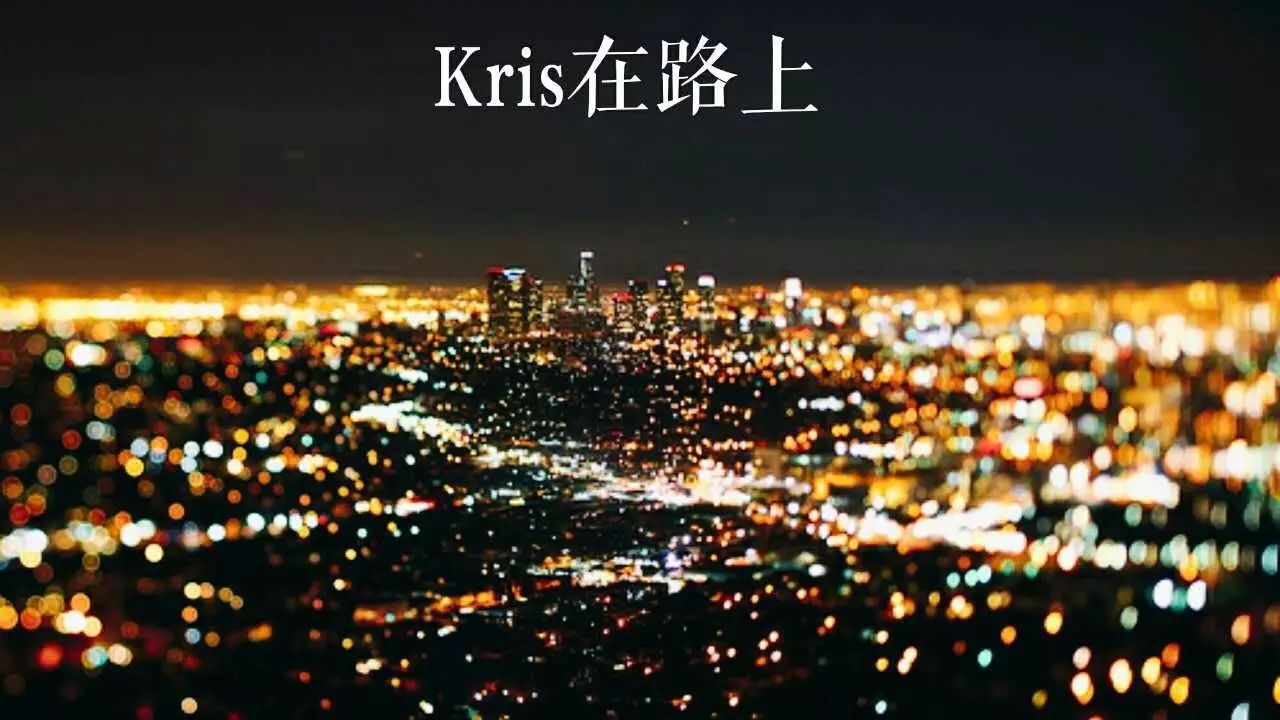
今天在整理书柜的时候,发现了一本09年出版的小书,《不实》,作者叫柏邦妮,是她在2005-2008年断断续续完成的明星访谈录。
我都已经忘记了自己还买过这么一本书,随手翻了几篇采访,竟然看得很投入。
不说文字,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曾经的大明星现在依然星光熠熠。
梁家辉、赵薇、范冰冰、周迅……
但我最感兴趣的却是朴树。
采访的时间是2005年初,那时的朴树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横扫华语乐坛,这张专辑也陪伴了我很多时光。
那年他32岁,和现在的我差不多年纪。
柏邦妮问:你是不是很爱阅读或者写字?我觉得你的歌词写得非常好。
朴树:我偶尔看书……那些歌词还是太雕琢了。
柏:你平常除了写歌词,还写什么呢?
朴:写日记。
……
柏:能写多长?
朴:有时长,有时短。短的时候就一句话:
“又混了一夜。”
有意思的是,昨天晚上,我也是:
“混了一夜。”
这也是我昨天没有更新的主要原因。
当然,我的混可不是什么不健康的夜生活,而是和两个高中同学吃饭喝酒聊天,然后还征得老婆同意,在同学家过了一夜。
三个人差不多9点钟到家,然后斗地主,斗到了快2点才去睡。
无聊吗?不无聊,因为想了想这可能是几年来第一次这么折腾了。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本科的时候甚至还破了KTV连刷三夜的记录。
但是工作之后,尤其有了家之后,这种生活已经彻底离我远去了。
每年回老家过年,和老家工作的同学聊天,总会酸溜溜加一句:“真羡慕你们每天打麻将的生活。”
但其实,我知道,真的让我这么过生活,用不了几天就会崩溃吧。
打牌是其次,主要还是聊天。
昨天聊天的主题是:
压力。
没错,以前隔三差五就会聚一次,但从2017年开始,我们的聚会频率骤降,因为,大家都太忙了。
三十而立或许是每个人的诅咒,三十岁以前总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但三十岁已过,生怕什么事情都来不及。
我说,每周一脑子里就一个词:“
疲于奔命。”
起早到公司,干活到9点赶紧出发去学校上课,然后经历上下午两节大课之后,马不停蹄地回公司加班。
疲于奔命的感觉真的不爽。
同学W,就是那个和我一起跑马的兄弟,《
无兄弟,不跑马——第一次用脚来丈量42公里
》
,跑马拉松的时候他正在复习考研,变态到我们整个高铁路上他都在背单词,背政治,当时那篇文章我写到:
“你要是考不过,天理不容啊。”
果然,他高分通过考试,现在在中国最好的医院研究生部就读。
“很累,事情很多”他说。
“现在我一有时间就赶紧休息,因为我知道如果一刻不停,我可能真的会崩溃。”
这就是压力吧。
我说:“你以后就是王专家了,说不定国家领导人以后还得找你看病。”
他笑笑:
“差的太远,越学越觉得差距之大。”
同学Z,就是那个之前我写的那篇《
那些不动声色就搞定一切的人到底有多酷
》里
,在燕郊买房的那个。
这次其实聚会是一方面,另外也算是给他暖暖房,参观他的新家。
因为他爱人也怀老二了,最近回老家,所以邀请我们过来happy。
在从饭店回家的路上,他说:
“当时知道有老二之后,我和老婆犹豫了一周,我最后说,大不了把房子卖了离开北京,我们换个地方生活”
于是,两人决定,生!
是啊,在北京要二胎,真的是一件极其需要勇气的事情,压力大到喘不过气。
但,如果因为压力,就放弃了一直想要的四口之家的生活,那何必要守着这座城市呢?
这一夜,虽然混过去了,但却混得很开心。
就像W说的,有时候紧绷的状态,很可能一击即溃,倒不如找个机会放松自己。
休息是为了更好的上路,混是为了以后的不混。
混完这一夜,想清楚了很多事情。
压力大不是因为自己能力差,而是我们多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
因为我们都相信,
通往梦想的路上,不会有捷径。
出于好奇,我搜索了一下柏邦妮,原来才意识到,她就是那个《奇葩说》的编剧辩手。
顺藤摸瓜找到了她的知乎,然后就看到了她的这篇回答:
问题是:
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到北上广深打拼,即使过得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
非常贴合今天文章的主题:压力
。
以下是柏邦妮的回复:
昨天在手机上看到那个牛逼回复,很感动,今天还是忍不住,
爬上网,写下自己的回答。
我二十岁那年,是个傻逼电影青年,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电影,
我决定辍学北上,去心中的电影圣殿——北京电影学院旁听。
在北京,我基本上只认识一个人,带着家里给我的两万块钱(也是家里几乎全部积蓄),
带着自己攒的几本电影书,毅然来到北京北漂,如今已有十二年。
初到北京的日子,住在电影学院旁边北影厂招待所,一个床位,每月四百五十块。
当时电影学院拉片室,拉一部电影得要六个小时,一个小时三元,得要十八元。
学校最便宜的盖饭六七元。为了拉片,我把盖饭分成两份儿吃,中午一半,晚上一半。
旁听的那一年,没出过海淀区,蹭所有能蹭的课,看所有能看的片,
到港台资料室,复印当时买不到的台湾远流版电影书,
不让复印的,手抄。就这么抄完了朱天文的很多剧本。
旁听的第二年,老师介绍我写一个电视剧,三十集。
我可以坦然承认,那真的是个烂电视剧,但是那时候,是我唯一的机会。
所有写过的烂片,都曾经是我唯一的珍贵的机会,被人唾骂亦无怨无悔,
因为很早我就想明白了,我们这个行业,就像打游戏晋级一样,你得慢慢积攒你的行业资历。
A级的导演,找A级的编剧,A级的演员,如果你是C级的编剧,为何会用你?
D级并不可耻,积攒几部,我就是C级,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走。
摩羯座从来不相信侥幸,只相信努力。
每一个机会,我从不轻视,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和才能,最大心血去写的,
因为我知道,机会只有一次,就是眼下这一次。
真的很苦。
一天写两万字,一大早制片人打电话披头盖脸来骂你,改不知多少次,
宿舍没有网,写完了去网吧传,在网吧查资料,手抄下来回去写。
浑身疼得要死,躺在地板上,缓解一会儿,继续写。
有时压力太大了,自己一个人出去哭,
站在三环天桥上,外面下雪,哭完了回去继续写。
真的是生写出来的。
编剧这一行,会写都是其次,能写,爱写是第一位的。
后来写过一次主旋律题材,一个部队老编剧说,他们写剧本,条条框框修修改改更是数不胜数,
怎么办?“谁叫你爱写呢?谁叫你爱这个呢?!”
说得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
是啊,谁叫你爱这个呢?!
并不能总接到剧本,得活吧,好多年给杂志写时尚文章,采访明星。
时尚杂志要的是绚丽吹捧的文字,有自己的路数,要命的是一起约稿一起截稿,
也就是说,四五家杂志约稿,几天之后,一起截稿,压力大到不可思议。
最要命的是,内心的理想和现实的工作的冲突,看看自己写的那些稿子,
总是痛苦得不行,隔一段时间就责问自己一遍,觉得自己烂掉了,写废掉了。
心里最苦的时候,手心肿胀,有两倍厚。
刚出道的时候,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
上面写:NEVER WRITE WHAT I DARE NOT SIGN。
我绝不辜负自己署名的每一篇文章。
很幼稚,很挣扎,但是很认真,很较劲,明星采访,娱乐专题,山东快书,企业改革,
我接的每一单工作,都尽全力去做。
就这样,一点一点在行业内站稳脚跟,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
06年,考研第三年,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研究生。
07年,写李少红导演版《红楼梦》电视剧,08年,写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
09年,和彭浩翔导演合作,写《撒娇女人最好命》,10年,写舞剧《金瓶梅》,
11年,话剧《北京我爱你》,12年,和张一白导演合作,
13年,和关锦鹏导演,林育贤导演合作,虽然后面这几个项目都没成,
但是我学到了许许多多,从写字到做人,衷心感激。
来到北京时,我20岁,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并不自信,一无所有。
十年以后,我还在这个城市里,做着我想做的事,
我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是,我没有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不忍离去?
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
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
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
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分割线我不会弄就这么着大家懂就好啦)
我有一个干姐姐,是一个庞克文艺女青年。
我认识她的时候,也是不省油的灯,画画,和搞音乐的男人在一起,
深夜我们坐在路边抽烟,觉得自己是美丽世界的孤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