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物行止录(四)
陈远 辑
据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还有一次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恰巧那天黄侃也在隔壁请客,听到老师说话,学生赶紧过去打招呼,黄侃一见便对他批评起来。学生请的客人都到齐了,黄侃还不放他走,学生情急之下,便把饭店的人叫来,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的钱全都记到我的账上。黄侃听了大乐,便对学生说,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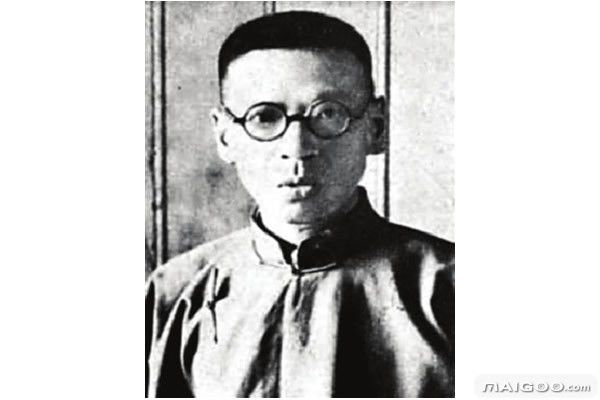
在北大执教时,黄侃曾借住在吴承仕家,二人既是章门弟子,又是朋友。黄侃恃才傲物,在课堂上经常放言无忌,一次被女生告到系主任吴承仕那里。吴知道黄的脾气,委婉地请他注意,一言不合,两人便闹翻了。不幸的是,这年七月,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突然病逝,念华年仅19,“性行和厚,能读父书”,黄侃悲痛欲绝,“思避地以杀其悲”(黄焯语)。也许因为悲伤过度,黄从吴宅搬走时,不仅不付房租,还在白色墙壁上用毛笔写满了许多带鬼字旁的大字,画了许多黑色叉叉,并在房梁上写下“天下第一凶宅”几个大字。吴向他索要房租时,他不仅拒不支付,还理直气壮地说,再要房租,须还我儿来!吴只得作罢。
郑奠是黄侃最喜爱的学生,黄去教室上课时,常常让郑奠替他拿着皮包。郑奠毕业之后,也留在北大任教,与黄侃由师生而同事,但对黄侃还是很尊敬。
有一天,国文门教授黄节在家里请同事吃饭。黄侃和郑奠师生二人都前去赴宴。郑奠那天穿了新买的一件皮袍。黄侃见了,大为不悦,便说:“我还没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
郑奠心想:你管得着吗?就回了一句:“我有穿皮袍的权力!”
黄侃听了很生气,从此再也不理会郑奠了。

蒋梦麟
蒋梦麟初到北大时,与陈独秀气味相投,他俩都一个相同的习惯,就是在参加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就喜欢把冷盘或者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上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吃饭了,所以大家都说他们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1924年10月,鲁迅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当时的《晨报副刊》。鲁迅的好朋友、编辑孙伏园随即编发,但是在见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到报社看大样,发现鲁迅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撤掉了。孙伏园一看就按捺不住火气,加上刘勉己又跑过去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然而又说不出任何“要不得”的理由,孙伏园一时气急,顺手就打了刘一个嘴巴,还追着他大骂一顿。第二天,孙伏园就辞职了。
1925年东南大学风潮中,柳诒征遭人攻讦,说他想做文学院院长,又说他想做江苏教育厅长,柳也不分辩,只是马上辞了东南大学的教职,远走东北,应了东北大学之聘。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柳先生才回来任该校教授兼筹备委员。当时实行的是大学区制,全省的专门学校和中学校,都归这个大学管辖。国民中央政府规定,指拨江苏田赋180万,充教育专款。而省财政厅长说,江苏预算已经制定,田赋收入并无余款可以指拨。校长和财政厅长商量不通,派柳先生和另外两三个筹备委员去仍是不通。隔了一天,校长再派柳先生等两人去。财政厅长说,已说过一个钱也没有,何必又来说空话。柳先生说,这次不是来说空话,只是商量一个具体的办法。接下来说:我晓得财政家都有个秘诀,收入是以多报少,支出是以少报多。财政厅长一听立即站起来说,哪有这样的情形,若是这样,你来当厅长我去教书好了。柳先生说,请您莫动气,我若是不明了江苏财政的实际情形,也不敢乱说,我是读书人,已从《赋役全书》上看到了最近全省的各种统计数字。我们江苏的老百姓向来不敢拖欠国税,但是每年秋勘之后,征收总不足额,那是各县知县和胥吏舞弊,名为民欠,其实都可追缴。所以每年的预算,都有带征积欠一项。前天厅长让我们看的本年预算,田赋收入项下,既与征额之数不符,又和前几年实征之数不符,又未载明带征积年的欠款,这不明明是以多报少吗?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将我写的一篇账请你细看。厅长无语。柳先生又给对方出主意,说,你既已在省府会议上说过没钱,再开会时,也不必说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只说教育经费至关重要,教育界诸位逼迫太甚,我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各位就不必问这笔钱的来路,你看这样说好不好?这话若可行,就一言为定,180万照拨,你若不以为然,我就将我所写的,在各报上公布,请莫见怪。“这位厅长,真正漂亮,听我一席话,满口应承”。
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任研究教授时,校长林文庆召集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教授们开会,说明“学校经费困难”,提出削减研究院一半经费的计划。教授们纷纷表示反对,说:“研究院的经费本来就少,连研究成果的印刷费都付不出,绝对不能再减了。”
林文庆无奈,只好使出撒手锏:“关于这事,不能听你们的。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