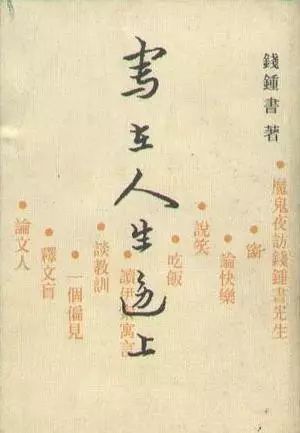
一直很喜欢钱钟书先生的文字,举重若轻,读起来一点都不累。就算是文论,钱先生也能够写得让人心旷神怡,富有“理趣”。记得高中时代第一次读《写在人生边上》,我心里就一直在嘀咕,这老家伙真没叫错名字,他到底读了多少本书!?现在仔细想想,只能佩服钱先生读书笔记和卡片的功夫做得十分到家,所以不论是文论,还是散文,写起来都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中西合璧的引文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地方,让
读者如我既羡且敬。但是读《写在人生边上》总感觉那个时候的钱钟书似乎刚从国外留学归来,选题立意都透着很浓的西欧色彩,即便是引文也是中少西多,不成比例。虽然明知道这纯粹是个人风格,毫无垢病之处,但还是让多少有些“中文情结”的我感觉有点遗憾。《窗》这篇我很喜欢的散文也让人有了类似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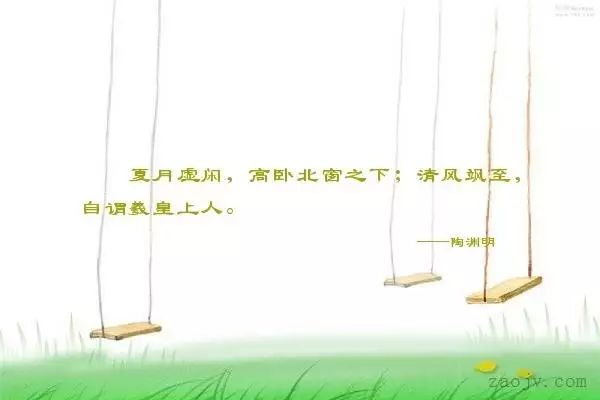
其实,在中文里面,“窗”一直是主体处于和谐状态的象征。陶渊明在《归去来辞》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这种主体的和谐透着中国一种特有的风雅,一种独到的智慧,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一种“行到水穷处,坐看风云起”的潇洒。值得注意的是,从陶渊明开始,中国文化又多了一个传统——幽窗夜自吟:在幽静的夜晚,守在小窗前,望着那灿烂的星空, 憧憬着美妙的人生境界,吟咏着自己宽广而又温柔的心灵。久而久之,我们的身心都与那广阔的星空、美妙的境界融为一体,实现了人生的超越。后世刘方平的“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吴从先的《小窗自纪》和陈眉公的《小窗幽记》所体现出的从容和空灵正是与陶渊明一脉相承的。当然,我们这样并不是说只有夜晚的窗子才是和谐的象征,在杜甫那里,白日的小窗也同样具有了极强的主体意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真是好诗!看过一遍之后还想再看一遍。只有读了杜甫的诗你才知道中文可以构造的多么精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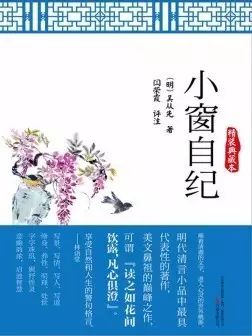
宁静的夜晚,推开窗子,抬头就可以见到天上的明月。这样的场景对于待在家里的人当然是十分舒适和惬意的事情,但是对于离家在外的游子来说,却是乡愁来得格外清新猛烈的时候。“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李白的乡愁,质朴纯粹,似拙实巧。“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这是王维的乡愁,删繁就简,清新自然。“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这是柳永的乡愁,孤寒冷峭,落寞异常。“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弦解语,恨难说。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这是辛弃疾的乡愁,国恨乡愁,尽在纸端。

乡愁是让人痛苦的,但是更让人痛苦的是,自己不能陪在心爱的人身边。听!“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闺房深处寂寞的人儿,她的心声是多么的酸楚。“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浪漫的李白相思起来果然是惊心动魄,不由得“使人听此凋朱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沉郁的杜甫来得则是非常的含蓄,不说自己想老婆,却说孩子不知道想爸爸。“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当年为了娶这个老婆不惜得罪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令狐绹,仕途从此坎坷。一份经历了世俗考验的感情当然值得拥有一篇传世之作来为它讴歌。“小轩窗,正梳妆,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苏轼的生死恋情缠绵悱恻,就算是今天读来也忍不住让人流泪。举了这么多男诗人的例子,如果再不举一个女诗人,女权主义者们恐怕要骂了。别着急,这不是来了:“放下你的信笺,走到打开的窗前,我把灯撑得高高,让远方的你,能够把我看见。”舒婷虽然是现代诗人,但是这也正表明了,“窗”作为相思的象征从古至今从未断绝,而美妙的中文也一直后继有人。





